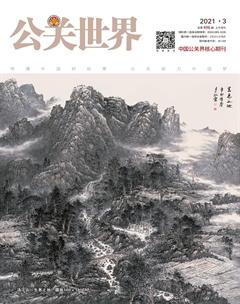中印自貿(mào)區(qū)建設難點問題探析
一、研究背景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現(xiàn)行國際金融體系中存在的漏洞,沖擊下的WTO多邊貿(mào)易談判進展緩慢,全球貿(mào)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jīng)濟陷入泥潭……為尋求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世界各國尋求一種更為靈活的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形式,自由貿(mào)易區(qū)由此重煥生機。事實證明,自貿(mào)區(qū)建設有效拉動了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加速了全球經(jīng)濟復蘇。
為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從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機的再次發(fā)生,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應運而生。規(guī)律的會晤機制、不斷翻新的發(fā)展議題和種類繁多的雙多邊合作為國際經(jīng)濟復蘇做出了極大貢獻。為推動合作進一步完善,中國提議建立“金磚國家自貿(mào)區(qū)”并釋放利好信息:“通過設立自貿(mào)區(qū)可以廢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充分發(fā)揮競爭優(yōu)勢,促進貿(mào)易和投資自由化” 然而,因中印存在意見分歧,此提議而難以落地。這不禁使人聯(lián)想到中印在一帶一路自貿(mào)區(qū)和中印自貿(mào)區(qū)建設中的艱難磋商,感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中國與印度作為地緣接壤、實力相近、訴求相似的發(fā)展中大國,推動建立雙多邊自貿(mào)區(qū)既是大勢所趨,又將帶來廣泛好處。但金磚國家自貿(mào)區(qū)、中印自貿(mào)區(qū)、一帶一路自貿(mào)區(qū)、孟中印緬經(jīng)濟走廊、RCEP等一系列自貿(mào)區(qū)建設議程均遭到印方的拖延、回避或拒絕。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不是對自貿(mào)區(qū)建設存有偏見。1998年,印度與斯里蘭卡簽署自貿(mào)協(xié)定;2003年,與東盟通過“印度—東盟地區(qū)貿(mào)易和投資區(qū)”的建設協(xié)議;同年,與泰國簽署自貿(mào)協(xié)定;2004年,《南亞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框架條約》簽訂;2005 年,印度與新加坡“全面經(jīng)濟合作協(xié)定”簽署。2010年,印度—東盟自貿(mào)區(qū)進入實質性階段……由此可見,印度參與自貿(mào)區(qū)合作的興趣廣泛,而中國被有意排除在了名單之外。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將本著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tǒng)一的原則,嘗試找出中印兩國在自貿(mào)區(qū)建設議題上合作難的主要原因。
二、原因的假設與分析
(一)經(jīng)濟利益沖突
由于在經(jīng)貿(mào)結構、發(fā)展側重和經(jīng)濟制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與差距,兩國利益沖突和貿(mào)易摩擦日益嚴重。
第一,中印貿(mào)易不平衡或使印度將對華經(jīng)濟合作評估為“挑戰(zhàn)有余而機遇不足”。中印貿(mào)易摩擦首先體現(xiàn)于貿(mào)易不平衡。目前中國為印度第二大貿(mào)易伙伴,而印度僅為中國第七大貿(mào)易伙伴。2006年以來,中國對印度貿(mào)易順差額逐年增長。 印度擔心自貿(mào)區(qū)的建立將繼續(xù)拉大中印差距,增強中國在印度勢力范圍內(nèi)的經(jīng)濟影響力。
第二,印方始終沒有對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地位給予官方承認。究其原因,一是印度自身反傾銷法界定不明,二是對中國市場開放性和透明性存疑,三是西方主流態(tài)度的影響。三者相疊,構成了印度曖昧不明,陰晴不定的對華經(jīng)濟政策。印度是對華提起反傾銷訴訟次數(shù)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其對中國市場經(jīng)濟地位的不承認為印度回絕金磚國家自貿(mào)區(qū)等雙多邊自貿(mào)區(qū)提議提供了直接理由,嚴重阻礙了中印經(jīng)貿(mào)互信和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進程。
第三,兩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日益明顯,出口市場也有較大重合。正如“印度制造”是“中國制造”的競爭對手,中國第三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也對印度服務業(yè)構成了挑戰(zhàn)。因此,在第三國市場中的競爭加重了印度對中國自貿(mào)區(qū)提議的疑慮。
然而,上文提及的“印度擁有與世界各國建立經(jīng)貿(mào)關系的強烈意圖”及中印其他領域可觀的經(jīng)貿(mào)合作,都從側面反映出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兩國經(jīng)濟領域的競爭。下面我們將以印度的內(nèi)外政策為切入點,逐一探討影響兩國自貿(mào)區(qū)合作的非經(jīng)濟因素。
(二)戰(zhàn)略互信缺失
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壓力下,印度的沖突型戰(zhàn)略文化傳統(tǒng)、傳統(tǒng)安全邏輯、“不結盟”歷史及大國情結共同推動形成了印度對華信任赤字,自貿(mào)區(qū)建設的停滯是其在經(jīng)濟層面的表現(xiàn)。
第一,以曼荼羅理論為代表的沖突導向型戰(zhàn)略文化在印度頗為盛行,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被由包括友好國、中立國和敵對國組成的曼荼羅圈所包圍著”,其核心觀點是“鄰國往往會成為敵人,而敵人的鄰國則是朋友或盟友” ,歷史上,印度控制不丹和尼泊爾、分裂巴基斯坦、討伐斯里蘭卡等行為便是對這一理論的實踐。當曼荼羅理論與門羅主義情結相結合,再加上意識形態(tài)分歧和歷史遺留問題,“中印安全困境”便形成了。此外,一帶一路建設的南亞部分加深了其疑慮,印度認為中國必將對其南亞地區(qū)影響力發(fā)起競爭,中方建設自貿(mào)區(qū)的提議也是如此。
第二,印度更傾向于短期、可視化、靈活的合作關系。本著“要么再度輝煌,要么淘汰出局”的“尼赫魯思想”,印度的外交政策帶有很強的目標導向性,所有決策都是為了實現(xiàn)大國夢而服務。此外,在“非暴力,不合作”和不結盟等政治傳統(tǒng)的影響下,印度更傾向于靈活的多邊關系,“鐵打的目標”與“流水的政府”也使其戰(zhàn)略決策傾向于短期、可視化的利益獲取,其在“美印日”與“中俄印”合作機制間的周旋正是這些特點的體現(xiàn)。
第三,在中印合作中,印度更傾向于相對收益。沃爾茲認為,在合作機會面前,感到不安全的國家更關注相對收益,即“誰將收益更多”,而不是“我將收益多少”或“是否雙方都能獲益”。印度單方建構的“中印安全困境”使印度將自己設定為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一方”。因此,即使涉華自貿(mào)區(qū)的建立將使印度獲得可觀的絕對收益,但只要其緊盯相對收益,合作就是困難的。
第四,中國、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復雜的三角關系及印度對涉巴事務的敏感態(tài)度為中印關系的發(fā)展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條件,中印雙多邊自貿(mào)區(qū)建設也深受影響。
綜上,政治層面上互相信任作為國家關系建立的基礎,與各個領域都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lián)性,是中印雙多邊自貿(mào)區(qū)建設進展困難的源頭。
(三)復雜的外部因素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美國深感其世界主導地位受到挑戰(zhàn),進而謀求全球戰(zhàn)略布局的轉變,以維持其全球優(yōu)勢地位。這樣的訴求在特朗普當選后達到高峰,該政府發(fā)布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公開指出美國將更加關注“印太”地區(qū)。
然而,相較于美印“準盟友”關系的培養(yǎng),印度政府仍將“大國崛起”作為首要目標,繼續(xù)大國平衡政策和“東進”戰(zhàn)略。參與“印太合作”不僅是為了制約中國,也有加強與東盟、日本等國聯(lián)系、擴大在亞太地區(qū)影響力的目的。
綜上,外部因素對印度政策制定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由于印度政策的自主性與發(fā)展目標的明確性,外部勢力很難對印度決策形成主導。印度對印太戰(zhàn)略的考慮沿襲了其一貫的“搖擺政策”,美方施壓難以決定其利益評估。
四、結語
經(jīng)濟競爭是印度在涉中自貿(mào)區(qū)議題上猶豫不決的直接原因,印太戰(zhàn)略等外部影響是輔助因素,政治互信缺失是根本原因。戰(zhàn)略互信是國家合作的充要因素,推動中印雙多邊自貿(mào)區(qū)建設應著力加強兩國戰(zhàn)略互信。
推動合作的可能方式是:秉承“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的精神,對中國提議的“潛在競爭者”即國際其他雙多邊合作機制進行研究,站在印度角度量化評估其優(yōu)缺點,分析印度戰(zhàn)略評估的可能性機制。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積極調(diào)整中國自貿(mào)區(qū)提議的細節(jié),繞開短期內(nèi)難達一致的歷史遺留問題,求同存異地將仍存發(fā)展空間的區(qū)域建構為印度認可的,相較于同期其他機制更具吸引力的,能在短期內(nèi)看到回報的雙多邊區(qū)域合作機制。一旦印度將其評估為本階段最具戰(zhàn)略意義的自貿(mào)區(qū)合作機制,合作難題便會不攻自破。
參考文獻:
[1]辛仁杰:《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中印關系》,《南亞研究》2011-3
[2]王學敏:《中印參與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的現(xiàn)狀分析及戰(zhàn)略比較》2012-7
[3]薛梅:《中國貿(mào)易順差問題研究》2009-11
[4]任飛:《印度戰(zhàn)略文化對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影響》,《南亞研究》2009-2
[5]陳宗海:《印度對中國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域外觀察》2020-3
[6]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與印度對華戰(zhàn)略邏輯》,《當代亞太》2019-6
(作者簡介: 李欣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黨外交學院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系專業(yè)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