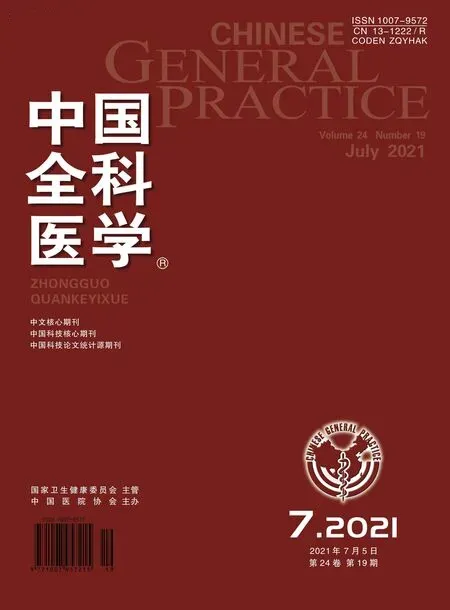我國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估指標體系研究進展
魏云,王飛躍,王美榮,潘朝路,金光輝,路孝琴
全科醫生是居民健康的最佳“守門人”。隨著全科醫學的快速發展和分級診療制度[1]的逐步落實,越來越多的患者逐漸轉向基層醫療保健機構接受健康服務。隨著患者下沉,基層全科醫生是否能夠勝任新時期對全科醫療崗位的工作需求,該問題受到業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勝任力這一概念由McClelland提出,在《測量勝任力而非智力》中將勝任力定義為:勝任力是指能區分特定工作崗位和組織環境中績效水平的特征[2]。目前歐洲[3]、美國[4]、英國[5]、澳大利亞[6]、加拿大[7]等已經有較為成熟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體系。而在中國,尚未形成統一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體系。近年來,國內陸續有研究者積極探索構建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因此,本研究利用當前數據信息對國內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旨在了解目前中國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進展,為發展統一成熟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標準和系統規范的評價方法提供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檢索策略 2020年9月15—25日,采用計算機檢索3個中文數據庫(中國知網、維普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中文檢索詞包括:全科醫生、全科醫師、家庭醫生、基層醫療衛生人員、崗位勝任力、勝任力模型、能力、評估、評價、指標、工具。采用高級檢索,構建檢索策略:(崗位勝任力+勝任力模型+能力)*(全科醫生+全科醫師+家庭醫生+基層醫療衛生人員)*(評價+評估+指標+工具)。以“中文摘要”或“題目”為檢索條件,匹配方式為“精確匹配”,檢索時限為“發表時間不限—至今(2020年9月)”。同時,通過其他途徑檢索到與主題相關的參考文獻也納入本研究中。
1.2 文獻篩選標準 納入標準:(1)研究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的文獻;(2)研究確定的評價指標或崗位勝任力標準;(3)研究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的學位論文。排除標準:(1)重復文獻,即同一篇文獻刊登在不同的期刊,同研究內容在期刊和學位論文中均有報道,或同時收錄于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2)非科研性質的文獻,包括卷首語、目錄、分類索引、征稿啟事、告知、讀者來信、刊登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文摘、新聞消息、新聞訪談等;(3)綜述類文獻,未報道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4)會議紀要、政府公報、政府工作報告、領導講話、對機構工作的介紹和總結等;(5)研究專科醫生或者護士崗位勝任力的文獻;(6)未發表的灰色文獻。
1.3 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完成信息提取。內容包括發表時間、發表期刊、研究方法、研究開展地點、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內容、是否經過信效度檢驗等。當有疑問或意見不一致,通過咨詢本課題組中的第3名研究員解決。
1.4 統計學處理 根據文獻計量分析目的和研究內容,使用文獻管理軟件NoteExpress管理文獻,應用Excel建立數據庫,提取、收集文獻信息。本研究計數資料用頻數和率表示,并結合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納入文獻基本情況 共檢索到相關文獻762篇,最終納入分析的中文文獻31篇(見圖1)。其中27篇為中文期刊文獻,4篇為學位論文。中國開展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的研究發表時間為2011—2020年,其中2016—2020年發表文獻20篇(64.5%)。指標構建在全國跨省層面開展的有3篇(9.7%),在地方省市開展的有27篇(87.1%),其中上海開展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的研究最多(6篇,19.4%),其次為浙江省(5篇,16.1%)、廣西壯族自治區(3篇,9.7%),其他省市開展相對較少(1~2篇)。發表雜志最多的是中國全科醫學雜志(14篇,45.2%),其他雜志發表數量相對較少(1~2篇)(見表1)。

圖1 國內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文獻檢索及篩選過程Figure 1 Search and screening process of the literature on positionspecific competencies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hinese general practitioners
2.2 指標構建方法 本研究納入分析的31篇文獻中,24篇(77.4%)采用多種指標構建方法相結合的方式開展研究,剩余7篇(22.6%)采用某一種指標構建的方法開展全科醫生指標體系的構建研究。涉及的指標構建方法有9種,使用最多的是文獻研究法(22篇,71.0%),其次為定性訪談法(14篇,45.2%)、問卷調查法(14篇,45.2%)、Delphi法(14篇,45.2%)(見表2)。此外,8篇(25.8%)研究報道了所研究的指標體系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系數);9篇(29.0%)研究對指標體系進行了因子分析,驗證其結構效度,其中6篇研究(19.4%)同時報道了信度和效度的驗證情況(見表1)。

表1 納入的31篇文獻基本情況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31 included literatures

表2 31篇文獻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構建方法應用情況Table 2 Methods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on-specific competencies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hinese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the 31 included studies
2.3 指標體系構建參考框架 納入分析的31篇文獻中,12篇(38.7%)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借鑒了一個或多個國外應用廣泛的全科醫生能力模型或框架。其中,最常見的參考模型是世界家庭醫生組織(WONCA)樹模型,有7篇(22.6%)研究在該框架的基礎上建構指標體系。其次為美國畢業后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GME)提出的全科醫生能力框架(3篇,9.7%)和Spencer提出的冰山模型(3篇,9.7%)。其他如澳大利亞皇家全科醫生協會(RACGP)提出的全科醫生能力框架、英國皇家全科醫生學院(RCGP)提出的全科醫生能力框架等僅在1篇研究中被參考(見表3)。其他19篇(61.3%)研究在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沒有明確的參考框架,僅通過文獻綜述或定性訪談等方法總結建立指標體系的維度和條目池。

表3 31篇文獻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構建參考框架Table 3 Frameworks u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on-specific competencies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hinese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the 31 included studies
2.4 中國構建的指標體系內容 納入分析的31篇研究中,有26篇(83.9%)將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以勝任力框架的形式展開,即指標體系分為一級指標、二級指標,甚至三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數最少3個,最多8個;條目(最后分級指標數)最少14個,最多113個。有6篇(19.4%)研究的條目數≤20條,13篇(41.9%)研究條目數21~40條,7篇(22.6%)研究的條目數>40條(見表1)。中國目前構建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一級指標(或維度)是基本醫療服務能力(13次),其次是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能力(11次)和溝通能力(10次)。臨床基本技能、人文執業能力、臨床專業知識、教學能力、基于實踐的學習與提高、團隊合作能力也比較常見,出現頻次均在5次及以上。中國的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與國外5個能力標準既有共通之處,又有所區別,目前國內構建的崗位勝任力標準基本上也涉及其他國家的全科醫生能力標準相關內容(見表4)。

表4 中國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順位前10的指標)與國際其他全科醫生能力標準的比較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on-specific competencies evaluation systems for Chinese general practitioners(the top 10 indicators in terms of frequency)with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3 討論
3.1 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的研究與發展在中國廣受重視,但仍缺乏成熟的崗位勝任力框架 本研究發現,近年來隨著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越來越受到國內業界人士的關注與重視,中國構建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的研究較多,但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因此,探索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成為中國該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此外,目前中國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研究開展較多的地區是上海和江浙一帶。隨著國內全科醫學的飛速發展,各地區發展水平漸顯差異,其中上海、浙江、北京等地區全科醫學發展較快。既往研究發現,第一作者所屬地區發表文獻數量排名前3的地區分別是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39]。各地區不同全科醫學發展水平可能也是目前中國未形成統一實用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框架的一個重要原因。
3.2 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構建方法多樣,且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深受廣大科研人員的青睞本文中納入的研究大部分采用衛生領域的經典勝任力模型構建方法[40],如文獻研究、定性訪談法、Delphi專家咨詢法等。此外,本文納入的文獻多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構建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方法主要是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定性研究(訪談、專家咨詢)的方法,結合全科醫生工作內容和職責特點,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框架,進行專家咨詢與論證,實現框架的層次化、條理化。應用定性訪談法可以收集到第一手資料,所得結果的信度和效度較高。但既往研究發現,單獨采用行為事件訪談法(定性訪談法)建構勝任力模型難以保證嚴格的科學性,所以該研究提出綜合采用多種方法交互驗證,強化問題設計的多角度和針對性[40]。而Delphi法作為指標體系構建的最權威的預測方法[41],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42],指標體系大多是在文獻分析法的基礎上再運用Delphi法構建的,近年來在選題小組法基礎上,進一步采用Delphi法構建指標體系的模式嶄露頭角,此方法克服了Delphi法的某些不足。分析中國2004—2014年的文獻,構建指標體系主要選用的方法以采用Delphi法、Delphi法與層次分析法相結合的方法為主,由此可見Delphi法結合其他方法構建指標體系亦成為趨勢[39]。
3.3 我國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的特點
3.3.1 多指標 本文納入的研究構建的指標體系符合典型的多指標這一特征。對于評價工具而言,條目較多的工具花費時間相對較長而不適用于日常的臨床應用。既往研究發現,大多數應用者不會采用完成時間超過5 min的測量工具[43]。因此,指標構建除了需要考慮指標的全面性[44]外,還要考慮實用性。
3.3.2 內容涵蓋廣泛 我國目前構建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在參考借鑒國外成熟的崗位勝任力框架基礎上,結合中國全科醫學實際發展情況與基層實踐的特點,以崗位勝任力為目標,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評價體系。其中,最常見的勝任力包括基本醫療服務能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能力、溝通能力等。基本符合《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內容與標準(試行)——全科培訓細則》[45]和社區全科醫生崗位內容和管理要求。與國外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框架,如歐洲[3]、美國[4]、英國[5]、澳大利亞[6]、加拿大[7]的全科醫生能力標準相比,由于所針對的對象與提出的機構職能有所不同,中國的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與國外5個能力標準既有共通之處,又有所區別。首先,專業知識與技能、醫患溝通能力、職業素養這3項能力都受到了重視,這是國內外為應對“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新模式的挑戰而做出的共同選擇。其次,我國尚未出臺正式的全科醫生能力標準,但目前構建的崗位勝任力標準基本涉及了其他國家的能力標準內容,同時,結合中國全科醫生在社區還需承擔一定的公共衛生方面的工作,中國的全科醫生勝任力指標體系還著重強調了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能力。
3.3.3 缺乏實證檢驗 目前國內開展了大量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評價指標構建的研究,但大多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科學的實證檢驗。本研究納入分析的研究中,僅6篇研究驗證了指標體系的信度和效度。工具的質量評價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諸多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衡量測量質量的標準包括精確度、準確度、信度、效度。其中,信度和效度測驗是多數實證研究中,對一次特定測驗的可靠性、有效性的說明[46]。
3.3.4 未形成較為系統、實用的勝任力評價方式 在英國,RCGP總結了全科醫生必須具備的13項核心崗位勝任力,并制定出具體的評價方法,即360度評價、患者滿意調查、問診觀察、病例討論、迷你臨床演練、臨床帶教老師評估[5,47]。美國畢業后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提出醫師需具備6項勝任力,并開發和實施各專科基于勝任力住院醫師教育評價框(Milestones),其評估方式包括檢查醫療清單、標準化病人考試、360度評價、學習檔案記錄檢查等[4]。中國自2011年開始將全科醫生培養制度統一規范為“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臨床醫學(含中醫學)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對于規范化培訓結束的學員進行考核的方式主要是規培結業考核(科室輪轉手冊檢查,臨床知識書面考核和技能考核)。對于培訓合格后的全科醫生是否能夠勝任全科崗位,目前還沒有相應的統一的考評方式給予反饋。
綜上,本研究系統綜述了目前國內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構建研究,發現目前中國學術界和相關組織圍繞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大多研究僅止步于指標體系的構建,缺乏科學的實證檢驗,實際應用仍乏善可陳。全科醫生勝任力評價的研究仍需不斷深化和完善。在指標構建過程中,充分考慮全面性、實用性、導向性、獨立性等原則。制定出實用的勝任力評價方式同樣是中國今后繼續開展全科醫生勝任力評價研究重點。因此,未來的研究可致力于指標體系的實際應用方面,以此構建科學的、系統的、具有實踐意義的全科醫生崗位勝任力指標體系,用于中國基層全科醫生的崗位勝任力評估。
作者貢獻:魏云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結果的分析與解釋、論文撰寫;路孝琴負責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論文的修訂、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魏云、王飛躍負責數據收集;魏云、潘朝路負責數據整理;魏云、王美榮負責統計學處理;金光輝負責英文的修訂。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