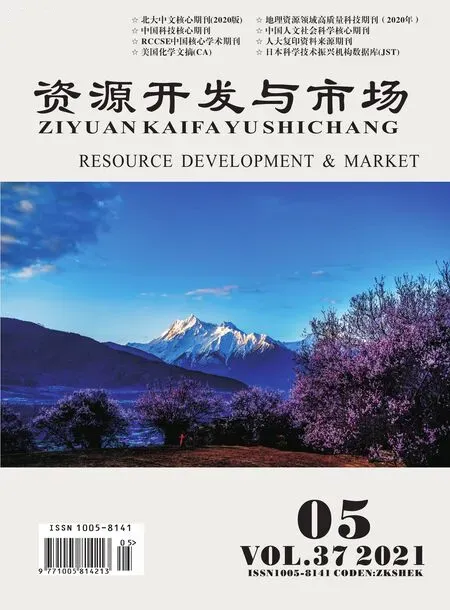美國雙向投資時空演變及其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分析
周 鴻,陳 瑛,齊 慧
(陜西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710119)
美國是當今世界吸收外商投資(I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最大的國家。美國IFDI和OFDI流動對全球生產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具有重要影響,對其進行研究有助于探尋均衡全球投資格局和經濟協調發展的途徑。國外關于美國FDI 的研究角度較多,主要集中在3 個方面:①影響美國雙向投資的因素。Aristotelous K研究了歐洲貨幣聯盟對美國OFDI進入歐盟的影響[1];Cavallari L等研究了產出波動和匯率波動對推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等[2-5]。②美國對外投資產生的影響。Ntembe A 等利用1996—2013 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美國投資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14 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6];Axarloglou K L 等分析了FDI 流入對美國各州的影響等[7-10]。③美國吸收外投資風險分析。Click R W分析了美國在59 個東道國進行直接外國投資的風險[11];Lektzian D等首次研究了美國制裁對全球直接投資的影響等[12-15]。國內關于對美國FDI 的研究相對較少,多側重于以下方面:①研究美國FDI現狀特征及對中國的啟示。張曉平和陸大道等分析了美國OFDI的行業結構及世界范圍內地區結構的變化等[16-18]。②影響美國FDI 的因素。葛振宇等利用向量誤差修正等模型考察中國對美投資的影響因素[19];楊珍增等基于地理距離研究其對美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規模和投資動機進行分析等[20-26]。
本文將分析美國雙向投資在全球的時空演變規律和空間集聚特征,對比美國對不同類型國家之間投資驅動影響因素,以期為我國吸引美國投資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根據已有的數據投資特點,將美國雙向投資分為北美地區、歐洲地區、拉美和部分西半球國家、非洲地區、中東地區、亞太地區六大區域。由于不同國家(地區)與美國之間的相互投資開始時間不同、數據詳實程度不一,考慮到數據的可比較性,本文選取1990—2019 年為研究期,對美國在全球主要國家的投資流動情況進行詳細分析。其中,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的投資進程和內涵與大陸相差較大,因此未將這3 個區域與美國的投資互動并入計算,此部分數據來自于美國經濟分析局和聯合國貿發會議。
1.2 空間自相關
全局空間自相關:在分析某一要素在整體研究區空間上的相互關系時,通常采用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I)表 示。Global Moran′I ∈[- 1,1]。Global Moran′I∈(0,1],表示存在空間正相關;Global Moran′I ∈[- 1,0),表 示 存 在 空 間 負 相 關。Global Moran′I=0,表明不存在相關性[27]。計算公式為:


局部空間自相關:全局自相關無法衡量“局部”區域的異質性,進一步使用局部自相關方法進行測量。采用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I)表示,結果用Lisa散點圖進行可視化展現。計算公式為:

式中,Li為Local Moran′I;其他變量解釋同式1。Lisa散點圖利用計算處理后的屬性值及其平均值構成的4 個象限表示局部空間相關的類型,即第一象限H—H(高值集聚)、第二象限H—L(高值包圍低值異常區)、第三象限L—L(低值集聚)、第四象限L—H(低值包圍高值異常區)[27-30]。
1.3 美國OFDI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美國OFDI 在全球的分布特征,北美地區僅加拿大一個發達國家,而與歐洲地區投資互動的國家多為發達國家,因此在歐洲選擇吸收和對美投資規模較大的英國與北美地區的加拿大來比較美國對不同發達國家投資考量因素的差別。拉美和西半球部分國家區域幾乎全是發展中國家,巴西是該區域最大發展中經濟體;亞太地區除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之外,發展中國家是主體。中國是亞太地區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在世界投資格局中地位不斷上升,是美國重要的國際合作伙伴,將其與巴西進行對比,既可以找到兩國吸收美國投資驅動因素的異同,又可為中國發展投資提供經驗或教訓。中國和巴西具有廣闊的市場和較為豐富的資源等相似的投資因素構成,因此分別選擇中國和巴西作為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影響因素分析的研究對象。美國與非洲、中東地區的投資互動均較少,相關國家所處區位多為資源豐富、政治局勢較不安定地區,因此在這兩個區域分別選擇與美國投資互動較大、綜合實力較好且數據較齊全的尼日尼亞和科威特作為美國對資源豐富國家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此,選取的樣本國家為加拿大、英國、中國、巴西、尼日利亞、科威特6 個國家,結合相關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參考已有對美國OFDI 影響因素成果,基于對美國與各國的經濟數據定性分析,同時考慮相關數據可獲取性及可比較性等原則,截取1998—2016 年相關經濟數據分析美國在這3 種不同類型國家投資驅動因素的異同,選取本文的因變量和自變量及數據來源(表1)。

表1 變量及數據來源
本文借助EVIEWS 8.0 軟件,利用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分析,參考已有的面板模型[31-35],建立本文研究基礎模型:

式中,FDIi,t為美國在t年對i國的投資額OFDI,或美國在t 年吸收來自i 國的投資額IFDI;Xi,t為影響美國、中國等6 國投資互動的系列因素,有市場規模(GDP)等。α為常數;β為待定系數;λ為調整系數;ξi為個體效應;εi,t為擾動項。將解釋變量全部加入基本模型中得到完整模型:

為檢驗美國分別對六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建立時間序列模型:

式中,各變量解釋同式(3)。
2 美國IFDI和OFDI的時空演變
2.1 美國IFDI和OFDI概況
1990年以來,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吸收的投資呈持續上升的態勢。1990—1998 年,美國IFDI 存量逐年平穩增長,此后亞洲經濟危機、美國“911 事件”使亞洲地區對美投資大量減少,加之政治環境的影響,導致美國吸收的投資減少。2002 年后,美國所獲世界的IFDI又勻速增長。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世界,此后美國政府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吸引外資。總體看,1990 年以來美國29 年間保持著約9%的速度穩步上升。美國IFDI 存量占全球IFDI 存量的比值波動較大,由1990 年一直上升到1999 年。2002年起隨著世界經濟形勢好轉,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吸引了較多的全球投資流入,美國IFDI 存量占比開始持續下降,后隨著開放的投資政策出臺,吸收外資迅速增多,占比逐年增長。美國IFDI 流量占全球IFDI流量的比值波動相對較小,且與世界形勢和美國國內局勢較為吻合(圖1)。

圖1 1990—2019 年美國外商直接資的流量和存量及占比變化
美國OFDI 存量總體保持上升的趨勢,但波動較大。1990—1999 年美國對外投資存量以年均15%的速度保持增長,此后三年受限于全球投資低迷,美國向外投資也有所減少。之后五年,美國對外投資額持續上升,除2008 年受經濟形勢影響降低些許,直至2019 年呈波動上升趨勢。美國OFDI 流量則自1990 年起保持10%左右的速度增加。1990—1999 年,美國OFDI存量占全球OFDI 的存量比重波動較為平緩,1999 年至峰值后波動下降,到2008 年降至最低值26%,之后一直保持在30%左右波動。美國OFDI流量占全球OFDI 流量的比值波動較為平穩,一直在18.6%附近上下波動(圖2)。
2.2 美國雙向投資時空格局分析
本文以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2019 年4 個時間節點為例,對美國在全球主要國家的投資流動情況進行詳細分析。截至2019 年,美國IFDI的來源國遍及全球大部分國家。就六大區域而言,歐洲地區成為美國外資流入的主要來源地區;其次是亞太地區國家,接著是北美地區、拉美和部分西半球國家。相對而言,雖然非洲和中東地區對美國IFDI 的總量在上升,但占比非常小,六大區域對美投資額均在不斷上升,但投資增速有所差異。就全球層面來說,投資來源地有向全球范圍擴散的趨勢,亞太地區地位有上升的跡象(表2)。

圖2 1990—2019 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及占比變化

表2 美國吸收六大區域投資的數額及占比變化
美國IFDI來源區域基本穩定,空間分布呈現顯著的地域集中性。1990—2019 年,美國IFDI 來源地覆蓋范圍越來越廣,但基本格局保持穩定。其中,歐洲地區是最大的美國IFDI 來源地區且上漲幅度和速度均較大,具有明顯的地域集中性特征;其次是亞太地區,從2000 年起份額持續上升,有望成為美國IFDI來源國新的增長區域;北美地區落后于亞太地區成為全球第三大對美投資區域;拉美和部分西半球國家區域對美投資波動較大,份額相對較小;非洲和中東地區對美投資較少,上漲緩慢且占比較小,與其他區域的相對和絕對差異都在擴大(圖3)。

圖3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2019 年美國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空間分布
截至2019 年,美國對歐洲地區的投資最多,占美國OFDI總額的比值持續增長;對拉美地區和西半球部分國家的投資額總體上大于亞太地區;對北美地區的投資排名第四位,且持續下降;對非洲和中東地區投資趨勢大致相同,占比均不足 1%。1990—2019 年,美國OFDI 總體增幅較小,但對外投資范圍在不斷擴大,且有向已有投資地不斷深化的趨勢(表3)。
美國OFDI在全球重心穩定,空間分布不均衡。美國OFDI的空間非均衡特征顯著,歐洲地區占據著核心地位,亞太、北美和拉美等地區處于次中心地位,非洲和中東地區處于邊緣地位。美國對全球六大區域投資格局變化較大,除歐洲外的其他各區域都有一定的交叉變動,歐洲地區一直保持排名第一,是美國對外投資空間分布的顯著集聚區(圖4)。

表3 美國對六大區域投資的數額及占比變化

圖4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9 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空間分布
2.3 美國IFDI和OFDI的空間關聯特征
結合全局自相關公式,利用Geoda 軟件計算美國IFDI和OFDI的全局Moran′s I。結果顯示,1990—2019年美國IFDI 莫蘭指數平均值未超過0.3 但是在波動增大,而美國OFDI 全局莫蘭指數呈波動上升的趨勢但也未超過0.5,因此美國IFDI 來源地和OFDI目的地均存在一定的空間關聯性,但全局相關性不強(表4)。
為更準確地反映美國IFDI 來源國和美國OFDI目的地的空間分布在局部的差異變化及與鄰近國家的相似情況,結合公(3)—(5),利用Geoda 軟件繪制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2019 年美國雙向投資的LISA散點圖(圖5)進行局部自相關分析。觀察1990年、2000 年、2010 年與2019 年美國IFDI 莫蘭散點圖,發現美國IFDI 來源國多屬于H—H 和L—L 類型,表明美國IFDI來源國空間分布存在正向空間自相關作用。1990 年與2000 年,對美投資的國家均屬于H—H 類型的有德國、荷蘭、比利時,說明這些國家對美國投資較多,同時帶動周邊國家向美國投資;L—L類型主要有尼日爾、阿根廷、貝寧、中國、朝鮮等50 多個國家,主要分布在南美洲西部、東非和整個亞洲區域。2010 年與2019 年,愛爾蘭、法國、英國、意大利等進入H—H類型區,這些國家多位于德國、荷蘭、比利時周邊,受周圍國家空間集聚效應和已有投資路徑依賴作用的影響,形成了高值集聚區;而L—L 類型整體投資較少型國家增加至80 多個,主要分布范圍擴展至整個非洲、南亞和東南亞島國和南美洲地區,但部分國家脫離了低值集聚區,如中國、韓國進入H—L類型。

表4 1990—2019年美國雙向投資全局自相關指數
1990 年與2000 年,美國投資的國家均屬于H—H類型的國家有愛爾蘭、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等國,主要位于西歐和中歐地區,而均為L—L類型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中國等40 多個國家,主要分布于非洲(北非和東非)、中西亞地區和南美部分地區,反映出美國對這些地區及周邊國家投資較少。2010 年與2019 年,瑞士退出H—H集聚類型,同時英國和挪威加入H—H類型,反映出美國對英國及鄰國愛爾蘭和對挪威及鄰國瑞典的投資快速增長;而L—L類型國家地區分布變動不大,但是分布區域更廣,主要位于非洲(北非、東非、南非)、中西亞及東南亞島國和南美洲部分區域,這與美國對這些地區投資整體規模不大且增長較少有關;H—L類型加入了中國、巴西、韓國3 國,說明與鄰國相比,美國進一步加大了對這3 國的投資(圖6)。

圖5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9 年美國IFDI莫蘭散點圖
觀察美國OFDI莫蘭散點圖,發現美國OFDI 國家也多屬于H—H和L—L類型,顯示出美國投資目的地空間分布的關聯性。

圖6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9 年美國OFDI莫蘭散點圖
3 美國OFDI影響因素分析
3.1 美國OFDI影響因素總體分析
本文利用廣義矩估計回歸對美國向巴西等6 國投資的影響因素總體進行了分析(表5)。從表5 可見,Sargan檢驗和AR 序列相關性檢驗均通過,因此模型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有效且殘差序列間不相關,模型設定及結果合理,可用于后續分析。

表5 美國對六國投資影響因素GMM 估計結果
從表5 可見,中國等6 國的GDP、實際有效匯率、金屬和礦產資源、貿易出口額、技術水平、勞動力工資水平、勞動力質量、政治穩定對美國OFDI 的進入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市場規模、自然資源豐裕度、貿易開放度、勞動力質量、政治穩定程度與美國OFDI呈正相關;匯率和暴力沖突等與美國OFDI 呈負相關,集聚效應并不顯著,說明其對外投資的國別選擇范圍越來越廣泛,且所選國家中科威特和尼日利亞目前吸收美國投資規模較小,具有一定隨機性,因此集聚效應不顯著;通貨膨脹率與被解釋變量呈負相關關系,說明各國宏觀通脹率的上升引起美國企業跨國投資下降,但該解釋變量并不顯著;失業率的相關系數極小且不顯著,說明用失業率來衡量經濟風險因素有所不足。燃料出口占總出口額對美國外資進入有正向影響,但相較于礦石和金屬出口額這個指標,影響較小且作用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美國在所選取的6 個國家進行的投資類型不一和各個國家的區位優勢差異造成了此影響因素不顯著。基礎設施水平用互聯網普及率進行表征,結果顯示其與各國吸收的美國FDI 呈正相關,也表明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是重要的引資優勢之一,但并未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可能原因是所選取的這幾個國家互聯網普及率相對較好,未能體現出對美國OFDI的影響。
3.2 美國對六國投資影響因素對比分析
基于篩選剔除后的變量,利用逐步回歸法對美國對巴西等六國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美國對六國投資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加拿大和英國:影響美國對英國和加拿大投資的共同因素有集聚效應、市場、貿易開放、實際有效匯率和通貨膨脹率。加拿大和英國作為先進發達國家,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美國對其投資回報率相對較高,因此進一步的投資會存在集聚效應。從數值來看,對英國的集聚效應比對加拿大強,這是由于加拿大占美國對外投資占比有所下降造成,市場規模上升帶來的美資流入差異也是類似原因造成。實際有效匯率、貿易開放和通脹率吸收美資的增減都符合其與FDI的關系,而加拿大的勞動力工資、基礎設施和燃料、礦石等基礎設施與英國的內部沖突、技術水平和勞動力質量是各自不同的影響因素。可能是由于加拿大自身存在較豐富的資源,但對美國有著獨特的貿易“劣勢”,也可能是美國通過貿易獲取資源成本更低所致。而英國與美國可能開展的國際合作技術要求較高,因此對技術水平和勞動力質量更為重視。
巴西和中國:巴西和中國分別為美國對亞太地區、拉美及部分西半球國家投資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影響因素有基礎設施建設和自然資源稟賦,說明兩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都還有上升的空間,對吸引美國投資產生促進作用,且兩國的政治環境均引起美國投資較為強烈的反應。而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利潤較大、總體政治經濟環境較好,因此存在集聚效應。巴西的市場規模、貿易開放度、技術水平是其單獨的影響因素,國際綜合實力相對較中國較弱,因此技術水平的提高才能滿足美國跨國公司相應的要求,從而吸收的投資額會增加。
尼日利亞和科威特:自然資源和政治環境是兩國吸收美資共同的影響因素,兩個國家均位于沖突較多的地區,其政治穩定性也受到更大范圍局勢的沖擊,對美資流入產生負面效應。科威特不同的因素在于通脹率、貿易開放和勞動力質量。科威特地區發展較早,高等院校入學率高于尼日利亞,可能達到對美資進入產生影響的閾值。科威特的資源出口額占其國內GDP比值較大,也有可能吸引美國的投資。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基于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和演化理論,對全國在全球范圍內的投資互動狀況進行了闡述,探究了美國IFDI和OFDI的時空演變和空間集聚特征,參考已有研究,并結合中國與巴西、英國與加拿大、尼日尼亞與科威特為研究對象,測量美國對6 國投資的影響因素因素,并比較影響因素的異同。主要結論如下:①美國IFDI和OFDI發展迅速,但在全球地區間空間分布差異極大。美國IFDI 來源區域基本穩定,空間分布呈現顯著的地域集中性;美國OFDI在全球重心穩定,但空間分布不均衡。②美國IFDI和OFDI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定集聚規模,但集聚效應較弱,從局部地區來看,西歐地區是美國IFDI的重要來源地和OFDI 的主要目的地集聚多以非洲地區形成的L—L 類型和歐洲地區的H—H 類型為主。③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較為多樣,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市場規模、實際有效匯率、集聚效應、貿易開放和通貨膨脹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基礎設施建設和自然資源稟賦是其共同的作用因素;而對資源型國家進行投資時自然資源和政治環境是影響美國OFDI 的因素,各個國家其他的各種投資誘發要素構成的不同,也使其吸收的美國OFDI各有差異。
4.2 討論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由于數據獲取的局限性,對影響因素的探究還不夠全面;二是分析的是全球范圍,沒有在國家層面進行探討,也未對重點區域進行詳細的研究,因此后續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