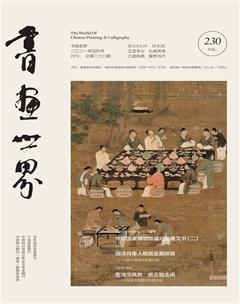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吐魯番文書(二)
孟瀟碧



吐魯番地處新疆中部,自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便成為由內地前往中亞、歐洲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域重要的政治、軍事、文化及經濟中心。唐太宗于貞觀十四年(640)平定高昌,置西、庭二州,同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顯慶三年(658),安西都護府西遷龜茲,西州改置都督府,在此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制度,自此吐魯番地區和中原的關系更為密切,遺留了豐富的文物。
吐魯番地區深處內陸,遠離海洋,降水稀少,氣候極度干燥。吐魯番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使文物不易腐爛,加上地處邊陲,人為破壞相對較少,留下了大量石窟建筑、古城遺址和古代墓葬,保留下來大量珍貴的古代文獻。
吐魯番出土的文書數量相當龐大,跨越時間長,可據其了解中古時期西北地區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教育等各方面情況。此外,這些文書書體豐富,書風復雜,成為書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填補了書法史上的某些空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此四件文書為西北考察團于1928至1930年在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所得,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內容為當地主事官員對于文書事宜的復文。根據同批出土的開元十三年(725)征物殘牒及對文書批示的官員判斷,該批文書應皆為唐開元年間文書,雖大多殘缺,但是也可以據其了解其時官制、公文處理程式及書法風貌。
一、張元璋殘牒(一)
殘紙,出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縱14.7厘米,橫42.6厘米,上下殘缺。此文書與本輯《吐魯番文書(一)》中的開元十三年征物牒大小相若、字體類似,應為同一時期文書。
牒文二行,文曰:“判稽違不上事目如前/年十二月日典張元璋牒。”
批示八行, 文曰“ 兩道放至/ □(暉)道已上/下濟示/二日”“到情亦可/□(放)卻少間/了□決/□(晚)濟□二日”。
牒文楷書,晉唐小楷風格,略有寫經遺意,正是下層文吏書風。批示行草書,運筆嫻熟、率意,不乏六朝遺意,然而技法不重細節,亦是典型唐代文吏書風。如“已”“上”“濟”“示”等字,運筆中側互用,與“二王”一脈行草書相承。像“亦可”,草法至簡,全用中鋒,是唐人的風格;像“到”字右部鋪毫重按,與顏真卿書風一致,正是盛、中唐時期的時代特征。像兩個“道”字、“情”字,均有筆畫承接時未能充分調鋒的技術缺陷,“放”字末筆翻轉時力不從心,即是民間書法與經典法書的差距。然而唐人殘紙,率皆筆致渾厚,如“印印泥”,字間露出一種自信高邁、大氣流轉的感覺,彌足珍貴。
二、張元璋殘牒(二)
殘紙,出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縱14.9厘米,橫19.2厘米,上部殘缺。
牒文四行,文曰:“應須行下任便處分牒/錄白施行謹牒/二月九日典張元璋牒/判官倉曹李。”
批示一行,文曰:“□廣濟示。”
文書中的廣濟與張元璋殘牒(一)及開元十三年征物牒、府司阿梁狀詞并批中的濟應皆為一人,黃文弼先生在《吐魯番考古記》中分析,濟或廣濟“為通判諸曹之高級官員,疑為長史、別駕之屬也”[1]。李方先生在《唐西州長官編年考證—西州官吏考證》中進一步考證,廣濟應為開元十三年左右西州都督府都督。參曹參軍李為判官,廣濟只能是高于判官的官員,通判官署名前加“諮”字,廣濟署名前未加“諮”字。在府司阿梁狀詞并批文書中,廣濟在狀詞后首先署名,符合長官首先署名的程序,而且“諸如小事,便即與奪訖申”,像這種小事應直接處理完畢后再申報即可,一副訓斥下官口吻,可見廣濟即為時任都督府長官。
牒文行楷書,書寫者晉唐小楷基礎扎實,行書字法與《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相近,似亦多少有點歐陽詢行書的影子,想必也是當時流行的書法風貌。雖然不能肯定書寫者學過名家字帖,但他應當受過良好的書法教育。
批示中的“示”字,字法與王羲之尺牘中“示”字基本一致;另一張張元璋殘牒(一)中的“示”字更像王羲之的,此略加楷化。“廣濟”二字,用筆沉實,結體雍容,與顏真卿行書幾無二致。
如前文分析,本文書為開元十三年左右的文書。顏真卿生于景龍三年(709),開元元年為公元713年,其時顏真卿也就十幾歲。也就是說,殘紙作者絕無學習顏真卿書法可能。由此可見,顏真卿行書的基本面貌,為當時所流行。顏真卿化俗為雅,點石成金,能于“二王”之外別樹一幟,正所謂“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三、府司阿梁狀詞并批
殘紙,出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高28.7厘米,寬35.9厘米,中部殘缺。
狀詞四行,文曰:“府司阿梁前件萄為男先安西鎮家無手力去春租/與彼城人卜安寶佃準契合依時覆蓋如法其人至今/不共覆蓋今見寒凍婦人既被下脫情將不伏請乞商/量處分謹辭。”
批示五行,文曰:“付識□□勒藏/蓋□□重□/諸如小事便即/與奪(按:黃文弼先生《吐魯番考古記》釋為‘曹辦,不確,此為‘奪字)訖申濟/示十三日。”
此狀所陳,大抵為卜安寶租種別人土地,但是沒有按照契約“依時覆蓋”,致使葡萄“今見寒凍”,阿梁被下脫(欺騙),期望“商量處分”,“濟”在批示中說:“諸如小事,便即與奪訖申。”也就是說,像這樣的小事,你們自行處理,處理完了報告一下就行了,最終判決勒令卜安寶藏蓋葡萄。
葡萄在唐代吐魯番地區已經廣泛種植,并可以制作成葡萄干、葡萄酒,在出土文書中可以看到關于葡萄種植、管理的相關記錄。如《武周圣歷元年(698)前官史玄政牒為四角官葡已役未役人夫及車牛事》[2]載:
四角陶所
合陶內抽枝、覆蓋、踏漿并收拾□枝、埋柱等總料得夫玖
后略。
其中,“抽枝”“覆蓋”“收拾□枝”“埋柱”應為葡萄種植的措施,“踏漿”為葡萄酒制作之步驟。“覆蓋”應該是北方嚴寒地區葡萄種植的一項措施,西州地區冬季嚴寒,采取這種措施十分必要。
此狀書法風格與張元璋殘牒顯然有差距,狀詞楷書,筆致單調,結體未穩;批示書法,用筆沉酣,使轉自如,字不經意,而動靜相生,奇趣撲面;整體神采奕奕,不減齊梁名家。率爾書寫的批示,竟能如此精彩,這也說明較高層的官吏有良好的書法修養。當然,也正因為率爾批示,意不在字,反而能天真爛漫;反之,一矜持便落下乘矣。
四、虞候司及法曹司請料紙牒
殘紙,出吐魯番哈拉和卓舊城,高29.1厘米,寬141.8厘米,共33行。首為虞候司請六月料紙事,前有殘缺,次為法曹司請黃紙事,文尚完具。
文云:
史/六月八日受即日行判/錄事使/錄事參軍自判/案為虞候司請六月料紙事
法曹/黃紙拾伍張,壹拾伍張典李義領/右請上件黃紙寫,敕行下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開元十六年六月 日府李義牒/法曹參軍王仙高
付司楚珪□(△)/九日
六月九日錄事使/錄事參軍沙妻付/檢案
沙白/九日
牒檢案連如前謹牒/六月 日史李藝牒/
法曹司請黃紙準數分/付□(長?)領沙妻白/九日
依判諮希望示/九日
依判諮□□(球之)示/九日
依判楚珪□(△)/九日
開元十六年六月九日/史李藝/錄事參軍沙妻/史/六月九日受即日行判
此殘件分別為虞候司、法曹司申領料紙、黃紙之牒文,因屬于同類文書,“牒檢案連如前”(“連”是牒文處理的一種臨時措施,即把同類的牒文粘連起來,留待以后一并加以處理的方法)[3],被粘連在一起。其中法曹司請料紙牒較為完整,可以推知文書處理之程序。唐代實行四等官制,四等官自上而下依次是長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四等官制之外,還設置了勾檢官,掌勾檢稽失、省署抄目等。[4]每一個案件一般需要四等官連署意見,各級官員都參與案件的審理,各司其職、互相監督,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錯判、誤判的可能,保證了案件審判的公正和有效率。
西州其時為中都督府,長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對應的分別為都督,別駕、長史,六曹參軍及領取紙筆時的錄事參軍,典、史、佐等。以法曹司請料紙牒為例,法曹司請黃紙牒文到都督府后,首先由長官楚珪簽署“付司”,再由判官錄事參軍沙妻受付并鈐印,向主典李義下達檢案的指示,主典李義做出牒檢案連如前的回復,判官沙妻簽署初步審判意見,通判官球之、希望簽署“依判”,諮請長官最后定奪,長官簽署最終意見“依判”。最后再由勾官沙妻勾檢,“受即日行判”,即在受理案件的當天就完成了公文的流程,體現了很高的工作效率。
沙妻在本案中既是判官,也是勾檢官,在其余申請紙筆的文書中也有類似的情況。錄事參軍管紙筆,這種案件一般由錄事參軍自判。
以書法的眼光看,此件殘紙的主體,為“李義”“沙妻”二人所書。虞候司及法曹司請料紙牒“牒檢案連如前謹牒/六月日吏李藝牒”,“法曹/黃紙十五張”“右請上件黃紙寫,敕行下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開元十六年六月日府李義牒/法曹參軍王仙高”應為李義所書,“法曹參軍王仙高”按理應為王仙高具署,但其風格,與上述“李義”高度一致。考慮到法曹參軍為法曹長官,署名似乎不會如此局促整飭,所以,這一行字也應是上述“李義”所書。李義楷法嫻熟,與顏真卿楷書《多寶塔碑》風格近似,早于《多寶塔碑》數十年,應為當時流行的楷書風格。唐人楷書,初唐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類皆瘦削,高層文人所書碑志,多有規仿歐、褚書風者。但是在民間,寫經體的大眾化,并不受歐、褚籠罩。盛唐社會風氣逐步轉變,趨于尚肥。所以,稍后中唐出現顏真卿的楷書,也是審美流變的自然結果。
虞候司及法曹司請料紙牒除李義署名部分,受付部分“六月九日錄事使/錄事參軍沙妻付/檢案沙白/九日”及判詞部分“法曹司請黃紙準數分/付□領諮沙妻白/九日”,應為沙妻所書。其書點畫圓潤,行筆流暢,而骨力勁挺;結體以瘦峻為主,中宮緊收,然而時有長筆畫呈輻射狀,提振精神;氣息上率性自由,力量感十足,體現了唐人特有的自信張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結構方法,似與歐體有某種承接,但與初唐書風并不一致,也與稍后的顏體迥然不同,倒是與《張猛龍碑》等斜畫緊結一路魏碑暗合。同時,這一現象也說明,晚唐柳公權的楷書結構方法,除來源于歐、顏,也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這種自由自在、不驕不矜、深沉樸茂的書風,值得當代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