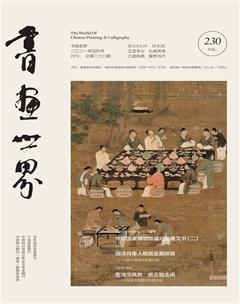洗盡鉛華無意歸真
呂永生



曹元偉,書法界的名人,名人中的辛勤勞動者。剛剛步入“花甲”之年的曹元偉,被譽為“書壇常青樹”。其書作或小品,或巨幅,或冊頁、手卷,俱筆精墨妙,古意盎然,栩栩而富生氣。其書作與主題、落款與字形、內容與形式等,俱為和諧,不溫不火,而風規自遠。其書法線條語言的表達,不鑿本源之真,無傷自然之神。夫唯胸滌塵埃,氣消煙火,境界因古雅而成。舒舒之容,令觀者飄飄然而有霞舉之思;落落清姿,令觀者曠曠然而生宋元之想。思隨書遷,蓋因性情入妙,筆墨巧拙兼奪。氣韻生動之勃勃,骨法洞達之歷歷。綜以觀之,其書法所蘊含的藝術修養或宏觀或微觀,淺述如次。
一、承貝爾“形式論”的妙趣而溢
曹元偉書作承襲了“ 有意味的形式”。英國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于《藝術》一書中提出:藝術本體在于“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指不同于日常情感體驗的一種高尚且特殊的、排斥現實生活中諸類考慮的“審美感情”。“有意味的形式”是能夠引起人們審美情感的、以獨特形式組合的線條、色彩等特殊的形式關系,包括“審美的、感人的”“激發審美情感的意味與形式或形式間的關系”等兩個方面。克萊夫·貝爾認為這種形式既能讓我們了解客觀實物,又創造了審美感情。它是創作主體自我審美情感的呈現和主觀創造,是獨立于外部實物的一種嶄新的、精神性的現實。它可傳達創作主體的情感,是區別藝術品和非藝術品的“最基本的性質”,審美活動及審美經驗是對這種“有意味的形式”的審美觀照。曹元偉書法作品的形式基于“有意味的形式”,無論承趙孟之秀美還是沿米芾之率真,形式感皆具鮮明與獨特的表達,或條幅或斗方,或小品或橫幅,其形式感撲面而來,令人愉悅又令人凝思。那種享受的快感立馬能激起你對其作品的回味與反復品讀。
2021年元旦,曹元偉舉辦小品、小字新作微展,其作品形式獨特,以小見大,面目煥然一新。微展中的15幅小品,幅幅形式各異,無論小條幅還是小橫幅,皆令人震撼,亦讓人如癡如醉。如小品行草條幅之一,縱七行豎寫,后三行兼落款長短不一,“元偉并書”與三小印成一行,“謹記之”三字居上而前呼后應,“敏行堂硯邊卮言三則”九字緊靠“謹記之”而下,使整幅作品的左下角呈現出強烈的空靈感。曹元偉蓋章也很有思想,此作中的三方小印,大小、距離、朱白文等非常講究。總之,線條與線條之間、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的特殊安排,給人的感覺是清秀、輕松、恬靜。又,“謹”字與“偉”字的字形端莊、雄偉、夸張,能喚起人們崇敬的心情,可喚起人們對書法美好的憧憬,使人感到有一股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線條大膽潑辣,行筆跳躍性大,特別強調各種對比手法,以奇取勝,使人有巧奪天工之妙感。
賞析曹元偉行草條幅“有意味的形式”,會感受到《易經》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境界,使人感覺到這種線條的組合有音樂般的律動,每個字和整幅作品都轉化為鮮活的生命。筆法方中參圓,簡中寓繁,充滿耐人尋味的筆墨意趣。律動的是觀者的靈魂,靈魂深處正是形式感的意味。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云:“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深乎風者,述情必顯。”眾目昭彰,內心的感受,蓋須通過洗練的形式表達出來。當然,“有意味的形式”是依附于豐富而生動的筆墨語言的。
二、奇妙而生動的藝術語言
書法作品的特定主題,必須借助一定的、豐富的藝術語言,才能表現及物化為可供人們欣賞的藝術對象。沒有藝術語言的充分表達,也就沒有書法藝術作品的存在。在長期的發展中,各種門類的藝術都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藝術語言。藝術語言是指創作主體在藝術創作活動中,以別具一格的客體材料為媒介,按照美的規律、特點等進行藝術表達的手段和方法,是作品外表的形式和內在的獨特結構。藝術作品的特定內容必須借特定的藝術語言方可呈現,成為人們觀摩與鑒賞的對象。可謂沒有優秀的藝術語言,就不可能產生優秀的藝術作品。各門類藝術伴隨著自身的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而與眾不同的藝術語言。如繪畫以線條、色彩、色調等為藝術語言,書法的藝術語言則為筆法、字法、章法、墨法、飛白等。當然,探析曹元偉書法的藝術語言亦是如此。
(一)筆法:內含筋骨、外耀鋒芒
所謂筆法,簡而言之,就是用筆的基本方法。元代趙孟曰:“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曹元偉繼承了“二王”、米芾、趙孟等人筆法的同時,善于限控與駕馭毛筆的指、使、轉、用,其命脈是中側兼用,寫出符合書法專業技巧所要求的點畫與線條的質量。“錐畫沙”“屋漏痕”“印印泥”等書法專業術語統統聚集于曹元偉的筆端,能夠充分體現出曹元偉書寫時的筆勢及線條的力量感。雖然書法作品屬靜止的藝術形象,很難從作品中觀察到書寫時毛筆的運動感,但在曹元偉創作時,毛筆運動變化的軌跡仍然遺留在點畫的形狀上。所以觀賞者在欣賞時,要從其書法作品中點畫形狀的變化中想象出毛筆運行的動作以及點畫內部所蘊含的運動筆觸。唐孫過庭《書譜》曰:“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曹元偉亦然,一畫之間筆法微妙,同時又隱含于點畫的內部,難以預測運筆的軌跡。曹元偉運筆方圓兼備,藏露互見,中側互換,貌似側鋒居多且變化十分豐富。
曹元偉書法運筆中側兼施,筆勢勁健,如斬釘截鐵,十分利落,但又不失通過擦、揉而產生的毛澀感。那局促而明快的筆意造就呈向右上聳肩之斜勢,似乎亦受蘇東坡左枯而右澀的結體影響,產生了緊峭與奇譎的視覺效果與外在的形式感。就使轉而言,轉折處多以方取奇,隨意頓挫,不乏圭角,與六朝墓志方筆所呈現的天然之態相吻合。枯筆澀行可謂曹元偉的獨特風格。枯筆線條,任其自然,常于字組中由濃至枯,產生勝似飛白的效果,于強烈的節奏中富于沉著痛快的旋律。間或用顫筆。運筆時墨色已枯,繼續澀行,顫筆的痕跡歷歷可見。這種顫筆的效果不僅毫不減弱字的氣勢與形式感,相反還增加了蒼茫與渾厚感。
(二)字法:欹側相間、以險寓正
所謂字法,即是漢字結體的方法。唐孫過庭《書譜》曰:“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這句話蘊含著濃厚的哲學思想,亦吻合儒、道“中庸”與“陰陽”對立統一的藝術特征。我們從中可以領悟結字的法則和規律。曹元偉書法的結體運用易學“九宮”八卦之象,將結字的“中宮”緊收,重心偏下或偏上,常將字形縱向拉長。蔡邕《筆論》云:“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失,若水火,若云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曹元偉的字法仿佛亦受蔡邕此則書論的強烈影響,其結體活潑多變,形象生動。
然而,相對點畫而言,曹元偉書法單字的結體是一個組合,也是一個整體。結構方法有主觀處理的意識,但主要受制于字形結構,如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包圍結構等。造型以結體為基礎,從結體方法到造型方法的發展,本質上是從客體到主體、從寫字到藝術的升華。當然,曹元偉非常重視字的結構。其結體深受米芾、趙孟的影響,中宮緊縮而呈縱勢,一字之中多用直筆并稍帶弧線,再加入局促的鉤趯,于不經意中彰顯縝密的藝術效果。在縱橫的欹側中,結體往右上傾斜而向左下舒展,或菱形或方形,或橢圓或三角形,頗具審美思想與審美情趣。
(三)章法:字距稍密、行距稍疏
曹元偉行草書作品,其行距不疏不密,字距稍緊,但每一獨立之行都頗具生命力,時而起伏跌宕,時而收放自如、連綿不斷。不僅單行左右擺動而自然活潑,且行與行之間亦是顧盼生情,無意中的穿插更是錯落有致,相互間的搖擺猶如成隊表演的廣場舞,隨著富有節奏的舞曲于紙上和諧而優美地舞蹈。條幅落款大膽,讓作品錦上添花,既簡單又有空靈感,頗具禪宗意識。其小品扇面以小見大,一般第一行寫六至七字,而第二行均為兩字,一行長一行短,一氣呵成。姿勢飛揚,聚散開合,強悍之氣凜凜而后生。曹元偉書法的章法豐富多樣,譬如小品行草橫幅。此小品運筆古雅渾厚,結字跌宕奇逸,章法同樣是字距稍密、行距稍疏,注重節奏,氣骨凜然。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精品力作,遵循起承轉合的原理,大膽落筆,信筆書之,體現出很強的控制和駕馭能力。行筆果斷而不草率,下筆重拙而不粗俗,筆畫圓渾而內蘊力量。整篇寫來,順其自然,無意中形成自然而富有變化的藝術形象。章法與布白更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極,真可謂無畫處皆是妙境。
(四)墨法:干墨渴筆,尤顯神采
品味與觀摩曹元偉行草書時,于神采飛揚的大幅行草立軸中方能見筆見墨。若筆法乃為書法創作中的筋或骨,那么墨法則屬于曹元偉書法創作中文字形象的血肉與靈魂。墨的使用與技巧問題一直是曹元偉關注的重要問題。從狹義角度來說,墨分五色,即分為焦、濃、重、淡、清或濃、淡、干、濕、枯。曹元偉的書法創作,以濃墨為主,因濃墨與白色宣紙的色度對比十分強烈,亦不乏濃淡兼施。在書家的眼底下,濃墨最顯精神,特別是行草,似乎只能用濃墨才能表現出筆力和神韻。從曹元偉書作來看,的確大多數作品因濃墨而富有強大的生命力。筆痕所示,曹元偉或許亦善焦墨。焦墨是指運筆中的墨濃而重,水分甚少,往往產生帶有渴筆而奇異的趣味性,如干皴之筆,一般在書法作品中使用難度較大。焦墨法是一種特殊的用墨技巧,如恰到好處地運用,也許有畫龍點睛之妙。若再加上濃淡變化,則效果更佳。明代倪元璐、徐渭擅用焦墨法。干墨,也指運筆中含墨較少,但比焦墨稍濕。于行草書中,干墨技法常于不經意間造就飛白的藝術效果,加強作品的墨色與層次。如宋代米芾《虹縣詩》《蜀素帖》以及黃庭堅草書,均使用干墨法。在書法創作中,曹元偉有能力做到用墨干而不燥,而筆勢依然通暢。孫過庭《書譜》中“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的論述,即是對書法用墨的最佳表達。曹元偉抓住書法用墨技巧與規律,特別擅長用焦墨、濃墨、干墨、淡墨,也偶用濕墨,往往產生渴筆與枯筆,濃而不滯,淡而厚,焦而清,書卷氣溢于紙墨之外。
三、純樸自然無意歸真
中國美學中向來就有兩種不同的美,其一是“錯彩鏤金、雕繢滿眼”,其二是“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錯彩鏤金”與“初發芙蓉”代表了中國美學史上兩種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貫穿了整個中國美學的發展歷史。宗白華認為“錯彩鏤金”和“出水芙蓉”分別對應著儒與道的兩家思想。“錯彩鏤金”的美反映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審美趣味,而“初發芙蓉”的美則往往是同道家的獨立人格、精神自由和美在天然等觀念聯系在一起。曹元偉的書法彰顯的是后一種美,即“初發芙蓉、自然可愛”之美。當然,這與曹元偉甚富儒道思想密不可分。在藝術上,曹元偉也提倡表現自然與樸素之美。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本身就是“自然”。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游》)“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莊子又強調“不飾于物”,主張“不以身假物”。因此老莊把自然素樸作為美的一種主要標志。這種標志亦為曹元偉創作所運用。
宗白華說:“中國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要做到“纏綿悱惻”就必須具有“錯彩鏤金”般的繁復之美,而要做到“超曠空靈”就必然融“芙蓉出水”般的白描。曹元偉亦是如此。他在崇尚“初發芙蓉”的同時,亦對“錯彩鏤金”進行舍棄,但主旨猶如李白所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并著力追求宋代蘇軾“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藝術觀點。蘇軾《與侄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弘一法師云:“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絢爛至極,歸于平淡。”毋庸置疑,曹元偉的書法作品不矯揉造作,保持自然本色。
曹元偉的書作,構思空靈,虛實相生,筆墨甚富魏晉之風。或小品,或巨作,俱為古雅。無須濃妝掩飾,然意境致遠靈動,頓使作品生機勃勃,形成了“洗盡鉛華、無意歸真”的筆墨語言,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高度。他對歷代法帖或碑文有深入的研究,注重吸收前人之優點,加以經營與創造,運筆變化多端,行草能“集眾所善,以為己有,更自立意,專為一家”。奇異之形,立意免俗,是禪宗境界的幻化。字形各異,姿態各殊,線條迂回蕩漾,富有節奏。如字組間的草書運筆,恍若行云流水。無意于法,實則有法;無意于佳,實則更佳。
四、結語
概而言之,曹元偉書法的綜合創作能力于國內已不多見,真不愧書法界的獲獎專家。其于藝術語言、意境與意蘊以及最難駕馭的用墨等,無不面面俱到,少有敗筆而歸真返璞。從古人中來,到古人中去,乃樸素自然之表現。曹元偉在提倡“神在能離”的同時,脫胎換骨而不離古,且追求線條流暢與線條組合的“無意于佳”之美,筆墨情趣充溢于作品之中,呈現出飽滿雄強、豪放遒勁的生命力。他把“自然天趣”作為書法的最高境界,出神入化,隨心所欲。其書法特點可用六字概括:一曰正統,二曰典雅,三曰和美。雖然在不同階段因學習碑帖有異,但他的書作始終保持著正統、典雅、和美之特色。不管是鐘繇的古樸、王羲之的淳美還是米芾的痛快等,一旦在他的筆下出現,似乎都經過了一番“中庸”的特殊處理,打上了趙松雪書風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