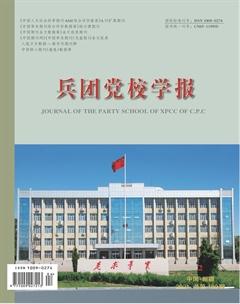基于耦合模型的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研究
菅琳琳 彭利 甘曉成



[摘要]新西部大開發提出將旅游業打造為區域重要支柱產業,新疆黨委政府已提出旅游興疆戰略,旅游業展現出強大的吸引力和復蘇力。生態環境是旅游業能否持續健康發展,能否走全域旅游發展模式的重要載體。新疆走全域旅游發展之路,必須處理好經濟、旅游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本文依據 2008—2017年新疆14個地州市旅游、經濟、環境方面的面板數據,選取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3大子系統20個評價指標進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三個系統的協調度進行定量測算。測算結果表明,新疆14個地州市的旅游業、區域經濟及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指數總體上均呈現出增長態勢,耦合協調類型大致經歷了“輕度失調—瀕臨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的轉變,而且旅游業、區域經濟及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變化特征穩定。 2017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處于良好協調狀態,其余各地州市耦合協調度處于中級協調階段。
[關鍵詞]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新疆
[中圖分類號]F125 ?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9—0274(2021)02—0071—08
[作者簡介]菅琳琳,女,新疆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與政府治理;彭利,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區域經濟、數量經濟;甘曉成,女,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與政府治理。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提出,支持西部地區大力發展旅游休閑、健康養生等服務業,打造區域重要支柱產業。新疆黨委政府已提出旅游興疆戰略,旅游業展現出強大的吸引力和復蘇力。越來越多的游客將目光聚焦新疆。2015年以來,新疆各地區接待國內外旅游人次逐年攀升。2019年,新疆接待游客歷史性突破2億人次。新疆旅游業發展勢頭強勁,日益成為新疆經濟增長的新增長極。全域旅游是新時代旅游發展的新模式,生態環境質量是旅游業能否持續健康發展,能否走全域旅游發展模式的重要載體。新疆發展全域旅游,必須處理好經濟、旅游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新疆處于干旱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環境是否能夠承載新疆全域旅游發展模式,新疆經濟、旅游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度如何,很少有學者研究,特別是14個地州市的三個系統的協調度筆者首次進行測算分析。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業—區域經濟—生態環境三者相互協調發展作用機理的基礎上,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截取新疆14個地州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數據,根據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對14個地州市的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分析,測算分析新疆14個地州市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程度,以期為相關部門制定全域旅游發展規劃及相關政策提供一定依據和參考。
一、文獻回顧
筆者在CNKI核心期刊中,以“經濟、旅游、生態環境、耦合”為關鍵詞搜索,不限發表時間,共搜索到68篇文獻。自學者劉定惠,楊永春(2011年)第一次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分析安徽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系統之間的關系以來,關于三者間耦合關系的文章2014年研究最多。研究區域包括廣西、廣東、安徽、湖南、江蘇、山西、黑龍江、新疆等十幾個地區。
劉定惠、楊永春(2011年)在研究和分析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過程中,首次使用耦合協調模型,結果發現,安徽省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依舊處于中級協調階段[1]。龐聞、馬耀峰(2011年)運用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對西安市2001—2009年間旅游經濟、生態環境進行了實證分析,文章結論部分指出,耦合協調模型是定量分析旅游可持續發展情況的重要工具,可以詳細分析二者之間的耦合關系和協調發展狀態,有利于評估旅游可持續發展實際狀況[2]。鐘霞、劉毅華(2012年)利用物理學中耦合協調度函數建模法,對廣東省21個城市2001—2010年間旅游、經濟、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研究結論:廣東省21市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在不斷提高,但不同地區間協調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3]。熊鷹、李彩玲(2014年)對張家界市1996—2010年間的旅游、經濟、生態環境三者之間協調發展程度的研究當中,同樣使用了耦合協調度模型,通過對測算結果的分析得出結論:相對于快速發展的旅游業來說,張家界市的生態環境發展與改善還具有較大的潛力和空間[4]。韋福巍、周鴻(2015年)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了廣西14個地級市2010—2012年間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研究結果顯示,三系統間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變化特征較為穩定,且綜合評價指數整體呈現增長態勢[5]。李琳、張濤(2019年)定量分析了黑龍江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程度[6]。張珍珍、曹月娥(2020年)分別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和GM(1,1)模型定量分析了昌吉回族自治州2007—2016年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的耦合關系和協調發展水平,結果表明三大系統間的綜合評價指數總體上呈現波動上升趨勢[7]。趙胡蘭、楊兆萍(2020年)以新疆整體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灰色預測模型對新疆2008—2017年間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大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三大系統間具有較高的耦合度,而協調度稍有起伏,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8]。
耦合協調度模型已逐步成熟并被越來越多學者所認可,廣泛運用于研究之中。目前從研究范圍來看,有關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三系統耦合的研究范圍主要集中在東中部地區,西部邊疆地區的研究則較少。關于新疆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三系統耦合研究也大都從新疆整體出發或只對昌吉州進行研究,還未分析各地州市的協調度、具體分析南北疆協調度差異。因此,本文在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上,以新疆14個地州市為研究對象,測算分析各個地州市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三系統間的耦合度及協調度時間和空間變化,比較不同區域間協調度差異。
二、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系統作用機理及模型構建
(一)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系統作用機理
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作為一個開放的、復雜的系統,具有不確定性強以及多層次性等特征,且該系統的各個組件相互關聯,相互依存,并且彼此交互。 它們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積極和消極影響并存。 因此,研究其多重相互作用機制是實現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
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機理如圖1所示:首先,區域經濟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為更好地保護環境、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提供必要的財政保障和技術支持,如轉變生產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發展可以為旅游業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與服務,推動旅游業發展與升級。其次,旅游業還是協調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旅游業作為“無煙工業”,具有經濟驅動力強、直接污染少的特點。一方面,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其他相關行業如住宿、餐飲等行業也將隨之得到很大發展,同時也可以促進地區與外界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動。另一方面,生態旅游的發展也使得旅游地更加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促使其在對生態環境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方面更加積極主動。最后,生態環境是旅游業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天然優勢和重要前提,同時人類從事一切生產活動所需的能源資源都要從生態環境中獲取。具體體現為,一方面,經濟的發展需要從生態環境中獲取資源;另一方面,旅游業得以健康及長期發展離不開生態環境提供的重要基礎。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發展可以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及旅游業的發展提供必要支持,而生態環境是經濟和旅游業得以發展的重要基礎,旅游產業則是協調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關鍵,三者密切聯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系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開放系統,所涉及的要素眾多,因此需要從多個角度來評價其協調發展程度。由于新疆各個地州市統計口徑的差異,對評價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造成一定限制,在閱讀文獻時發現不同學者對于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主要是根據研究區域范圍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及對比性原則來進行選取,因此本文在參考熊鷹(2014)[4]選取的29個評價指標 、韋福巍(2015)[5]選取的18個評價指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綜合考慮評價指標選取的客觀性、代表性,同時結合新疆14個地州市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情況,選取了經濟子系統、旅游子系統、生態環境子系統 3個子系統20個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其中旅游子系統分別選取國內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占GDP比重、星級賓館數、旅行社總數、住宿和餐飲業從業人數(城鎮非私營單位)6個指標;經濟子系統選取地區生產總值、人均GDP、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9個指標;生態子系統選取生活垃圾處理率、生活垃圾清運量、造林面積、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天數、人均公園綠地面積5個指標,來評估新疆14個地州市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狀況。
由于指標性質存在差異,每個指標的量綱和單位是不同的,無法直接比較、計算,因此在進行計算時,數據需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這里采用極差法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如下:
[xij=Xij-min(Xj)max(Xj)-min(Xj)](正向) ? ? ? ? ? ? ? ? ? ?(1)
[xij=max(Xj)-Xijmax(Xj)-min(Xj)](負向) ? ? ? ? ? ? ? ? ? ?(2)
式中:i為樣本數,j為指標序號,X為指標值,x為標準化值。為防止出現數值較小或為0的情況,且為了計算的統一與方便,可以將數據進行平移處理:[x″ij=H+x′ij]
由于[x′ij] ?位于0和1之間,因此H一般可取1。同時,本文采用熵值賦權法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具體步驟如下:
step1:用比重法對平移后的數據進行歸一化
[yij=x″iji=1nx″ij]
step2:計算各指標的熵值
[ej=-1lnni=1nyijlnyij]
其中[ej]為第j個指標的熵值(下類似),j=1,2,3……p。
step3:計算差異系數:[gi=1-ej]
step4:計算指標的權重:
[ωj=gjj=1pgj]
評價指標及其權重如表1所示(注:由于文章測算地州市較多,在此對各地州市權重計算結果不進行一一羅列,僅以烏魯木齊市2008—2017年權重計算結果為代表進行展示)。
(三)耦合協調度模型和計算方法
各子系統綜合評價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f(x)=i=1maix′i] ? ? ? ? ? ? ? ? ? ? (3)
[g(y)=i=1mbiy′i] ? ? ? ? ? ? ? ? ? ? ? (4)
[h(z)=i=1mciz′i] ? ? ? ? ? ? ? ? ? ? ? ? (5)
式中: f(x),g(y),h(z)分別代表旅游業、生態環境、區域經濟各系統的綜合效益;[ai],[bi],[ci]分別為各子系統中各指標的權重;[x′i],[y′i],[z′i]分別表示旅游產業、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無量綱化指標值。
本文主要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耦合模型,對新疆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耦合度及協調度進行定量測算。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推廣得到多個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1],即:
[c=f(x)g(y)h(z)(f(x)+g(y)+h(z)/331/3] ? ? ? ? ?(6)
在公式中,C代表耦合度,其取值范圍為0—1。C值越趨向于1,說明系統間相關性越強,并且朝著有序方向發展,當它等于1時,為最佳耦合狀態。反之,則說明系統間相關程度較弱,并且朝著混亂方向發展,當它等于0時,表明系統完全混亂狀態[5]。耦合階段劃分見表2。
由于耦合度只能說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反映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5]。因此,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以便更好地評價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協調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D=CT],[T=?f(x)+βg(y)+δh(z)] ? ? ?(7)
其中:C表示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度,D表示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T表示三者之間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α、β、γ分別為待定系數。需要說明的是,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的計算公式中涉及的權重值,在權衡相關研究領域專家的評價意見后,考慮到城市旅游業、區域經濟、生態環境具有同等重要性,故取α、β 和 γ取值相同,可以平均認定為各占1/3。
為了更直觀地表述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程度,本文參考廖重斌(1999年)[9]的研究,對耦合協調度的等級進行劃分。由于D∈[0,1],采用均勻分布函數法來確定耦合協調度的類型與劃分標準,見表3耦合協調度等級分類:
三、實證研究結果分析
首先利用公式(1)(2)對新疆14個地州市的區域經濟、旅游業及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評價指標體系中2008—2017年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采用公式(3)—(5)計算得出各城市旅游產業、社會經濟及生態環境評價指數,再將其代入公式(6)、(7),經計算,最終分別得出三者之間的耦合度指數、綜合評價指數及耦合協調度指數(見表4—表6)。
從表4、表6中可以看出,新疆14個地州市的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整體上都呈現增長趨勢,這表示各個地州市三者之間的互動性逐漸增強,逐漸形成良性互動。
(一)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個系統綜合評價得分分析
新疆14個地州市旅游系統的綜合得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波動。就旅游子系統來說,從表5中我們可以看出2008—2009年間,新疆14個地州市的旅游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得分整體偏低,2010年有所回升。2011—2014年間,旅游子系統綜合評價得分持續走低。 2015年以來,新疆穩定紅利初步顯現,同時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和“橋頭堡”,新疆憑借自身旅游資源豐富獨特、人文氣息濃厚等優勢,迎來了旅游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從經濟子系統看,過去十年間,新疆各地州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呈逐年增長態勢,但其增長速度并不穩定。2008年,具有相對優勢的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地區的經濟子系統綜合得分在0.5左右,相對落后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得分不到0.4,而到2017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經濟子系統綜合得分在0.7左右,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喀什等地區得分仍然在0.4左右浮動。北疆和南疆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存在著顯著差異。
鑒于統計年鑒中各地州市生態環境統計口徑存在差異,故只選取生活垃圾處理率、造林面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等五個共有統計樣本作為評價指標。從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得分看,新疆14個地州市生態環境整體得分呈穩步上升態勢,其中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吐魯番、哈密等地區綜合得分在0.7左右,比其他地區稍遜一籌,究其原因在于這些地區人口密度較大,人口壓力以及一些不合理的開發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阿勒泰地區綜合得分在0.8以上,阿勒泰地區地處新疆最北端,過去十年間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天數均在350天以上,且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在全疆范圍內是最多的, 2017年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為27.48㎡。
(二)各地州市耦合協調度變化分析
1.各地州市耦合協調度的時序變化分析。從表6和圖4可以看出,新疆14個地州市在過去十年間經濟、旅游、生態環境三個系統耦合協調度(D值)呈上升趨勢。2008—2009年間,新疆大部分地州市耦合協調度處于勉強協調(0.50—0.59)和瀕臨失調(0.40—0.49)狀態,其中阿勒泰地區2008年處于輕度失調狀態,2010年新疆14個地州市除吐魯番地區外,基本呈現初級協調發展狀態,吐魯番地區2010—2011年間較其他地區相比,處于勉強協調階段,結果顯示阿克蘇地區2010年呈現出中級協調狀態;數據顯示2012—2017年間,新疆14個地州市D值雖有起伏,但整體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到2017年,各地州市的耦合協調度值達到0.7、0.8以上,進入中級協調階段和良好協調階段。
雖然新疆14個地州市D 值總體上呈上升趨勢,但各地州市在不同研究時段內都存在一定程度波動,而且出現波動的時間基本重合。如2011年,受到新疆社會局勢穩定的影響,各地州市的 D 值普遍有所下降;2014年,同樣受到穩定局勢的影響,新疆大部分地州市的D值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之后幾年,新疆在全區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奮斗下,經濟社會發展平穩,尤其是近五年,新疆著力推動旅游業大發展,大力實施旅游興疆戰略,不斷推進全域旅游的發展,使得新疆旅游業不斷取得驕人成績。除此之外,自2015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自治區牢固樹立“環保優先、生態立區”理念,在該理念的指導下,全疆各地州更加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堅持走綠色健康可持續發展道路,因地制宜加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和建設力度,確保在推進旅游興疆戰略過程中,保護好生態環境,最終實現產業發展的順利轉型升級,進而推動全疆經濟的發展。截至2017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塔城地區以及阿勒泰地區的D值均在0.8以上,呈現出良好協調狀態。
2.各地州市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變化分析。根據表6,對新疆14個地州市的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時段的橫向空間對比分析。通過對比分析發現新疆2008—2017年10 年間耦合協調度空間發展呈現不平衡的發展狀態。
2008—2009年,新疆部分地州市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吐魯番地區、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耦合協調發展度D值處于0.40—0.49之間,處于瀕臨失調狀態。其中,旅游子系統和生態子系統得分較低,究其原因是當時這些地區旅游業發展動力不足,且大都位于邊界地區,普遍出現生態赤字現象[10],其余各地州耦合協調發展度D值皆在0.50—0.59之間,處于勉強協調狀態,從生態系統得分我們可以發現,烏魯木齊市、昌吉州、伊犁州、博州等地州生態系統得分相對其他地州較高,這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及原有生態環境良好。
2010—2011年,新疆14個地州市耦合協調發展度D值都呈現一定程度的增長,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擺脫瀕臨失調狀態,旅游、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進步,D值在0.60—0.69之間,屬初級協調狀態;南疆阿克蘇地區超越其他各個地州市,率先進入中級協調狀態,這與阿克蘇地區良好的環境建設密不可分。
2012—2015年,新疆大部分地州市旅游、經濟、生態環境整體發展態勢較為平穩,處于初級協調狀態和中級協調狀態,2012—2013年,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和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耦合協調發展度D值在0.70以上,開始進入中級協調狀態。
2016—2017年,伊犁州、昌吉州、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經濟—旅游—生態系統耦合協調發展度D值率先突破0.8,在全疆范圍內率先進入良好協調狀態,其領頭兵作用非常突出。受益于這四個地區三個系統的良好耦合協調狀況,隸屬于伊犁州的昭蘇縣、溫泉縣、昌吉州的木壘縣、阿勒泰地區的阿勒泰市、布爾津縣在2016年被評為國家級“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單位”。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對新疆14個地州市區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指數及耦合協調度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從耦合協調度的時間序列變化來看,新疆14個地州市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呈上升趨勢。新疆在發展經濟、旅游業的同時,生態環境保護措施不斷加強,環境改善明顯。旅游、經濟、生態環境三者之間聯系愈加緊密,相互驅動、相互影響的程度逐漸加深,新疆范圍內旅游、經濟、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基本實現。但新疆走全域旅游發展之路,需要黨政統籌、規劃引領,環境保護等多部門聯合,高位推動全域旅游發展,制定和完善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及其他方面協調發展戰略,扎實推進,確保新疆早日進入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
其次,從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變化來看,北疆和南疆地區全域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還存在一定差距。北疆大部分地州市旅游、經濟、生態環境基礎好,耦合協調度增長速度較南疆稍快,日漸成為輻射和帶動新疆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南疆四地州雖然基礎薄弱,發展較為滯后。盡管隨著近年來新疆全域旅游、旅游興疆戰略的不斷落實推進,南疆各地州紛紛抓住發展契機,大力發展當地旅游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耦合協調度值也隨之緩慢增長。但南北疆三個系統的耦合協調性還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南疆克州、和田、阿克蘇等地區要大力發展旅游業,同時也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這種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南北疆產業與經濟的交流和互動,只有南北疆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才能助力“旅游興疆”戰略更好推進,因此應通過整合各地州市的優勢資源,盡量縮小經濟—旅游業—生態環境三個系統協調發展差距,從而打開南北疆互利共贏的新局面,真正形成互聯互動、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進而提升全疆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劉定惠,楊永春.區域經濟—旅游—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研究——以安徽省為例[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11(7):892-896.
[2]龐聞,馬耀峰,唐仲霞.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及協調發展研究——以西安市為例[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6):1097-1101+1106.
[3]鐘霞,劉毅華.廣東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分析[J].熱帶地理,2012(5):568-574.
[4]熊鷹,李彩玲.張家界市旅游—經濟—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綜合評價[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S3):246-250.
[5]韋福巍,周鴻,黃榮娟.區域城市旅游產業、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研究——以廣西14個地級市為例[J].廣西社會科學,2015(3):24-28.
[6]李琳,張濤.黑龍江省旅游產業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研究[J].林業經濟,2019(12):25-31+50.
[7]張珍珍,曹月娥,趙珮珮,蔣璟.昌吉回族自治州經濟—旅游—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初探[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3):95-101+126.
[8]趙胡蘭,楊兆萍,韓芳,時卉,王璀蓉,郭姣姣.新疆旅游產業—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耦合態勢分析及預測[J].干旱區地理,2020(4):1-12.
[9]廖重斌.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判及其分類體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熱帶地理,1999(2):3-5.
[10]史磊,周華榮.2009—2014年巴州生態足跡時空變化及驅動力分析[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7,(S2):311—316.
[11]周成,馮學鋼,唐睿.區域經濟—生態環境—旅游產業耦合協調發展分析與預測——以長江經濟帶沿線各省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6(3):186-193.
責任編輯:彭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