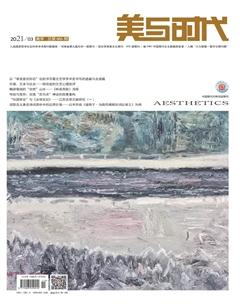“怡園琴會”與《會琴實紀》
摘? 要:1919年8月25日,葉希明在江蘇蘇州怡園舉辦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大規模琴人雅集“怡園琴會”,而《會琴實紀》則是“怡園琴會”的會議紀實。通過對《會琴實紀》卷一至卷六記錄的內容研究,可以發現“怡園琴會”具有琴人群體的特定性、琴學的家族傳承性以及禮樂之治寄興于琴等典型特點。可以說,蘇州“怡園琴會”的召開是一種創舉,挽救琴學于頹廢,重振琴人之信心,因而這一琴會的舉辦也被譽為“古琴文化藝術邁入近代的標志”,為古琴文化藝術的傳承奠定了基礎,影響深遠。
關鍵詞:“怡園琴會”;會琴實紀;江蘇;古琴文獻
20世紀初,隨著封建帝制的瓦解,西方啟蒙思想的進一步傳播,先進的知識分子們打著“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口號,發起了以“四提倡、四反對”為內容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批判封建社會制度和倫理思想,直把矛頭指向“孔家店”。而自公元前10世紀誕生以來的古琴,歷經三千多年的發展與演化,作為“八音之首”的琴,經歷了從“法器”“禮器”“道器”至“樂器”的轉變。在歷代琴學文獻和相關古籍中,都可見學者們對琴學思想的探究,而古琴作為儒家思想的一種載體,此時也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以致于民國時期古琴文化藝術幾近消亡。面對古琴的生存危機,通琴儒者一方面仍堅持傳統琴學主張,另一方面又以復興琴學為已任。1919年8月25日,葉希明在江蘇蘇州舉辦了“怡園琴會”,這“是近代史上有據可查的首次大規模的邀約各地琴人的全國性集會”,有挽救琴學于頹廢,重振琴人之信心之功,因而這一琴會的召開也被譽為“古琴文化藝術邁入近代的標志”。
一、“怡園琴會”與《會琴實紀》的內容
“怡園”是蘇州名園中建成最晚的一座,它集“滄浪亭”“網師園”“拙政園”“獅子林”等名園之妙于一身,是其主人顧文彬歷時七年于1874年修筑完成的,自此成為集詩歌琴韻、曲音不絕的雅園。至今一百余年前,怡園主人顧鶴逸(顧文彬之孫)與蘇州鹽商葉希明藉以興起絕學繼往開來,遂“聯合同調討論琴學”大集琴侶,組織了近代史上首次來自北京、湖南、揚州、上海、杭州、蘇州、四川、河南等地善撫琴、通琴理之琴人相聚怡園,開展了為期一天的全國性集會“怡園琴會”,以共同商討研究琴學。而《會琴實紀》則是“怡園琴會”的會議紀實,由葉希明主編,共六卷,分別為程式、雁訊、鴻篇、答案、會記、琴考;另卷首有圖片六幅,分別為琴會操縵者合影、藏琴合影、部分琴友合影以及李子昭作《怡園會琴圖》長卷一至三。1920年秋,葉希明邀請了吳昌碩題寫了書名,刊印成書。如今我們從《會琴實紀》的記載中可還原當年“怡園琴會”的歷史風貌。
(一)“怡園琴會”的召開時間與地點
從《會琴實紀》卷一“程式”的“請柬式”記錄可見,琴會原定于“夏正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地點為“蘇州城內護龍街尚書里顧家別墅,一名‘怡園”,也即今蘇州市人民路1265號。但從“臨時改期知啟式”又可知因“整理瑟弦,頗費手續,展緩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舉行,地點不變。《會琴實紀》卷三“鴻篇”記載,與會者周慶云“賦五古一章”可見,主人原定于二十四日的集會,因其本人外出有事而不能參會,所以展緩一日于二十五日舉行;從與會者方外廣陵谷和尚所題“俚語二章”中“已未中秋后十日”以及未能赴會的蜀南董汝昌所賦詩中“名園勝會暮秋天雖在八月寒露已過”可知,“怡園琴會”召開的時間是按農歷日期所記八月二十五日(即農歷1919年8月25日)。
(二)“怡園琴會”的受邀琴人和參會琴人
從《會琴實紀》卷一“程式”記錄的“發柬計數”可見,葉希明最初邀請了48位琴人,主要來自北京、長沙、揚州、上海、杭州、蘇州、四川、河南等地,其中又以揚州、上海、蘇州三地琴人最多,達27人。從“臨時改期知啟式”其后所列出的24位琴人是延會一天所邀請的對象,主要是蘇州本地琴人。對比兩份受邀名單可發現“臨時改期知啟式”所邀請的24位琴人中有21位是重復出現在最初“發柬計數”邀請的48位琴人名單中的,只有3位來自“本公堂”(葉希明就職于蘇州鹽公堂)的琴人郭誠齋、傅栽之、鄭玉蓀是新增邀請人員。也就是說,最初邀請的48名琴人中有21位是無法參與原定時間八月二十四日舉辦的琴會的。接著從八月二十五日“到會簽名簿式”中不僅可見共有33位琴人與會簽到,而且可知與會者姓名、年齡、籍貫與通信處等信息(具體參見《歷代古琴文獻匯編——琴人琴事卷下》第1972-1973頁)。從這份名單中可知與會者年紀最長者是來自吳縣的費德保(73歲),年紀最小者是來自杭州的葉震群(13歲),其他與會者年紀多數在四五十歲之間。從《會琴實紀》卷二“雁訊”篇可見,有4名未能赴約的琴人以“來書”的形式婉言拒絕了葉希明的邀請,分別是近代著名琴學大師楊宗稷(北京)、近代著名古琴音樂大師張子謙(揚州)、上海根如和尚以及杭州談靖仙女士。
(三)“怡園琴會”的具體活動內容
從《會琴實紀》卷一“程式”記錄的“次第”可見本次琴會主要開展八項活動,分別是暢敘情話、輪流撫琴、單獨鼓瑟、試擘箜篌、研究學術、入座飛觴、成興雙彈、鴻雪留痕。卷一“操縵一覽表”記載了與會琴人中14位演奏者的情況,包括姓名、年齡、籍貫、琴操名(所演奏琴曲的曲名)、音調、段數、琴譜名(演奏琴曲使用的曲譜名)等信息(具體參見《歷代古琴文獻匯編——琴人琴事卷下》第1973-1974頁)。在這14位演奏者中,來自江蘇4人,湖南4人,蜀中和浙江各3人,最長者是來自崇慶的李子昭(63歲),所彈琴曲是出自清代《五知齋琴譜》的《雁過衡陽》,最年輕者是來自杭州的葉震群(13歲),所彈琴曲是出自清代《自遠堂琴譜》的《圯橋進履》。14位演奏者共彈奏了12首傳統舊曲,除琴曲《胡笳十八拍》使用“外調”定弦以外,其他琴曲均使用“正調”定弦,其中《梅花三弄》和《平沙落雁》分別有兩人彈奏。來自江陰的鄭覲文用自制仿古樂器瑟與箜篌分別演奏了琴曲《鷗鷺忘機》和《秋風高》。六旬長者李子昭不僅與琴友吳觀月雙琴對彈《風雷引》,還與鄭覲文琴瑟合奏了《良宵引》。琴會八項活動之一的“鴻雪留痕”主要就是與會人員全體合影、部分琴友合影、琴瑟箜篌合攝、撰述會記、繪圖徵題和鐫石藏圖。其中,“研究學術”作為本次琴會的一項重要活動,主要探討了七個問題,其中“甲學理”有二:“換調轉弦與換調不轉弦之原理”“按音三準泛音四準不同之原理”;“乙技術”有五:“一為譜中,一云‘喚一云‘換,究以何者為標準,及其動作法;二為‘午即‘滸之減字,應如何取音及動作法;三為‘芑譜云‘對起,宜若何用指法;四為‘飛吟‘淌吟‘往來吟‘游吟之用指區別,取音分明不致牽混法”,最后一個問題實質是一則構想或建議,將諸公所奏之曲詳細記錄以刻琴譜。由于會期短、時間緊,“甲學理”與“乙技術”所涉及的七個問題未能在琴會當日展開討論。因此,在《會琴實紀》卷四“答案”篇中可見由吳縣王壽鶴對琴學之六“問題”進行研究并撰寫了“答案”逐一回復。
二、“怡園琴會”與《會琴實紀》的特點
通過對《會琴實紀》卷一至卷六記錄的內容研究,可以發現“怡園琴會”中的幾個典型特點,主要體現在琴人群體的特定性、琴學的家族傳承性以及禮樂之治寄興于琴等方面。
(一)琴人群體的特定性
從“怡園琴會”的兩份邀請名單看,《會琴實紀》卷一“程式”記載的原定于“夏正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的“請柬式”所邀請的48位琴人名單、“臨時改期知啟式”定于“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召開的臨時邀約名單以及“到會簽名簿式”的名單,可見受邀琴人和與會琴人的姓名、年齡、籍貫、通訊處等信息,由此可知,琴人群體集中于“士紳”階層。而這一特性也正是沿著西周時期古琴逐漸普及到士階層,成為儒家士大夫修身養性的“道器”,是一條通往智慧之路而發展的。“士無故不徹琴瑟”(《禮記·曲禮篇》)“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心也。”(《左傳·昭公元年》)“會彈琴,彈好琴”則逐漸成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其成為士紳階級的象征。但從反面而言,這種“士紳”階層的特性,同時對學琴者、彈琴者、聽琴者都提出了較高要求,要求三者都應具有“同質性”,即在文化修養、精神內涵等方面具有相似或相近的審美觀,否則是彼此無法“聽懂”的,這也正體現了春秋時期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故事的意義。“同質性”必然導致“排他性”,“排他性”也必然導致琴人群體的封閉性,事實上這不僅不利于古琴文化藝術的傳播與普及,在一定意義上且成為其絆腳石。
(二)琴學的家族傳承性
從《會琴實紀》卷一“程式”的“請柬式”所邀請的48位琴人名單和“到會簽名簿式”記載的與會33位琴人名單中可見,年紀最小者是來自杭州的葉震群(13歲)。在33位與會琴人中,僅有14位琴人參與了即席“操縵”(這14位操縵琴人應該是琴藝水平較高者),而這位僅13歲的葉震群作為14位“操縵”者之一,演奏了一曲出自清代《自遠堂琴譜》的《圯橋進履》。再次研究33位與會者的年齡結構可發現,除最長者是來自吳縣的費德保(73歲),其他與會者年紀多數在四五十歲之間,而年紀與葉震群相仿或二十歲左右的青少年琴人并沒有,從葉震群所填寫的通信處是“蘇州鹽公堂”(琴會組織者葉希明是蘇州鹽公堂大鹽商)以及其他資料可知,葉震群應該是生于琴學世家且受到了琴學的家族傳承。家族傳承通常是由上一輩傳承給下一輩而世代延續,體現了“口傳心授”的教學特點與琴學的傳統性特色,試想,如果葉震群沒有琴學的家族背景,怎么可能小小年紀即擁有這樣參會與操縵的機會呢?從與會琴人中,年青琴人的缺乏也可見民國時期琴壇的凋零與頹境。
(三)禮樂之治寄興于琴
《會琴實紀》卷首的兩份“序”分別由“吳江金天翮松岑甫敘”(金松岑,清末民初國學大師)和“山陰吳隱潛容撰”(吳隱,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從金天翮松岑甫敘”所言的“今瑟學喪其傳而琴之制絲與桐之質,其于三代不能無異也”“今禮壞樂崩,聲音流放自箏琶羯鼓,以至歐美蕃樂洋洋盈耳,朝野嗜之”和“山陰吳隱潛容撰”所言的“琴固古樂而至今存者哉,世有夙悟神解妙達,音律不于成見,不溺于墜聞,出而審音定律庶幾可以矯俗可以復古”可見,在這兩份“序”中不約而同地都體現出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禮樂之治寄興于琴”。“禮”主要規范人的行為準則,“樂”主要起教化作用,是安定人心的工具,是制度性和規范性的結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作其教焉。”(《樂記》)琴作為“三代之音”的遺存,作為治世的代表,先王制禮作樂的目的是用“樂者,通倫理者也”,來實現“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的社會教化作用。盡管“怡園琴會”的召開已是民國初期,但是在舊式文人心目中,琴的“將治四海先治琴”地位與“扶正國風”功能依舊沒有改變。
三、“怡園琴會”與《會琴實紀》的意義
蘇州“怡園琴會”的召開是一種創舉,其影響深遠,為古琴文化藝術的傳承奠定了基礎。從《會琴實紀》卷二“雁訊”中杭州談靖仙女士來書可見,談女士稱“怡園琴會”是“從來未有之盛舉”、卷三“鴻篇”中大休和尚所言“大集琴侶系獨創舉”,以及卷首“例言”中葉希明自敘“同人贊為創舉,命將經過手續,編輯成帙,以資參考”,可見“怡園琴會”的召開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廣招海內諸名公的雅集,其地位被山陰吳隱譽為與永和九年的蘭亭雅集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同時,此創舉打破了傳統古琴雅集的地域性局限,為古琴文化藝術的傳承奠定了基礎。在“怡園琴會”的影響下,當年未能赴會的北京楊時百于次年1920年2月,在北京的“岳云別業”舉辦琴會;同年,周慶云在上海舉辦了規模較大,影響力較遠的多地區“晨風廬琴會”,以推動琴學復興,并散發了其主編的《琴史補》《琴史續》(是對宋代朱長文《琴史》遺漏部分的補充和延續)、《琴書存目》《琴操存目》等琴學著作。1936年,查阜西等人創辦了今虞琴社,編有《今虞琴刊》,定期組織全國各地琴人從事琴學研究,而“怡園琴會”正是“今虞琴社”建社的發韌。1956年,查阜西主持了全國古琴采訪調查,此次調查走訪了21個省,訪問了86位琴家,收集了270多首琴曲,并編印了《存見古琴曲譜輯覽》《琴曲集成》《琴論輟新》等琴學史料著作。
蘇州“怡園琴會”的召開“是近代史上有據可查的首次大規模的邀約各地琴人的全國性集會”作為全國性集會,“怡園琴會”的召開挽救了琴學之頹廢,重振了琴人之信心,因而這一琴會的舉辦也被譽為“古琴文化藝術邁入近代的標志”。古琴文化藝術在中國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2003年,古琴藝術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6年,被列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且還是唯一入選的古樂器。在三千多年的古琴史上,江蘇又是其發展重地,在古琴藝術的眾多流派中,從明清起先后成立了常熟的虞山派、揚州的廣陵派、南京的金陵派、南通的梅庵派以及蘇州的吳門派等,而吳門派正是在“怡園琴會”的深遠影響下,于1986年11月4日,由吳兆基等四人發起的“吳門琴社”在怡園成立。在全國性流行的八大古琴流派中江蘇獨占四席,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更成為全國的琴學中心,這一切與江蘇獨特的地理環境、豐富的自然資源、富庶的經濟條件、豐厚的歷史文化、優良的人文生態環境等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這一發生在江蘇大地上的有史料記載的重要琴會,為江蘇古琴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會琴實紀》呈現了當年“怡園琴會”的歷史風貌,也再現了民國時期江蘇琴壇的狀況,據此也可以了解到這一發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在一片“全面西化”的呼聲中,傳統舊式文人群體又是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去對待在這一激烈浪潮中的自己和自己的處境的。
參考文獻:
[1]古琴文獻研究室編.歷代古琴文獻匯編:琴人琴事卷下[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
[2]朱長文.琴史[M].北京:中國書店,2013.
[3]許健.琴史新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4]嚴曉星.民國古琴隨筆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5]戴微.新文化運動中的琴人與琴會:論“怡園琴會”和“晨風廬琴會”在近代琴史上的價值與意義[J].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5(3):70-81.
[6]王詠.文化遺民的區隔符號:對新文化運動中古琴藝術的社會學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120-124+140.
[7]林晨.名園與雅會:“怡園琴會”紀事[J].中國音樂學,2011(3):94-98.
作者簡介:雍樹墅,博士,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與古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