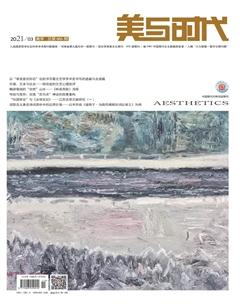淺析吳冠中油畫藝術的民族化


摘? 要:油畫藝術的民族化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近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美術家都在不停息地為之努力。吳冠中先生作為中國當代畫壇的巨擘,他“東尋西找”,把畢生精力都致力于了油畫民族化的探索之上。他扎根于故土,將油畫的厚重濃郁和形式美感與中國傳統的審美意境融為一體,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符合了中國普通大眾的審美情趣,使油畫實現了雅俗共賞,創造出了獨具個人風格和民族特色的繪畫圖式。
關鍵詞:吳冠中;油畫;民族化
油畫自傳入中國起,國內的藝術家就不間斷地嘗試將其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以實現外來油畫藝術的民族化。“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必然存在的文化現象,是文化傳播規律的客觀結果。油畫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中國化是其必然結果。”[1]
20世紀20年代,徐悲鴻至法國留學,在此期間他吸收了西方古典繪畫的技巧,并將西方寫實油畫的技法、精神帶回國內,開始了“中西結合”的探索,創作了如《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等作品。與徐悲鴻同時期的林風眠,也將印象派的外光畫法和中國的水墨畫法結合起來,同時又吸收了中國民間皮影、剪紙藝術的造型方法,創造出了一種既不同于中國古代又不同于西方現代的新的繪畫風格。除此之外,還有吳大羽、劉海粟,以及后來的“留法三劍客”——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等在中西方繪畫之間傾盡全力嘗試探索的人。雖然在油畫民族化的道路上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探索者,但由于各方面原因,這個過程艱難而又曲折,直至改革開放,中國油畫民族化的探索之路才得以迎來新的發展期。在諸多的探索者中,以吳冠中的民族化探索最為成功,最能凸顯中國百姓的審美情趣以及彰顯東方特有的文化意蘊。
一、早期的油畫民族化探索
吳冠中先生在留法期間,在老師蘇弗爾皮的啟發下對西方藝術,尤其是現代派繪畫的藝術品味、造形結構、色彩力度有了最基本的認識和系統性的了解,這些啟蒙對吳冠中后來的油畫創作和民族化探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蘇弗爾皮勸他回到中國,從自己傳統的根基上發出新枝,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作品不能脫離祖國的土地和家鄉的父老鄉親,必須把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融入到油畫中,將高雅的藝術通俗化,突出民族特色,表現民族風格,發揚民族文化,創造出具有時代意義的油畫作品。“西方現代油畫的主流早已從摹擬自然形態進入創造藝術形象了,畢加索+城隍廟,西方現代繪畫與中國民間藝術的結合,也正是油畫民族化的大道之一。”[2]189
要實現油畫民族化,吳冠中一開始便從“看不見的地方”入手,這個“看不見的地方”其實就是指意境,他說:“先不考慮形式問題,我只追求意境,東方的情調,民族的氣質,與父老叔伯兄弟姐妹們相通的感受。”[2]184意境是中國美學的核心關鍵,古代很多文學家、美學家都把意境放在品評作品優劣的首要位置。唐代詩人王昌齡在其《詩格》中認為詩有三境:物境、情境及意境,其中以意境為最高境界。明代朱承爵在《存馀堂詩話》中提出:“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清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意境的闡述更加全面深刻,認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吳冠中先生奔走于鄉村山野、江林湖海,通過寫生的方式描繪具有中國鄉土氣息和民族特色的事物,如《南瓜》《麻雀》《碾子》等作品,以普通老百姓常見的本土事物為題材,和勞動人民產生心靈上的共鳴,表現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情調。20世紀60年代,吳冠中用油畫寫生江南的黑瓦白墻、桃柳交錯,這些景物是中國大地上特有的,土生土長,在西方繪畫中從未有過,蘇聯專家一度認為這種景物無法用油畫材料表現出來。《萬戶炊煙》《浙江蘭溪》《江南小鎮》等寫生作品,讓人們意識到了油畫民族化的可行性以及用油畫表現中國意境的可行性。
二、在油畫民族化和國畫現代化之間的探究
吳冠中先生出國之前,曾跟隨潘天壽學習中國傳統繪畫,臨摹過大量山水畫,因此,在國畫方面他有著相對扎實的基礎,在感受到了水墨產生的奇妙畫面效果的同時,也常常囿于傳統的筆墨與程式。傳統中國畫雖然在繼承中發展,但往往把筆墨當作品評一幅畫的唯一標準,而忽視畫面的整體效果,喧賓奪主,舍本求末。這使吳冠中先生開始審視傳統,思考當代。于是吳冠中提出了“筆墨等于零”的觀點,認為“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筆墨,其價值等于零”“但筆墨只是奴才,它絕對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緒的表達,情思在發展,作為奴才的筆墨手法永遠跟著變換形態,無從考慮將呈現何種體態面貌。”[3]79筆墨當跟隨時代,唐宋元明清,各有其時代特色,時代不同,筆墨也不同。工業革命以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密切,同樣是地處東方的日本,在19世紀末就開始吸取西方繪畫語言與技巧,革新以線條為主的傳統日本畫。中華文化向來有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優點,佛教藝術的中國化就是極好的例證。如今中國畫的發展必須立足時代,著眼當代,若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只有死路一條。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作品必須表達作者的真情實感,油彩與水墨只是不同的繪畫媒介,并非區分東西方藝術的關鍵,二者皆存在優點與缺點。吳冠中說:“油畫的民族化與國畫的現代化其實是孿生兄弟,當我在油畫中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將它移植到水墨中去。有時倒相對地解決了。同樣,在水墨中無法解決時,就用油畫來試試。”[2]190他同時使用水墨與油彩輪番進行實驗、比較,對兩種不同媒介深入分析,取長補短,克服彼此內在的局限,尋找契合點,根據創作的需要而選擇不同的創作方式。吳冠中把油彩與水墨,比作是剪刀的兩刃,裁出東西方結合的時代新裝。他在傳統中國水墨畫中融入西方現代派繪畫的構成形式,將西方油彩賦予東方特有的審美意境,這便形成了吳冠中獨特的繪畫語言和風格面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吳冠中對油畫民族化與國畫現代化的探索達到了成熟階段,他的《拙政園》《香港之夜》《水巷》等油畫作品中,流露出濃厚的東方意蘊和靜謐的詩意,讓中國油畫開始受到世界的關注。
三、獨具個人風格的創作方法
文藝復興以后,經過科學分析的“焦點透視”被廣泛運用在西方傳統繪畫中,而吳冠中作畫卻不執迷于某一個角度。他說:“我的大部分風景畫是通過構思、選取不同的素材組成的,作一幅畫,往往要數次搬動畫架,從幾個不同地點去寫生。”[2]189這種“移花接木”的創作方式,全景式的構圖,正是中國傳統山水畫所采用的“散點透視法”。吳冠中的這種創作方式與畢加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畢加索以動點透視多方向去觀察物體,對西方傳統的觀察方式和形體表現做了革命性的改變,由此開創了立體主義繪畫的先河。而吳冠中通過這種移動畫架的作畫方式,避免了同一個視角觀察的局限性,拓寬了繪畫的視角,進而追求具體形象的真實生動感。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他的寫生作品《魯迅故鄉》,便是以俯視的角度對紹興的民居做了全景式的描繪,畫面右邊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搬來一組樹林作為近景,將中景的房屋進行遮擋,以加強畫面的層次關系;遠處的堤岸、房屋和白帆又符合西方空氣透視法所產生的近大遠小、近實遠虛的視覺規律,朦朦朧朧、若隱若現,一片江南煙雨景象,讓人產生無限的遐想。
傳統中國畫中,畫家為了突出畫面的意境,會將云、霧等作“虛”處理,甚至是留白,以達到山光浮動、雨霧煙嵐的畫面效果。吳冠中在油畫創作中,也將這種“虛”的手段運用在畫面中,如《雪后玉龍山下》《雨后山澗》《漓江之濱》《桂林》等作品,使觀者能夠在油畫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云霧縹緲、煙雨掩映的東方氣韻。
水墨畫講究筆墨的干、濕、濃、淡,由于吳冠中的油畫民族化探索在是油彩與水墨之間同時開展的,油畫的創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水墨技法的影響,其中“干與濕”的對比就是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古人在繪制山水畫時,常先用干筆勾勒皴擦出山石的形狀與主要結構,再以濕而淡的墨色渲染,以達到豐富畫面的效果。在吳冠中的作品《水巷》《新巴黎》《老墻》中,干筆在畫布上擦過后形成的特殊肌理效果,像極了枯毛筆在宣紙上留下的非白,這種由水墨畫中取來的表現技法,在吳冠中油畫民族化探索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除了以上幾點外,吳冠中還在作品中常用到“線”。線條在傳統繪畫和書法中能夠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吳冠中表現線條主要有兩種手段,一是直接用筆蘸顏料用書寫的方式進行表現,使輕盈的線條與濃郁的顏料產生視覺上的對比,如作品《白樺林》《山城魚池》中,用極具寫意性的線條勾畫山、石、樹木,給人以輕松活潑之美感;二是用調色刀刮出線條,“畫面已鋪滿遠景、中景、近景,黏糊糊的油彩上已無法再增加最前景的樹林、枝丫,于是用調色刀尖側鋒刮去其底色,呈現出素底的樹枝形態。”[3]19這種技法使畫面中的線更有表現力,如在其作品《山花》《野菊》《紫竹院》中,用刀尖刮出植物的細枝末節,在表現物象的同時又豐富了畫面的層次。又如《佛》中,用刀尖刮出佛頭上的小卷發,耐人尋味,使畫面更具有趣味性。
四、結語
作為中國當代畫壇中的旗幟性人物,吳冠中先生的油畫民族化,從意境入手,吸取傳統文化的精髓,立足于本民族特有的審美情趣,將東方韻味融入西方繪畫之中,消除了東西方文化間的隔閡,創作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油畫作品。與此同時,他以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把西方現代派繪畫的構成形式融入到中國畫的創作之中,突破了傳統中國畫幾近僵化的創作模式,從而創造出了具有鮮明個人特色和強烈時代性、民族性的繪畫語言和美術樣式,促使中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碰撞與融合,這都使得他成為了學貫中西的藝術大家。他的藝術實踐和成功經驗對新時代美術創作者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柏靜.淺談吳冠中油畫藝術的中國化[J].大眾文藝,2016(16): 110.
[2]吳冠中.畫里陰晴[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
[3]吳冠中.美丑緣[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王瑞德,新疆師范大學油畫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