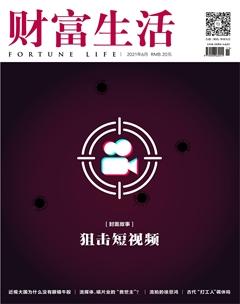被困灰色
最近,一場(chǎng)長(zhǎng)短視頻間針對(duì)作品版權(quán)的大戰(zhàn)把“二次創(chuàng)作”和“同人文化”再度拉入大眾的視野——針對(duì)“XX 分鐘看完一部電影”的打擊,連累同人文化“很受傷”。
正所謂“一千個(gè)人心中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不同受眾自身的閱歷與視角制造了人們對(duì)于文字、繪畫(huà)及影像作品不盡相同的解讀。而同人文化,可以被理解為基于現(xiàn)有作品進(jìn)行的一種二次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者主要是粉絲),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可以是視頻剪輯,可以是繪畫(huà),也可以是文字、手工、攝影、角色扮演(cosplay)等。
作為全球范圍內(nèi)研究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領(lǐng)軍人物,美國(guó)學(xué)者亨利·詹金斯在其代表作《文本盜獵者》一書(shū)中提到,通過(guò)再創(chuàng)作,粉絲群體形成了一種“參與式文化”,不僅將媒體消費(fèi)變成了新文本的生產(chǎn),甚至還是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產(chǎn)。
從這一角度來(lái)說(shuō),同人文化的繁盛,無(wú)疑會(huì)起到反哺原作的作用。像《劍網(wǎng)3》《陰陽(yáng)師》等游戲之所以能長(zhǎng)盛不衰,便是靠繁榮的同人文化穩(wěn)固住了玩家,使得熱度得以延續(xù);沒(méi)有實(shí)體的虛擬偶像初音未來(lái)、洛天依之所以能成為“國(guó)民歌姬”,還登上央視舞臺(tái),靠的也是官方對(duì)二次創(chuàng)作的鼓勵(lì)。
然而無(wú)論在國(guó)內(nèi)還是海外,這種創(chuàng)作長(zhǎng)期以來(lái)都處在一個(gè)曖昧而危險(xiǎn)的灰色地帶。因?yàn)椤胺劢z創(chuàng)作的根本特性,挑戰(zhàn)了媒體產(chǎn)業(yè)對(duì)流行敘事的版權(quán)”,有關(guān)二次創(chuàng)作和同人文化是否屬于“合理使用”的法律討論也始終未能有明確的定論。
圍觀這場(chǎng)長(zhǎng)短視頻間復(fù)雜的利益之爭(zhēng),我們誠(chéng)然支持維護(hù)影視創(chuàng)作者的權(quán)利,反對(duì)盜版和非法使用,但與此同時(shí),我們或許也該從中見(jiàn)到二次創(chuàng)作和同人文化所隱含的積極意義——非營(yíng)利性質(zhì)的二創(chuàng)愛(ài)好者,他們是向內(nèi)容提出反饋的觀眾,二創(chuàng)是他們表達(dá)批評(píng)或贊揚(yáng)的手段和渠道。在這一分享、表達(dá)和爭(zhēng)論的過(guò)程中,他們創(chuàng)造意義,也創(chuàng)造出更有趣的新文本。“一刀切”后,公眾能看到的若只是“被授權(quán)”的二創(chuàng),那是否意味著我們今后所見(jiàn)的,只能是同聲一辭的營(yíng)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