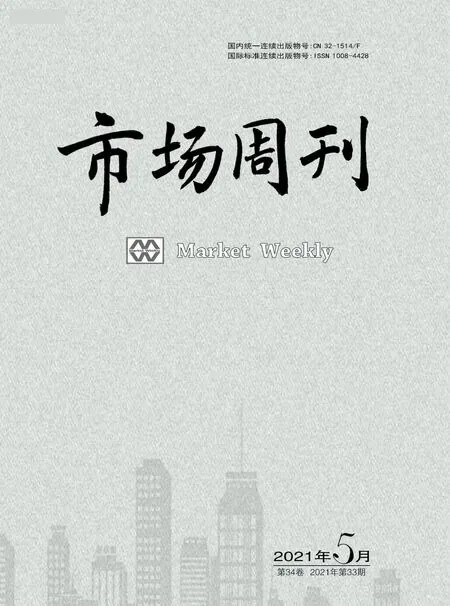中國非農就業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考慮糧食耕種收機械總動力及污染排放的研究
蔡夢雨,柴佳慧,張雨萌
(1.南京財經大學糧食和物資學院,江蘇 南京210003;2.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211100;3.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210037)
一、引言
中國如今處于農村人口普遍非農就業的時代背景下,農業從業人口大量減少,在勞動力投入下降的同時保持產量豐收,勢必會加大機械化投入、高產良種、農藥化肥等新型農業技術的投入。這給中國基于資源和環境雙重壓力的綠色農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農業生產效率的評估不該只是簡單的投入產出問題,更應該是環境污染問題以及糧食安全問題。農業面源污染對地下水以及空氣的污染日益嚴重,農藥化肥殘留被人體吸收后會對人體各個器官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也會破壞食物中的營養物質,嚴重危害糧食安全。因此,學者提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的概念。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在傳統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考慮能耗和污染排放等因素,是農業可持續發展質量的客觀反映。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在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的前提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如果忽略農業生產所造成的環境代價,勢必扭曲農業綠色發展現狀,夸大農業綠色發展績效,提出誤導農業綠色發展的政策措施。只有將環境約束納入發展綠色農業的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地評估中國綠色農業的發展現狀。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社會各界開始關注農業環境問題。但是,中國糧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尚未形成一個科學的標準,研究結論的差距較大。一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界定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李兆亮等把考慮農業面源污染要素的全要素生產率界定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郭海紅等認為碳排放也應納入環境污染的非期望產出中。二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指標選取和研究方法差別較大。許素瓊將環境污染作為非期望產出,而另有學者將環境因素作為投入要素變量,在測算方法上主要采用隨機前沿法和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法。三是樣本時間和空間上選擇的不一致也會導致結論的差距。農業投入與產出和時間的相關性顯著,樣本的時間跨度不一致導致測算出來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很大的差距。高揚等借助空間杜賓模型和偏微分方法發現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4.5%,且按照中、東、西部順序依次遞減。郭海紅等基于新型城鎮化理念構建新型城鎮化質量水平測算指標體系,設計面板門檻模型解析新型城鎮化水平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發現新型城鎮化水平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耦合協調度越高,越利于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此外,農機投入、農業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等也都會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以及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仍有補充的必要。可能存在的邊際貢獻主要是三個方面:①更加科學地選取污染變量,利用單元調查法,計算化肥施用、畜禽養殖這兩部分污染單元,核算的主要污染物指標是總氮、總磷排放量兩類;②中國城鎮化和老齡化的背景下,鄉村人口大量非農就業,對農業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因此非農就業可能會影響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③在面板回歸的過程中分別對空間效應、時間效應和雙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結果更具有科學性。
二、模型選擇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選擇
1.Super-SBM模型
國內外研究者主要運用兩種不同方法對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一是參數方法,如隨機前沿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該法利用生產函數構造生產前沿面,在處理多項投入指標時由于指標間的相關關系,可能會對結果的可靠性產生影響。二是非參數法,如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傳統的數據包絡分析法存在著無法對多個有效的決策單元進行比較的缺陷,而基于DEA基礎上的SBM模型突破了傳統DEA模型的局限,可以對各有效單元之間進行排序和比較,該模型是建立在超效率DEA模型基礎之上的一種非徑向非參數相對生產效率測算方法,是普通超效率DEA模型與非徑向測算方法耦合作用的結果。
假設有n個決策單元(省份),每一個決策單元使用m種投入(i=1,2,…,m),s1種期望產出和s2種非期望產出,向量表達式為:x∈R m,y g∈Rs1,yb∈Rs2。定義矩陣X、Y g、Y b如下:X=[x1,…,x n]∈Rm×n,Y g=[y g1,…,y gn]∈R s2×n,Y b=[yb1,…,其中
定義生產可能性集合為:P={(x,y g,y b)|x≥Xλ,y g≤Y g λ,y b≤Y bλ}。
依據Tone的研究,假定規模報酬可變,則省份i在t年包含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的非徑向、非角度Super-SBM模型為:

s-,s b,λ≥0;i=1,2,…,m;r=1,2,…,s1;t=1,2,…,s2;j=1,2,…,n(j≠k)
2.納入非期望產出的Malmquist指數
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的總體思想是通過構建一種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面,將決策單元與最優前沿面進行對比,然后利用指數法求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Malmquist指數定義如下:

Malmquist指數表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率,該值大于1表示生產率提高,小于1表示生產率降低。Malmquist指數可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effch)和技術進步變化(tech)兩部分:

上式中,(xt,yt)、(x t+1,y t+1)分別為t和t+1時期的投入和產出組合,Et、Et+1分別代表t和t+1時期的效率水平,M t、M t+1分別代表t和t+1時期的Malmquist指數。Malmquist指數表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率,該值大于1表示生產率提高,小于1表示生產率降低。Malmquist指數可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變化技術進步變化。這種分解不僅使得Malmquist可以展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過程,還可以將這種變動進行分解歸因,從而使計算結果更加細化。
3.空間計量模型
將空間相關關系引入基本計量模型中,以反映非農就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空間效應的影響程度。由于使用了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0~2018年的面板數據類型,因此將嘗試構建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以修正建立普通面板模型產生的偏差。空間面板模型分為空間滯后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3種。SLM模型是將因變量的空間滯后因子作為解釋變量加入模型;SEM是將被遺漏的解釋變量以及隨機誤差對空間溢出效應的沖擊考慮到模型中,因此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ε引入空間滯后項;SDM模型中將區域間的交互效應及誤差項的空間關系同時引入模型中,不僅考慮了因變量的空間關聯性,還考慮了自變量空間關聯性,能較好地彌補自變量空間聯系性問題,即非農就業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不僅來自本省份各因素,還受到鄰近省份滯后因素及滯后生產效率的影響,模型修正如下:

式中,GTFPit、UAit、X i t分別為第t期i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非農就業和控制變量;為空間權重矩陣,選擇地理矩陣作為空間權重;W×UAit和W×GTFPit分別為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空間滯后變量,由變量與空間權重矩陣相乘所得。α1~αn、β1~βn為待估系數;μi表示空間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表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誤差項,其均值為0,方差為δ。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1.數據來源
選取2000~2018年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8)、《中國氣象年鑒》(2000~2018)、《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0~2018)和《中國水資源公報》(2000~2018),并在測算之前對相應的經濟指標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調整。
2.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投入與產出變量
投入產出數據在DEA模型的效率評價中具有決定作用,因此開展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評價關鍵在于選取合適的投入與產出變量。投入與產出變量的定義如下:一是投入指標。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是土地、資本和勞動力。首先選擇可以反映這三種要素的投入指標,故參考以往研究,選取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業用水、考慮農業機械總動力和化肥使用量作為投入指標。二是期望產出。期望產出選用各省份的農業總產值來表示。三是非期望產出。農業非期望產出是指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等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面源污染排放物。根據以往的統計口徑,以排放到水體中的化學需氧量、總氮代表農業面源污染。
3.空間計量模型的解釋變量
一是核心解釋變量。考慮到非農就業(UA)的本質是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借鑒Kung、錢龍的研究,使用“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與總人數之比”表示這一變量。二是控制變量。根據錢麗的研究,選取產業結構(IS)、農村基礎教育水平(EDU)以及自然災害(DA)等外在環境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以第一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作為產業結構的代理變量,以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農村基礎教育水平的代理變量,以農田受災率(農田受災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之比)表示自然災害的影響。
機械化程度(MA):采用農業機械數額(萬)與所有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千公頃)的比重來反映。此指標的變化反映了農業機械化程度的配置狀況。
化肥施用程度(AS):采用化肥施用總量(萬噸)與所有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千公頃)的比重來反映。農業生產效率增長實質上是一個要素資源不斷優化配置的過程。此指標的變化反映了農業化肥施用密度的配置狀況。
三、結果與分析
(一)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分析
在進行空間動態面板模型估計之前,首先對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進行面板全局Moran’s I指數檢驗,以期探究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為了更好地反映農業經濟系統在地理鄰近或非地理鄰近地區的空間差異,研究采用鄰接空間矩陣定義全要素生產率的相互鄰接關系。基于此,運用MATLAB軟件對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數進行測度。由表1可知,中國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Moran’s I指數為正,且均保持在0.11以上,表明中國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的空間正自相關性,具有明顯的空間聚類特征,全要素綠色生產率高值省區常與高值省區集聚分布,全要素生產率低值省份也常被其他低值省份包圍。這有可能是受鄰近省區產業、人口等功能空間轉移而產生的空間上相互作用與關聯效應的影響,因此可運用空間計量面板模型進一步探討非農就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溢出效應。

表1 2000~2018年綠色全要素率Moran’s I統計值
(二)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若用傳統的OLS回歸分析必然會忽略非農就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空間上的關聯性與互動性而產生的估計誤差,因此可選擇基于空間模型形式的設定檢驗。首先可通過Wald檢驗,判斷SDM能否簡化為SAR和SEM。通過WALD估計發現,統計值有1%的顯著性水平,故選擇空間杜賓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LM檢驗和Robust LM的統計值均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拒絕了無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的原假設,此時應該考慮更具普遍形式的SDM。

表2 LM Error和Robust LM Error統計值
對于SDM,若隨機誤差項與某個解釋變量相關,則為固定效應模型;若隨機誤差項與所有解釋變量均不相關,則為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在處理面板數據時首先需要確定使用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其次采用豪斯曼檢驗進行模型個體效應的判別。檢驗結果顯示,豪斯曼統計量為-31.863,均接受原假設,且p值為0.019<0.05,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綜上所述,空間杜賓固定效應為本研究的最佳模型,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空間杜賓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論文采用四種模型分別進行了回歸,根據模型的擬合優度和穩健性,采用空間固定模型(即模型2)的回歸結果。該模型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非農就業對本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對周邊省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有很顯著的空間溢出正效應。原因可能是伴隨著本省非農就業比重的提升,特別是家庭非農收入的提高促使農戶有條件以雇用、機械的方式替代傳統的勞動生產,現代綠色無機農業的高效作業會一定程度地促進本省農業綠色發展。另外,本省的大規模非農勞動力的流動與轉移往往會為那些區位優勢顯著的省份帶來技術的積累。而從空間交互效應來看,優質勞動力資源的外溢能顯著提升人才轉移省份的創新生產能力,從而對本省的農業就業產生沖擊,農業勞動力的縮減使得本省轉向規模化、高效化的農業綠色生產模式。
在產業結構方面,產業結構(IS)升級對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影響系數為正,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省域產業結構升級會提升本省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這有可能是由于本省的第一產業發展水平較高,能更好地依托科技創新,運用和推廣農業先進生產技術,從而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產業結構空間滯后項(W×IS)回歸系數為負,說明本省區域經濟發展能夠對本省綠色要素資源產生明顯的“吸附”作用,區域產業集聚效應會對本省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化肥施用強度(AS)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化肥面積的增加和農村收入水平的上升對本區域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具有負的影響。究其原因,是過量的化肥施用和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使得農村生態環境日趨變差和農業生產積極性不高,造成農村土地撂荒景象呈常態化,土地資源生產要素極大浪費,這些無疑束縛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受教育水平(EDU)和受災情況(DA)對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一方面是由于大量農業勞動力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成為影響農業生態建設和產業空間布局改善的瓶頸,嚴重制約農業科技高質量推廣,另一方面是由于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在空間上呈現條狀、碎片化分布,但近年來大規模的流域性災害并未發生,故而不會對農業綠色綜合生產產生影響。
(三)直接和間接溢出效應分析
空間杜賓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證實了非農就業及控制變量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正向或負向影響,但其回歸系數包含了鄰接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互相影響的反饋效應,無法準確反映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的大小,因而需要剔除反饋效應。通過空間杜賓模型偏微分方法將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因素的總效應進行分解,結果見表4。

表4 總效應分解
從核心解釋變量的分解結果來看,非農就業(UA)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非農就業對本地農業綠色生產和鄰近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較為明顯。非農就業直接效應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說明隨著人民群眾對非農產品日益增長需求的上升,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進城就業,與之相伴的是農業就近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迅猛發展,勞動力、土地等要素逐漸流失,無疑會對本地區的農業生態建設產生影響。非農就業比重的日益擴大對于鄰近地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具有正向影響。這種正向溢出效應的產生,可能是由于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先前的集中于傳統農業逐漸流動到鄰省的第二、三產業等。這不僅改變了城鄉間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還會對鄰近地區的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產生競爭和溢出效應,從而促進鄰近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從其他控制變量的分解結果來看,產業結構(IS)對農業全要素生產效率的間接效應均為負向。這說明隨著第二、三產業比值的提高,將對鄰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到明顯的阻礙作用。究其原因是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農業總產值之間存在“U”型曲線關系,農業產業結構的單一化、非均衡發展會造成區域差異越發擴大化,不利于實現農業綠色化科學化治理。一些地區具有良好的發展優勢和可觀的就業機會,吸引了鄰近地區的資本、人才和技術等要素,故而使得鄰近省份的勞動技術變遷滯后。從表4中分解結果的溢出效應(即間接效應)來看,化肥施用強度(CD)和農業機械密度(MD)因素對相鄰省農業生產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化肥的有效配置施用和農業機械的使用是基于技術要素的空間聚焦,對鄰近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種正向溢出效應可能源于技術的省際流動及模仿學習效應。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依據2000~201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采用SBM-ML指數法測算了各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運用空間杜賓模型分析了非農就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其空間溢出效應,得到如下結論:①2000~2018年中國省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空間正自相關性,空間分布上具有較強的依賴性;②非農就業作為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因素,其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明顯的空間集聚效應,非農就業化水平對本省和鄰近省份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顯著,教育化水平和農業受災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作用不顯著;③各變量的間接溢出效應影響明顯,進一步證實了空間地理因素在區域農業綠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建議:①中國綠色農業發展的道路任重道遠,傳統的生產要素不能反映綠色農業的實際發展情況,環境監管部門應該監測更多的農業污染排放物,讓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非期望產出更加的全面,能科學有效地對農業發展的實際成就和問題進行測算,為農業綠色發展提供參考尺度;②加快新型城鎮化發展,積極提供非農就業機會,提高農戶非農收入,緩解其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資金約束,促進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實現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③各地區要進一步重視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村教學質量,培育農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感;④進一步推廣農戶采用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提升化肥減量增效技術,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提高農產品質量,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