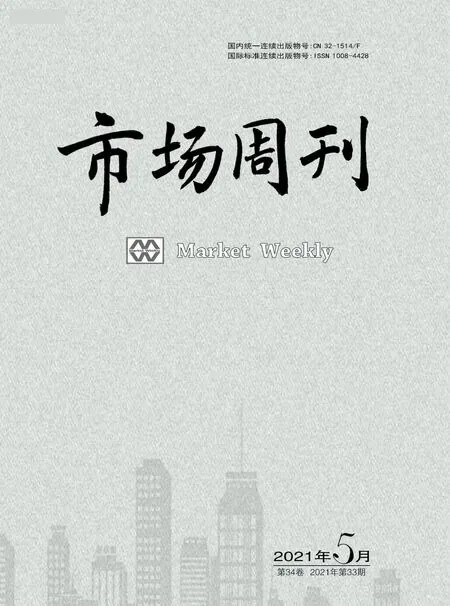環境規制對我國制造業經濟增長的影響
——基于行業碳排放分類
黃 素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430070)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我國實現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作為唯一具備聯合國工業體系中所有門類的國家,毋庸置疑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但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高消耗、高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國的環境造成了傷害。目前,我國越來越注重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著力兼顧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
制造業是我國的立國之本,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過去長期依賴粗放的增長模式,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環境規制是一國為了處理環境污染、促進環境保護所制定的政策,但環境規制真的能實現我國在發展制造業的同時兼顧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嗎?環境規制對不同污染強度的制造行業的影響力存在差異性嗎?是否有必要對不同污染強度的制造行業制定不同強度的環境規制政策呢?
二、文獻綜述
波特認為,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將增加企業的成本,但從長遠來看,只要環境規制力度合適,就能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促進企業減少污染排放,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強產業競爭力(Porter,1991)。不少學者已對“波特假說”進行了檢驗:趙紅研究環境規制對中國制造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在中長期內對中國制造業技術創新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張成等利用中國大陸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工業部門數據對波特假說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東部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與企業生產技術之間存在“U”型關系,而在西部,兩者的“U”型關系尚不顯著;Cai等的研究表明直接環境規制對我國企業的綠色科技創新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環境規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張小筠等將制造業分為高、低競爭性的行業,分析制造業的綠色發展是否會受到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的異質性影響,結果顯示環境規制對制造業整體綠色發展的影響呈“U”型變化;王玉燕等實證分析表明環境規制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存在“U”型關系,并且技術進步會強化正向調節作用;陳璇等運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污染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都存在“U”型特征;雷玉桃等同樣基于我國省份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存在非線性影響。
綜上所述,目前大量研究結果表明了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產業高質量發展呈現非線性影響,但大多數的研究運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環境規制對不同省份產業發展的異質性影響,少數文獻研究環境規制對我國不同排放碳程度制造業經濟增長的影響。行業的碳排放是對行業制定環境規制政策的一大重要依據,而制造業更是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因此論文基于碳排放對我國制造業進行分類,研究環境規制對不同碳排放程度制造業影響。
三、行業碳排放估算與制造業碳排放程度分類
(一)行業碳排放估算
能源消耗計算CO2排放方法是從消費端計算能源實物消耗所產生的CO2,這是目前計算CO2排放較為成熟的一種方法。本文根據IPCC提供的計算方法并借鑒劉傳江和趙曉夢的方法計算我國制造業行業的能源CO2排放。

式中,Ei為原煤、焦炭、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和天然氣七種能源的實物消耗量;NCVi為第i種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CEFi為第i種能源消費標準量的碳排放系數;COFi表示第i種能源的碳氧化系數;44、12分別為二氧化碳和碳的相對分子質量。
(二)制造業碳排放程度分類
不同的制造業因為生產工藝、流程、產業特性不同,在生產過程中使用能源類型和數量都會有差別,因此碳排放程度也不同。若對所有制造業制定統一程度的環境規制,會忽略不同碳排放程度制造業對同一環境規制程度的“適配度”,有可能對制造業的經濟增長和環境效益產生弊大于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計算出各制造業的能源碳排放來對制造業進行分類,分別探討環境規制對不同碳排放程度制造業的影響。
論文以我國27個制造業行業為研究對象。由于我國制造業行業的劃分在2011年前后有所差異,為了使數據更加連續且提高數據分析的準確性,橡膠塑料制品業在2011年之前劃分為橡膠制品業與塑料制品業,因此,進行合并;2011年后,交通運輸裝備制造業劃分為汽車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等交通運輸裝備制造業,同樣采取合并的處理方式。由于數據統計不全或數據差異太大,為了使數據更平滑,論文剔除了其他制造業、廢氣資源綜合利用業以及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經過合并、剔除處理最終剩下27個制造業行業。
根據前文計算公式,估算27個制造業行業2010~2017年碳排放量,相關的能源消耗數據均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對各行業的年平均值進行線性處理。

對27個制造業分類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業碳排放程度分類

續表
由表1可見,低排放程度的制造業主要是偏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如計算機通信、儀器表制造業等;中等排放程度的制造業主要有各設備制造業以及醫藥、化學制品業等;高排放制造業則具有高消耗的特征,主要有農副食品加工業、石油加工業等。
四、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定
靜態面板數據模型主要包括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采用Hausman檢驗選擇兩種模型,如表2所示檢驗結果表明,三類制造業均拒絕原假設,靜態面板數據模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因此,論文先運用固定效應進行回歸分析。相比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把被解釋變量滯后期納入模型能更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故再運用系統GMM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式中,Gi,t為第i個行業第t年的增長率,G i,t-1表示滯后一期的增長率;ERi,t表示第i個行業第t年的環境規制強度,表示環境規制強度的平方項;PFi,t為第i個行業第t年的營業利潤;LPi,t為第i個行業第t年的勞動生產率;EPi,t第i個行業第t年的能源生產效率;SIZEi,t為第i個行業的規模;ESSi,t表示第i個行業第t年的要素結構;u t表示個體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表2 Hausman檢驗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Gi,t
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反映了該行業的經濟運行狀況,但絕對值不能反映變動的狀態,因此由t+1年相對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變化值除以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來計算增長率反映制造行業的動態變化。各年的數據折算成2000年的不變價以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原始的數據來自《2000中國統計年鑒》。
2.核心解釋變量:環境規制強度
環境規制強度的測算方法主要有基于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測算、基于環境污染處理費用支出的測算、基于自然試驗和替代指標的衡量方法以及綜合評價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本文主要研究碳排放,因此選取第一種方法,環境規制強度(ER)用各制造行業的碳排放總量除以t年主營業務收入來表示。原始的數據都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0》《2000中國統計年鑒》。
3.其他控制變量
營業利潤PFi,t反映行業的盈利能力,由第t年的營業利潤除以主營業務收入來表示,消除了價格變動;勞動生產率LPi,t由第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除以勞動力來表示,本文以各行業平均用工人數來表示勞動力,主營業務收入處理為不變價;能源生產效率EPi,t由第t年的主營業務收入除以能源消耗來表示,能源消耗用標準煤能源消耗總量來表示,主營業務收入處理為不變價;行業規模SIZEi,t由第i個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除以該年所有行業主營業務收入之和來表示;要素結構ESSi,t由行業總資產除以平均用工人數來表示,總資產處理為2000年的不變價。數據來自《2000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局、EPS數據庫。
五、實證分析
(一)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和碳排放時序變化
圖1 、圖2分別反映了三類不同碳排放程度制造業2010~2017年的環境規制強度和碳排放的時序變化,如圖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高碳排放行業的環境規制強度遠遠高于低、中等碳排放行業,而中等碳排放行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又高于低排放行業,這說明了國家一直把減污減排的重心放在高排放的行業,而中等、低排放強度行業的環境規制較為寬松。從時間變化上來看,三類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總趨勢是不斷減弱的。圖2反映了三類制造業碳排放2010~2017年的時序變化。高排放行業2010~2013年排放有上升趨勢,但2010~2017年,碳排放還是在減少;中等、低排放強度行業的碳排放在研究期都處于下降趨勢。因此,從一定程度可以解釋環境規制強度的減弱。

圖1 三類制造業的環境規制

圖2 三類制造業的碳排放
(二)回歸分析
1.固定效應模型
表3 為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三類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體現為U型,其中,高排放制造業呈倒U型;中等排放制造業和低排放制造業呈U型。但變量系數顯著性不強且模型整體擬合度不佳,模型可能受到變量內生性的影響。為了更加準確地探討環境規制對制造業經濟增長率的影響,論文運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表3 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續表
2.系統GMM模型
系統GMM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表中統計了高排放、中等排放和低排放制造業的動態面板模型的回歸結果。對于動態面板模型,如果Sargan檢驗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為每個模型選擇的工具變量是合理有效的;殘差序列相關檢驗AR(2)證明原序列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從分析結果來看,系統GMM比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系數顯著性更好,因此,論文以系統GMM的回歸結果為分析重點。

表4 系統GMM回歸結果
由回歸結果可知,在三類制造業中,環境規制一次方對增長率的影響系數為負;二次方影響系數為正,并且回歸結果都具有強顯著性,因此環境規制對增長率的影響均表現為U型。由此可見,該研究結果也驗證了波特假說,環境規制強度存在一個“拐點”,在到達“拐點”之前,環境規制讓制造企業的運行成本增加,影響了經濟增長率的增長;當越過該“拐點”,環境規制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帶來的增長效應將彌補環境規制造成的額外成本,經濟增長率因此增加。此外,從固定效應模型來看,環境規制對三類制造業增長率的影響也呈U型,佐證了動態面板模型的回歸結果。
高排放制造業有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造紙業、石油加工等行業,這些行業都屬于高消耗、高排放的行業。從回歸結果來看,環境規制強度的“拐點”為1.26,而目前的環境規制強度為1.36,說明高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遠沒有到達補償效應超過成本效應的“拐點”。中等排放制造業環境規制的“拐點”為0.1,目前的環境規制強度為0.07,中等排放制造業與高排放制造業一樣,環境規制強度沒有到達補償效應超過成本效應的“拐點”。低排放制造業主要有計算機通信、儀器表制造等行業,這些行業有技術密集度大于能源密集度的特點。低排放制造業環境規制強度的“拐點”為0.02,目前的環境規制強度為0.01,因此,低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帶來的補償效應也不足以超過成本效應。雖然三類制造業目前的環境規制強度均沒有超過“拐點”,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類制造業的“拐點”不同,低排放制造業比中等排放制造業更易到達“拐點”,而中等排放制造業又快于高排放制造業到達,因此,如果對所有行業制定統一的環境規制強度,環境規制對不同排放水平制造業經濟增長率的異質效應將被忽略。
六、結論與建議
論文基于碳排放對制造業進行分類,分為高、中等、低排放行業,分析環境規制對不同碳排放程度的制造業的影響,通過構建動態和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高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高于低排放制造業,低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又高于低排放制造業,這說明了高排放制造業是減污減排的重點,而中等、低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較為寬松。
(2)三類制造業環境規制ER一次方對經濟增長率G的影響系數為負、二次方為正,ER對G的影響均呈U型。
(3)三類制造業目前的環境規制強度都沒有到達補償效應超過成本效應的“拐點”。
(4)低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強度比中等排放制造業更易到達“拐點”,而中等排放制造業比高排放制造業更容易到達。
依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持續對高排放制造業制定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具有高消耗特征的高排放制造業是減排的重點,但環境規制力度一直太弱,環境規制政策反而成了阻礙行業增長的因素。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石油加工業等行業都是基礎行業,依靠高投入帶動高產出而技術密集度低,因此更應該對這些行業加強環境規制力度,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提高生產的技術,降低消耗,實現環境規制對行業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的雙重效益。
(2)適度增強低、中等排放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力度。低、中等排放行業相比高排放行業技術密集度更高,CO2排放也較低,這些行業的環境管制容易被忽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業的環境規制力度接近于“拐點”,因此只要適度加大力度就可以實現環境規制的補償效應超過成本效應。
(3)尋求多元環境規制手段。論文所度量環境規制強度結果表明,三類制造業的環境規制力度在2010~2017年一直偏弱,這種強制性的環境規制只能間接激勵行業進行技術創新、改善環境,因此政府可以使用激勵性的環境規制手段對企業進行補貼,直接激勵企業采用更加清潔的生產技術和工藝,進行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