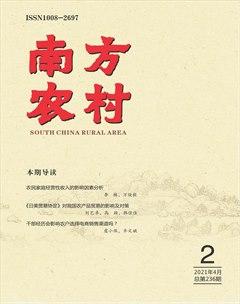農村“三產融合”視閾下數字經濟發展的法制思考
謝曉雯 蘇卓君
摘? ?要:數字技術能促使信息迅速的在一二三產業中傳遞和交換,其帶來的經濟效應有效地貫通了農村一二三產業的分界,對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大有裨益,是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通過對杭州、廣州、珠海、重慶四市農村“三產融合”中的數字經濟實踐比較考察發現,當前在農村“三產融合”中數字經濟仍主要體現為電商經濟,少部分則以科技賦能,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主線的多要素產業園經濟,然而目前關于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的法律討論暫且較少,故而應當從法律層面健全完善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的相關制度保障。
關鍵詞: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農村產業數字經濟;法制化策略
中圖分類號:F32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697(2021)02-0045-05
在當前農村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進程中,互聯網技術的影響力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愈發明顯,應用互聯網技術帶來的經濟效益日益提升。其中,由互聯網技術催生出的這種新型經濟形態即為數字經濟,其具備極強的滲透性,能促使信息迅速的在一二三產業中傳遞和交換,有效地打破了三大產業的邊界,推動了三大產業一體化的進程,對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大有裨益[1]。此外,數字經濟與生俱來的邊際效益遞增性、外部經濟性和可持續發展性對于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以下簡稱“三產融合”)也具有深刻意義,是推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發展進而推動鄉村振興的絕佳突破路徑。
一、數字經濟對農村“三產融合”的意義分析
在重要性方面,數字經濟以電子數據信息作為載體,具備天生的優勢。相對于傳統的農村信息流轉方式,數字經濟克服了農村交通不便和人文不通等種種弊端,只要存在網絡,已獲取的信息便能夠在產業間形成共同、協調、公平、高效、多維的流轉,大大減少了經濟上的“腳底成本”和信息獲取成本、資源上的非必要消耗和可能造成的環境上的污染惡化等,提高了經濟效率;而未獲取的信息也能通過網絡搜索等方式引入或分析獲得,由此進一步擴大信息技術來源,創建了農戶、投資方、消費者共贏的高效循環,為農村“三產融合”提供了良好穩定可持續的共贏環境,具有良好的可持續發展性。
在必要性方面,數字經濟具有多重融合性。首先,內容方面,在農村“三產融合”的實際工作中,“互聯網+模式”已是一種多地都推行的模式,從生產加工到銷售,甚至休閑旅游,多地以互聯網技術為媒介進行傳統農業的轉型升級,以此煥發“三農”的新活力。其次,主體方面,數字經濟刺激了產銷融合的產生,越來越多的農戶通過電商平臺或直播帶貨等形式在網絡上銷售農產品,較少了流通環節和交易成本,提升了生產效率,越來越多的主體分享到了數字經濟帶來的紅利。最后,城鄉融合是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而數字經濟亦能夠在推動農村“三產”融合的同時直接作用于城鄉融合。具體而言,數字經濟通過架設平臺渠道連接農村與城市間的供給與需求,個體能夠基于相對透明和公平的平臺進行綜合評估而做出理性、經濟的最優選擇,進而實現生產資源或最終產品在城鄉間的最優配置或組合,各方均能獲得最大效用,進而進一步推動城鄉間各種要素的流轉,逐步縮小城鄉間的差距。
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對推動農村“三產融合”進程十分重要和必要,基于此,研究在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的法律制度保障,為農村“三產融合”工作中發展數字經濟保駕護航便顯得十分關鍵。
通過查閱文獻發現,在數字經濟法律層面的討論上,有學者指出,作為一種基于通信技術而發展起的新型經濟,數字經濟面臨電子虛擬世界中數據安全的問題,數據治理、網絡治理和平臺治理是需要攻克的難題,治理及時性、系統性、科學性都有待強化[2]。另有學者則從經濟法的角度對維護數字經濟網絡市場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進行了探討,指出數據產權制度不明晰[3],應對掌握數字經濟技術,在市場上具有支配地位的企業加強監管[4]。還有學者基于愛莫森的協同治理統一模型提出數字經濟與社會生產生活渾然一體,治理復雜,更新迭代快,亟需構建多元主體間的領導協調機制、信息公開與信息共享機制和法律和規則體系協同機制[5]。可見,目前學界關于數字經濟法律層面的討論較少且大多是從整個國家、社會的維度對其可能面臨的挑戰與不足進行分析,鮮有學者針對農村數字經濟進行法律層面的深入探討和剖析,從農村“三產融合”的維度對數字經濟進行實例法律討論的更是前所未有。
綜上所述,及時發現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存在的法律漏洞或待完善之處,將有利于更為科學地為當地政府推進農村“三產融合”和數字經濟提供政策參考,提升政策有效性。本文將結合多市的實例,通過現象看本質,通過對當前數字經濟在其農村“三產融合”中的具體作用路徑和影響機理進行實例分析,探討實際應用中數字經濟可能存在的法律問題及對策,所形成的結論可以為相關機構制定相關條例策略提供有益導向,有助于達到促進農村“三產融合”、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進而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
二、數字經濟在農村“三產融合”中的作用路徑和影響機理分析——以多市實踐為例
在三產融合方面,作為“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的杭州市大力推動數字技術與農業、制造業、服務業深度融合,以數字經濟為抓手發揮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疊加效應。首先是全面發展農村電子商務。杭州加快數字經濟在農業流通領域的實現與應用,構建縣鄉村三級聯動、政企農三方互動的農村電商服務平臺和銷售網絡體系,加快生鮮農產品、特色鄉村食品線下體驗、網上直銷相結合的農產品新零售模式,實現產品提升、品牌升級、渠道拓展。在此基礎之上,杭州深化“互聯網+”發展經營機制,促進電子商務與民族鄉村經濟深度結合,建成一批民族村電子商務專區,通過數字化平臺,拓寬推動少數民族群眾增收途徑,加強對民族鄉村發展的高效精準管理。其次是積極探索創新體制機制,杭州以特色村寨、特色民宿、特色農場建設為著手點,培育一批優秀的發展典型,深化以各類合作社為主體的新型合作機制,完善農合聯組織運行機制,提升鄉村產業組織化經營水平。最后,杭州積極推進 “互聯網+農村物流”,加快農產品儲藏、運輸和冷鏈物流體系建設,打造了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的公共服務平臺。
廣州市積極探索數字鄉村建設。通過扶持發展荔枝等特色產業,借助互聯網加速宣傳推廣吸引客流,鼓勵發展農村電商、休閑農業、餐飲民宿,繼續推進精品村、風情小鎮、精品示范線、村落景區建設,以此加快農村一二三產融合。具體而言,2019年,廣州從化區搶先布局5G下鄉,加快推進現代農業產業園建設,高標準規劃建設艾米稻香小鎮,打造集“生態農業產業”“數字農業產業”“智能農業產業”于一體的景觀田園樣板。艾米在第十屆全球移動寬帶論壇上,向全球首發艾米5G數字農田成果,率先構筑農業領域的萬物互聯網絡。廣州白云區在“三產融合”方面則注重利用數字技術發展電子商務,推動農村電商、專業電商、跨境電商集聚發展、規范發展,支持建設一批農村電商產業基地及示范園,2020年全區創建2個以上電商專業村。廣州增城則是發展精細技術,加快數字農業和現代農業技術創新應用,落地業界首個“5G+數字農業”項目,規劃建設增城5G智慧農業試驗區。打造環保高效型畜牧業,建設現代生態農牧一體化產業基地,規劃應用物聯網技術,打造美麗生豬牧場。廣州南沙加快推進“南沙現代漁業產業園”,推進廣州南沙現代農業產業集團公司與中國農業大學國家數字漁業創新中心合作,共建國家數字漁業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分中心。
珠海斗門在“三產融合”中則積極推動“互聯網+現代農業”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建設現代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支持農村淘寶、農業電商平臺、農業電商孵化器和農產品直銷平臺、供港澳農產品配送中心建設,到2022年建成兩個農村電商產業園和孵化器。
重慶市在農村“三產融合”方面的數字技術應用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用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利用互聯網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二是提速發展“互聯網+農業”,擴大農業物聯網示范應用,優先推進生豬、柑橘、榨菜等全產業鏈大數據建設;三是大力發展農村電商,實施“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依托市供銷合作社建立市級電商平臺,讓特色農產品賣得快、賣得遠、賣得好。
通過以上多個市的實踐分析可以發現當前在農村“三產融合”中數字經濟仍主要體現為電商經濟,少部分則以科技賦能,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主線,結合生態、文化等進行生產加工服務銷售為一體的現代產業園。數字技術在其中更多的是充當媒介工具或催化劑,通過信息的傳遞交換提升產業內、產業間發展的效率,通過信息源的擴展激發產業內的潛能,深化產業間的融合程度。因此,如何去保障在此過程中應用數字技術、發展數字經濟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法律層面如何保障通過數字技術傳遞的信息的安全性,如何對其進行監管便成了尤為關鍵的命題,這對于發展可持續的數字經濟進而促進農村“三產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的法律思考和策略
(一)構建多方位監管體系,補全法律監管漏洞
1. 政府應加快構建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的監管體制
數字經濟是近年來新興的經濟發展形態,其最大優勢在于實時性和高效性,而農業則具有弱質性,再加之農村地區相對閉塞,在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天然面臨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雙重影響,三種產業的交融以及新興經濟發展形態可能由此碰撞出眾多矛盾與沖突,如果單純由市場本身進行調節,極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市場失靈。因此,作為市場宏觀調控的主體,國家政府及其地方有關部門應當采取相應的調控手段對農村產業數字經濟市場進行適當干預。
據了解,2015年至202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等相關部門出臺了十余部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相關政策,推動數字經濟在農村中的應用與發展。但在農業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浪潮下,政府對農業數字化產業的監管體制仍有待更新完善,應加快構建政府主體對農業數字化市場的監管體制,對農業數字經濟市場的行為進行行政監督和有效規制。具體而言,縣級以上政府須承擔促進數字鄉村振興的主體責任,通過建立“三產融合”發展中數字經濟的具體目標責任制和實績考核評價制度,將“三產融合”及數字經濟目標任務完成情況納入本級人民政府相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考核評價內容,將第三方評估作為財政專項資金分配或者安排的重要參考。
2. 行業協會發揮監管職能
行業協會作為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社會中介性組織,既能夠代表所在行業的整體訴求,也可以作為政府與企業間溝通的媒介。我國《反壟斷法》第十一條規定,行業協會應當加強行業自律,引導本行業的經營者依法競爭,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農村“三產融合”發展過程中,各地的農業行業協會應當關注區域內各單位對數字技術的應用情況,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利用行業的慣例特性,引導行業內部各企業間良性競爭,維護市場良好秩序。
3. 社會群體積極進行監督
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發展除了從經濟法角度的特殊社會關系主體落實監管以外,還可以通過社會群體以及平等主體進行監督。政府、企業在實施促進“三產融合”,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目標過程中,應當自覺接受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新聞媒體等社會各方的監督,同時,我國《反壟斷法》借鑒國際經驗,引入了“寬大制度”的概念,鼓勵平等主體之間的監督與舉報,相關經營者主動向司法機關坦白違法以換取減輕處罰,盡早瓦解壟斷協議,恢復市場良性競爭秩序。
(二)規范農村產業數字經濟中對數據市場的監管
數據是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基本要素,隨著我國要素市場的全面放開,數據這一重要的市場要素將會成為商品進入市場,由市場決定其價格,這也意味著在未來,數據權屬的不確定性將會大大增加。
從經營者的角度看,農村產業數字經濟離不開數據與算法這一環節,如果互聯網企業對農業數據與算法這一環節實施控制并在市場中形成相對優勢,便容易出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優勢地位,限制農村數字化產業鏈上其他環節的發展,對農村“三產融合”及數字經濟的發展造成重大的沖擊,甚至會對國家的正常經濟秩序帶來巨大威脅。對此,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近日公布了《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細化了對平臺經濟領域有關壟斷行為的定義,這意味著我國反壟斷從傳統行業延伸至網絡經濟領域,農村電商經濟作為農村“三產融合”數字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平臺領域經營者的行為必將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規制。然而,平臺經濟屬于典型的“三新經濟”,其經營業態、商業模式和競爭方式日新月異,從長遠來看,仍需通過制定法律規范加強對平臺經濟反壟斷的監管。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個人信息將會以數據的方式流入市場。全面放開要素市場意味著個人信息被視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同理,農村產業對個人信息保護將會成為重要關注點,為了避免農村電商對客戶個人信息的泄露,防止橫向卡特爾所造成的個人信息濫用,對此,我國正加緊立法,及時填補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缺口,在《民法典》人格權編中明確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制度,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也已出臺。但面對互聯網的海量信息,數據市場高速運轉,大部分消費者并不知道個人信息被誰泄露,甚至對自己個人信息被交易的事實并不知情,這對于消費者自身維權存在很大的阻礙,在未來的數據監管還需進一步完善。
(三)完善農村產業數字經濟責任制度
實現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的有效性監管,還需要建立健全完善農村產業數字經濟責任制度。通過健全法律責任制度,規范農村電商的個體行為,堅持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對農村電商經營者的違法行為進行追究,要求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并進行損害賠償。目前,我國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近日出臺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均明確了主體的法律責任。這些法律所規定的行政處罰金額有限,對于某些企業的約束力仍然有所欠缺。為此,政府有必要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將違反競爭規則、違法處理個人信息等不良電商經營者納入“負面清單”,限制其商業行為,從而通過落實法律責任的承擔,加強農村數字化企業對自身的行為規范。
(四)提高農村電商經營者準入門檻,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
近年來,我國農村電子商務行業迅速發展,主要以獨立個體商戶為主,具有零散性、無序性、多棲性等特點。2019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1.7萬億元,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3975億元[ 數據引自《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9》],為農村脫貧攻堅注入強大動力。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農村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會達到一個新高度。面對數字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紅利,農村電商經營者數量將持續增加,競爭也將愈發激烈。
電商平臺與農村電商經營者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利益關系,電商平臺為了追求用戶數量和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簡化對個體商戶資質的審核,而農村電商個體戶的素質參差直接導致農產品質量參差不齊,進而直接導致產業鏈上的環環隱患。因此,政府需要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生產經營許可證制度,嚴卡農村電商個體戶的準入門檻,同時,產品質量監督部門還要對農村電商經營者所售產品的質量進行不定期的抽查和檢驗,建立健全數字經濟下農產品質量監管制度,以此維護農村電商領域的運營秩序。
(五)建立農村產業數字經濟發展的長效發展的法律機制
隨著“十四五”規劃實施綱要的出臺,農村產業數字經濟未來五年內發展目標逐漸明晰。為了使數字技術能夠有力支撐農村“三產融合”工作實施,保障農村產業數字經濟長效發展的法律機制的應當受到關注和重視。把握農村“三產融合”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構建穩定的法制框架,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下規范農村“三產融合”中發展數字經濟的權利和義務,對相關主體的行為模式進行約束,對促進農村“三產融合”從而促進鄉村振興長效平穩發展有著深刻意義。
參考文獻:
[1] 左燕.數字經濟促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路徑研究[ J ].農村經濟與科技,2020,31(16):143-144.
[2] 何波.中國數字經濟的法律監管與完善[ J ].國際經濟合作,2020(05):80-95.
[3] 陳兵.法治視閾下數字經濟發展與規制系統創新[ 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04):100-115.
[4] 王欣偉.數字經濟的經濟法規制問題研究[ J ].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31(01):82-86.
[5] 杜慶昊.數字經濟協同治理機制探究[ J ].理論探索,2019(05):114-120.
(責任編輯:羅湘龍)
Legal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hree Industry Integration"
XIE Xiao-wen,SU Zhuo-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rapid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ts economic effect effectively connects the boundaries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It i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ural industries in Hangzhou, Guangzhou, Zhuhai and Chongq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ural industries is still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commerce economy, and a small part of it is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multi factor industrial park econom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main line. However, the current legal discussion on the digital economy of rural industry is not clear.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relevant system guarante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legal level.
Key words: Rural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ntegration;Rural Industrial Digital Economy;Legalization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