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tài)殖民主義與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
摘要: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是國(guó)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生態(tài)殖民主義既是生態(tài)范疇又是經(jīng)濟(jì)政治范疇;其實(shí)質(zhì)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應(yīng)享有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的雙重剝奪,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新”的殖民形態(tài);其表征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殖民化擴(kuò)張、生態(tài)資源的系統(tǒng)化掠奪、生態(tài)壁壘的制度化設(shè)計(jì);其生成的邏輯體系是,歐洲中心主義是其思想根源,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是其物質(zhì)基礎(chǔ),生態(tài)資本化是其邏輯主線,生態(tài)政治化是其前提條件。生態(tài)殖民主義給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生態(tài)安全構(gòu)成了嚴(yán)重威脅,必須超越生態(tài)殖民主義,在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中構(gòu)筑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屏障,促成全球生態(tài)善治。
關(guān)鍵詞:生態(tài)殖民主義;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資本邏輯;生態(tài)正義
中圖分類號(hào):D035.29;X2;X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3-5595(2021)02-0081-07
生態(tài)安全是國(guó)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是契合新時(shí)代的新安全形態(tài)。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關(guān)系到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持續(xù)發(fā)展、民族國(guó)家的長(zhǎng)治久安等,恰如諾曼·邁爾斯在《最終的安全——政治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基礎(chǔ)》中談到的,生態(tài)資源安全是國(guó)家生存的基礎(chǔ),生態(tài)資源退化終將導(dǎo)致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退化和國(guó)家的政治結(jié)構(gòu)混亂。發(fā)展中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布控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這一威脅試圖剝奪發(fā)展中國(guó)家應(yīng)享有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憑借其經(jīng)濟(jì)優(yōu)勢(shì),獨(dú)占環(huán)境收益而輸出環(huán)境污染,并以保護(hù)環(huán)境為借口,干涉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一系列行徑”[1]。目前,學(xué)界同仁已經(jīng)取得了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問(wèn)題研究的豐碩成果。不過(guò),系統(tǒng)探討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受到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具體威脅、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表征和生成邏輯、超越生態(tài)殖民主義邏輯以保障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之可行性等問(wèn)題,仍是學(xué)界研究需要進(jìn)一步深入拓展的方向。
一、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主要威脅
在民族資本日益成為國(guó)際資本、世界各國(guó)日漸“寰球同此涼熱”的時(shí)代,生態(tài)殖民主義已然構(gòu)成對(duì)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主要威脅。因此,必須首先剖析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及其表現(xiàn)特征。
(一)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
生態(tài)殖民主義不同于歷史地理學(xué)家阿爾弗雷德·克勞士比1986年提出的“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概念。阿爾弗雷德·克勞士比用“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概念描述歐洲殖民者對(duì)澳洲、美洲、非洲的“生物侵害”①。據(jù)詞源學(xué),“生態(tài)”在古希臘意為“住所/棲息地”,泛指生物及其環(huán)境間構(gòu)成的生存樣態(tài)。進(jìn)而,生態(tài)不僅指生物生態(tài),也包括經(jīng)濟(jì)生態(tài)、政治生態(tài)、社會(huì)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精神生態(tài)等。所以,生態(tài)殖民主義既是生態(tài)范疇,又是經(jīng)濟(jì)政治范疇。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實(shí)行的“新”的殖民形態(tài),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資本全球化布控下不平等經(jīng)濟(jì)政治之世界體系中,針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生態(tài)維度進(jìn)行的剝削性與剝奪性的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行為的總稱。作為客觀事實(shí),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資本全球化時(shí)期殖民主義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新自由主義肆虐全球幾十年后,地區(qū)性的生態(tài)破壞問(wèn)題已經(jīng)升級(jí)為全球性的生態(tài)危機(jī)問(wèn)題。自然資源問(wèn)題、生態(tài)環(huán)境問(wèn)題已成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存續(xù)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對(duì)此,貝米拉·福斯特看得十分清楚。他認(rèn)為,生態(tài)殖民主義并非什么陰謀詭計(jì),而是根源于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需要和帝國(guó)主義原動(dòng)力中的共識(shí);生態(tài)殖民主義更不是帝國(guó)主義的一項(xiàng)單純的政策行為,它的本質(zhì)是根植于資本主義本性中的有規(guī)則的現(xiàn)實(shí)。[2]
易言之,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殖民主義在生態(tài)維度的集中呈現(xiàn),始作于歐洲先進(jìn)資本主義國(guó)家15世紀(jì)左右開(kāi)啟的以殖民主義擴(kuò)張為政治方案的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進(jìn)程,這一進(jìn)程在20世紀(jì)70年代左右以加速度變化、系統(tǒng)性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到全人類眼前。20世紀(jì)70年代以前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直接伴以軍事占領(lǐng)、生命屠戮、經(jīng)濟(jì)掠奪、政治壓迫等方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guó)家成為先進(jìn)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原料能源供應(yīng)地、工業(yè)商品傾銷地。歐洲殖民者的入侵,通過(guò)生物侵占破壞了亞非拉原有的生態(tài)平衡,以建立適合歐洲殖民者生產(chǎn)、生活、生存所需的新型生態(tài)空間。[3]彼時(shí),先進(jìn)資本主義國(guó)家直接剝奪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對(duì)殖民地和半殖民國(guó)家來(lái)講就是純粹的“無(wú)”。20世紀(jì)70年代之后,發(fā)展為“新型”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則披上了“民主、自由、人權(quán)、發(fā)展”的外衣,把生態(tài)殖民主義赤裸裸的統(tǒng)治方式加以意識(shí)形態(tài)化和“文化與文明化”,以生態(tài)問(wèn)題為切口、以“援助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社會(huì)發(fā)展”“履行國(guó)際義務(wù)”為借口,故意給發(fā)展中國(guó)家制造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與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二元悖論”。“碳政治”②正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之雙重剝奪的真實(shí)寫(xiě)照。由此可見(jiàn),無(wú)論發(fā)達(dá)國(guó)家殖民主義的具體形式怎樣,生態(tài)殖民主義始終是其伴生產(chǎn)物。
(二)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表征
第一,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殖民化擴(kuò)張。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殖民化擴(kuò)張是指,發(fā)達(dá)國(guó)家憑靠科學(xué)技術(shù)、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武力之優(yōu)勢(shì),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原生態(tài)系統(tǒng)進(jìn)行強(qiáng)制入侵和系統(tǒng)改造。在殖民主義早期,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殖民化擴(kuò)張主要通過(guò)屠戮原住居民、遷移外生動(dòng)植物、帶入新的病菌細(xì)菌等方式,對(duì)亞非拉地區(qū)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進(jìn)行“生物換血”。這是一種明火執(zhí)仗的、“外科手術(shù)式”的強(qiáng)制入侵。而今天,發(fā)達(dá)國(guó)家假以“自由貿(mào)易”的面紗、通過(guò)高端前沿的生物技術(shù),在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重塑當(dāng)?shù)氐纳鷳B(tài)系統(tǒng),進(jìn)而將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生態(tài)循環(huán)永久性地、系統(tǒng)性地、結(jié)構(gòu)性地殖民化。例如,美國(guó)轉(zhuǎn)基因物種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大規(guī)模種植,已經(jīng)不可逆轉(zhuǎn)地改變了當(dāng)?shù)氐纳锒鄻有院屯寥罈l件,打破了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當(dāng)?shù)卦猩锓N群之間的生態(tài)平衡關(guān)系,破壞了當(dāng)?shù)卦械淖匀簧鷳B(tài)環(huán)境。另外,目前對(duì)人類食用轉(zhuǎn)基因食物可能出現(xiàn)的危害也存有爭(zhēng)論[4]。
第二,對(duì)生態(tài)資源的系統(tǒng)化掠奪。掠奪生態(tài)資源是生態(tài)殖民主義游走于國(guó)際間的重要目的。先進(jìn)資本主義國(guó)家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變?yōu)樵瞎┙o地和商品傾銷地的做法,本就是一種公開(kāi)掠奪后發(fā)展國(guó)家豐富而廉價(jià)的資源材料的令人發(fā)指的手段。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以美國(guó)為首的發(fā)達(dá)國(guó)家利用國(guó)際壟斷資本的優(yōu)勢(shì),通過(guò)所謂的國(guó)際自由貿(mào)易不斷從發(fā)展中國(guó)家“吸血”。例如,從1980年至1995年間,拉丁美洲對(duì)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出口量增長(zhǎng)了245%。發(fā)達(dá)國(guó)家一邊保護(hù)自己的森林植被,一邊去發(fā)展中國(guó)家亂砍濫伐,美國(guó)去南美、歐洲去非洲、日本去東南亞。當(dāng)日本把東南亞熱帶雨林幾乎砍盡后,又去拉丁美洲砍伐了。中國(guó)稀土儲(chǔ)量占世界總量的30%,卻承擔(dān)著世界稀土消費(fèi)90%的供應(yīng)量,供給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要占60%;美國(guó)稀土儲(chǔ)量世界第二,卻幾乎不開(kāi)采。2010年,中國(guó)開(kāi)始限制稀土開(kāi)采量,立即遭到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指責(zé)報(bào)復(fù)。海外和中東國(guó)家遭受的“石油詛咒”也鐵板釘釘般地控訴著發(fā)達(dá)國(guó)家實(shí)施的對(duì)生態(tài)資源的系統(tǒng)性掠奪。
第三,生態(tài)污染的結(jié)構(gòu)化轉(zhuǎn)移。如果說(shuō),對(duì)生態(tài)資源的系統(tǒng)性掠奪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向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生態(tài)索取,那么,生態(tài)污染的結(jié)構(gòu)化轉(zhuǎn)移就是一種負(fù)面的、隱晦的“生態(tài)貢獻(xiàn)”。有人十分向往歐美日國(guó)家優(yōu)質(zhì)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但卻無(wú)視這種優(yōu)質(zhì)環(huán)境是以污染發(fā)展中國(guó)家為條件和代價(jià)的。一方面,發(fā)達(dá)國(guó)家嚴(yán)格禁止其國(guó)內(nèi)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另一方面,發(fā)展中國(guó)家因其處于世界經(jīng)濟(jì)政治體系的中低端,經(jīng)濟(jì)技術(shù)落后但急于引進(jìn)外資,法律嚴(yán)重缺失而又無(wú)法監(jiān)管外資。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污染出口”和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外資引入似乎“一拍即合”。因此看到,美國(guó)把二分之一污染嚴(yán)重、消耗嚴(yán)重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到發(fā)展中國(guó)家,日本將2/3到3/4的高污染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地區(qū)。而將危險(xiǎn)有害垃圾傾倒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又一項(xiàng)“偉大發(fā)明”。正如世界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雜志《經(jīng)濟(jì)學(xué)人》曾載的一篇題為《讓他們吃下污染》的文章所窺測(cè)到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約有7億處于極端饑餓狀態(tài)的窮人,為了得到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不得不從發(fā)達(dá)國(guó)家“進(jìn)口”數(shù)百萬(wàn)噸的有毒垃圾并以此為生!王久良在阿姆斯特丹電影節(jié)獲獎(jiǎng)的《塑料王國(guó)》血淚般地痛斥了歐美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中國(guó)的“光輝杰作”!2010年之前,中國(guó)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最大垃圾處理場(chǎng)”!中國(guó)環(huán)保部2013年首度承認(rèn)的中國(guó)存在的“癌癥村”,正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中國(guó)人民做出的“巨大貢獻(xiàn)”!
第四,生態(tài)壁壘的制度化設(shè)計(jì)。生態(tài)壁壘的制度化設(shè)計(jì)最能集中體現(xiàn)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能最好地詮釋生態(tài)殖民主義威脅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之實(shí)質(zhì)——發(fā)達(dá)國(guó)家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應(yīng)享有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的雙重剝奪。發(fā)達(dá)國(guó)家憑借和依靠其自身的科學(xué)技術(shù)優(yōu)勢(shì)、經(jīng)濟(jì)體系優(yōu)勢(shì)、政治秩序優(yōu)勢(shì),以保護(hù)人類生態(tài)環(huán)境、實(shí)現(xiàn)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構(gòu)建發(fā)達(dá)國(guó)家宰制下的“生態(tài)正義”為旗號(hào),設(shè)置各種非關(guān)稅的制度化壁壘,以犧牲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為代價(jià)、以保護(hù)發(fā)達(dá)國(guó)家享受全球生態(tài)資源為目的,通過(guò)輸出“生態(tài)赤字”和輸入“生態(tài)紅利”的方式,在全球范圍內(nèi)實(shí)現(xiàn)有利于發(fā)達(dá)國(guó)家自己的生態(tài)壁壘的制度設(shè)計(jì)。發(fā)達(dá)國(guó)家設(shè)計(jì)的“生態(tài)正義”方案看似公平,實(shí)則不然。它們要求發(fā)展中國(guó)家遵照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環(huán)保標(biāo)準(zhǔn)。這其實(shí)是雙重標(biāo)準(zhǔn),即要求后進(jìn)發(fā)展中國(guó)家也承擔(dān)由先進(jìn)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歷史上欠下的很大一部分的“生態(tài)債務(wù)”,逼迫發(fā)展中國(guó)家承擔(dān)超過(guò)其承受能力的生態(tài)保護(hù)的義務(wù);并通過(guò)技術(shù)優(yōu)勢(shì)鉗制發(fā)展中國(guó)家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不可避免的生態(tài)結(jié)果,進(jìn)而徹底限制發(fā)展中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社會(huì)的發(fā)展空間。貝米拉·福斯特以《京都協(xié)議》的失敗為典型案例,來(lái)揭露發(fā)達(dá)國(guó)家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真實(shí)面目。
二、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的邏輯體系
生態(tài)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存有內(nèi)在耦合性。雖然,“生態(tài)殖民主義(包括廣義的生態(tài)危機(jī))是生態(tài)資本化的產(chǎn)物”的觀點(diǎn)為學(xué)界多數(shù)同仁所贊同,該觀點(diǎn)也極具學(xué)理價(jià)值和實(shí)踐意蘊(yùn),但筆者認(rèn)為,既然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實(shí)行的“新”的殖民形態(tài),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資本全球化布控下不平等經(jīng)濟(jì)政治之世界體系中,針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生態(tài)維度進(jìn)行的剝削性與剝奪性的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等行為的總稱,那么生態(tài)殖民主義并非單純的“生態(tài)資本化”的產(chǎn)物,作為歷史呈現(xiàn)出的現(xiàn)實(shí),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整體性結(jié)構(gòu)的復(fù)雜化的產(chǎn)物,即“生態(tài)資本主義化”的產(chǎn)物。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中國(guó)國(guó)有資本的存在,雄辯地證明了,資本和資本主義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但彼此又有實(shí)質(zhì)性區(qū)別的兩個(gè)概念。如果生態(tài)殖民主義僅僅是“生態(tài)資本化”的產(chǎn)物,那么在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建設(shè)生態(tài)文明的邏輯就不成立。通過(guò)論述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生成邏輯,一方面能夠有效和有力地證明筆者的觀點(diǎn),另一方面也能夠更加深刻地回溯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本質(zhì)和表征。
(一)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邏輯的思想根源:歐洲中心主義
生態(tài)殖民主義有著深厚的思想根源即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為不少人所接受的思想偏見(jiàn),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為自己主宰世界、制造歷史合法性的說(shuō)教。“人的發(fā)現(xiàn)”和“世界的發(fā)現(xiàn)”產(chǎn)生于歐洲,近現(xiàn)代的科技革命、工業(yè)革命、政治革命也出現(xiàn)在歐洲,這就重新安排了歐洲的經(jīng)濟(jì)政治結(jié)構(gòu)、科學(xué)文化結(jié)構(gòu)、社會(huì)階級(jí)結(jié)構(gòu)、生態(tài)循環(huán)結(jié)構(gòu),使歐洲走在了整個(gè)人類社會(huì)近現(xiàn)代發(fā)展的最前列,并為歐洲資本主義的遠(yuǎn)洋殖民提供了科學(xué)動(dòng)力和歷史合法性。從那以后,整個(gè)世界就被分成中心地區(qū)和邊緣地區(qū)(包括半邊緣地區(qū),下同)兩個(gè)部分。中心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物質(zhì)文明越來(lái)越對(duì)邊緣地區(qū)呈現(xiàn)出發(fā)展的巨大優(yōu)越性,并由此陷入無(wú)限向下的死循環(huán):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先發(fā)優(yōu)越性是通過(guò)無(wú)情剝削邊緣地區(qū)的剩余價(jià)值、生態(tài)資源和轉(zhuǎn)移生態(tài)危機(jī)到邊緣地區(qū)等方式維持的;這種優(yōu)越性反過(guò)來(lái)又被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傳教士”對(duì)邊緣地區(qū)人民反復(fù)傳頌,告訴這些地區(qū)的人民“如果想要過(guò)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生活,就走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道路”。
歐洲中心主義有兩個(gè)重要的理論支撐,一是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二是人類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并非一個(gè)嚴(yán)格而狹隘的地域范疇,而是泛指以盎克魯-撒克遜為核心的白人至上主義觀念。白人至上主義觀念的哲學(xué)根源是,以白人為唯一目的的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率先從中世紀(jì)走出來(lái)的歐洲人把自己打扮成文明、進(jìn)步的化身,把落后的亞非拉地區(qū)的國(guó)家的人民視作野蠻、愚昧、無(wú)知的下等生物。因此,歐洲人一方面把自己等同于人類本身,另一方面,在落后的亞非拉地區(qū)的國(guó)家和人民面前,又把自己打扮成“上帝”。同時(shí),開(kāi)啟了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歐洲人還把自己裝扮成科學(xué)、真理、理性的化身,高舉人類中心主義的大旗,宣揚(yáng)“人為自然立法”,把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解釋為主奴關(guān)系。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就強(qiáng)調(diào)了科學(xué)技術(shù)和理性知識(shí)在殖民開(kāi)拓過(guò)程中的重要作用,進(jìn)而“形塑了一個(gè)新的倫理,支持對(duì)自然的剝削”[5]。由此可見(jiàn),以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為根源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蘊(yùn)含著自然控制和種族控制的法西斯傾向的意識(shí)形態(tài)。所以,世界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雜志《經(jīng)濟(jì)學(xué)人》在2019年9月26日發(fā)送這樣一條推文,我們就不應(yīng)對(duì)此感到奇怪:“More poor people are eating meat around the world. That means they will live longer, healthier lives, but it is bad news for the environment.”③
(二)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邏輯的物質(zhì)基礎(chǔ):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
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邏輯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自身具有的擴(kuò)張功能。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的擴(kuò)張事實(shí)往往被研究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學(xué)者所忽略。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內(nèi)含了生態(tài)學(xué)內(nèi)容的經(jīng)濟(jì)政治范疇,反過(guò)來(lái)看,即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以生態(tài)學(xué)內(nèi)容為物質(zhì)基礎(chǔ)的經(jīng)濟(jì)政治范疇。生態(tài)殖民主義得以落地生根,并不只取決于殖民者是如何假定或怎樣假設(sh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因?yàn)椋趁裾叩纳鷳B(tài)殖民行為是建立在羅伊·拉波特所說(shuō)的“生物生存能力”[6]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擴(kuò)張的物質(zhì)基礎(chǔ)之上的。一旦殖民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開(kāi)啟了生物物種變更的“大門”,就會(huì)打破當(dāng)?shù)卦械摹⒎€(wěn)定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新生物群落在新物種聯(lián)合體的基礎(chǔ)上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從而新的物質(zhì)、能量、信息交換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便會(huì)啟動(dòng)。此時(shí),被選中的物種群就會(huì)出現(xiàn)生物學(xué)性質(zhì)的爆發(fā)性的增加。當(dāng)然,當(dāng)?shù)卦械囊恍┪锓N群落如果能夠“從由殖民遭遇過(guò)程本身提供的外在物質(zhì)或能量的融合中發(fā)現(xiàn)新的活力”[7]277,也可能異常茂盛。假以時(shí)日,作為先前入侵的物種群落已經(jīng)內(nèi)生化為新的穩(wěn)定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在殖民者的強(qiáng)力開(kāi)創(chuàng)下,這樣的體系通過(guò)生物學(xué)內(nèi)容自身的生態(tài)邏輯(這是內(nèi)因)生長(zhǎng)出來(lái),因而永久地改變了原生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進(jìn)而不可逆轉(zhuǎn)地適應(yīng)了殖民者帶來(lái)的新的殖民體系。這樣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體系具有容含的共生性質(zhì):“創(chuàng)造共生群落相互作用的穩(wěn)定模式,這種創(chuàng)造是通過(guò)回溯人口振蕩,以及在本土物質(zhì)循環(huán)和能量脈沖的參量?jī)?nèi)進(jìn)行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他人需要的方式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趨向于創(chuàng)造一些群落,這些群落能夠
防止物質(zhì)能量流入或流出某種局部性可持續(xù)的物質(zhì)循環(huán)體系,該體系
建立在太陽(yáng)能持續(xù)流動(dòng)的基礎(chǔ)上。”[7]278
(三)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邏輯的邏輯主線:生態(tài)的資本化
生態(tài)的資本化是指把生態(tài)的相關(guān)構(gòu)素簡(jiǎn)化成可以實(shí)現(xiàn)市場(chǎng)利潤(rùn)最大化的商品庫(kù),這樣做“是為了掩蓋現(xiàn)實(shí)商品交換而對(duì)自然極盡掠奪的現(xiàn)實(shí)”[8]。資本積累邏輯勢(shì)必把包括生態(tài)資源在內(nèi)的一切生產(chǎn)和生活要素統(tǒng)統(tǒng)商品化。毫無(wú)疑問(wèn),生態(tài)資源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物質(zhì)基礎(chǔ),因而具有各種形式的使用價(jià)值。這意味著,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也包括競(jìng)爭(zhēng)型壟斷機(jī)制,下同)中,生態(tài)資源的背后隱匿著不同資本對(duì)它的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的爭(zhēng)奪。生態(tài)資源的使用價(jià)值要在人的生產(chǎn)生活中才能被消費(fèi),而分配本屬于公共和共享性質(zhì)的生態(tài)資源的方式是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從而生態(tài)資源的質(zhì)量、數(shù)量、種類、性質(zhì)會(huì)直接影響到企業(yè)生產(chǎn)的規(guī)模、商品生產(chǎn)的質(zhì)量、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的能力等。如此,在資本主導(dǎo)的市場(chǎng)體系當(dāng)中,沒(méi)有價(jià)值和交換價(jià)值的生態(tài)資源獲得了被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規(guī)定的價(jià)格。正如馬克思所言,良心、名譽(yù)等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出賣換取金錢,并通過(guò)價(jià)格獲得商品的形式。[9]所以,把龐大的生態(tài)資源視為巨大的商品庫(kù)即生態(tài)的商品化是生態(tài)資本化的第一步。因?yàn)檫@時(shí),作為商品性質(zhì)存在的生態(tài)資源是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的邏輯預(yù)設(shè)和前提規(guī)定。可是,一旦生態(tài)資源進(jìn)入到現(xiàn)實(shí)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過(guò)程中,生態(tài)資源就會(huì)取得相應(yīng)的價(jià)格,而獲得了價(jià)格的生態(tài)資源就真正地實(shí)現(xiàn)了自己作為商品的屬性。與此同時(shí),這樣的生態(tài)資源也就從商品化階段進(jìn)入到貨幣化階段,即生態(tài)的貨幣化。
但是,生態(tài)的貨幣化只是個(gè)短暫的中間形式。參與到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的生態(tài)資源是為資本積累服務(wù)的,即生態(tài)資源本身要成為某種具體的資本形式即生態(tài)資本。作為資本存在的生態(tài)資源服從的唯一規(guī)律就是增殖。事實(shí)上,如果生態(tài)資源沒(méi)有作為資本形態(tài)的可能,生態(tài)資源是不可能取得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的;如果生態(tài)資源不能在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中帶來(lái)剩余利潤(rùn),生態(tài)資源就不可能作為資本而存在。由此,在資本積累邏輯中,生態(tài)資源是一個(gè)取之不盡的寶庫(kù),這是“上帝”免費(fèi)饋贈(zèng)的,沒(méi)有成本、沒(méi)有抱怨、沒(méi)有抗拒、沒(méi)有索取,如何最大限度地開(kāi)發(fā)利用生態(tài)資源以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的最大化,才是資本家醉心的事業(yè)。畢竟,在資本家眼里,“保護(hù)自然”也只是一門盈利的“生意”,而非惠及大眾的“主義”。至于拯救自然災(zāi)難、解決生態(tài)危機(jī)其實(shí)壓根兒不在資本家關(guān)心的視域里。因?yàn)椋谒麄兛磥?lái),自己有足夠的財(cái)力和物力來(lái)營(yíng)建自己私有的、優(yōu)質(zhì)的生態(tài)空間。
不管早期抑或當(dāng)下,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生成與擴(kuò)張,始終是在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下以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為中介發(fā)生作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是以資本積累邏輯為驅(qū)動(dòng)力。所以,生態(tài)資本化是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邏輯主線。
(四)生態(tài)殖民主義生成邏輯的前提條件:生態(tài)的政治化
在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國(guó)際政治秩序中,生態(tài)殖民主義內(nèi)在地要求生態(tài)政治化,生態(tài)政治化是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前提條件。2017年6月5日,美國(guó)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宣布美國(guó)退出《巴黎協(xié)定》。這再次表現(xiàn)了發(fā)達(dá)國(guó)家一貫以來(lái)的公然挑釁國(guó)際正義原則的政治傲慢,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其國(guó)內(nèi)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政治基礎(chǔ)上,延續(xù)與拓展歷史形成的國(guó)際等級(jí)化優(yōu)勢(shì)或排斥性霸權(quán)的表現(xiàn),也是創(chuàng)建更加公平、民主與有效的全球氣候或環(huán)境治理體制的內(nèi)在性障礙”[10]。在今天的全球?qū)用妫嘘P(guān)生態(tài)問(wèn)題的國(guó)際商討都是在由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不平等的國(guó)際政治秩序架構(gòu)中展開(kāi)的,總體形勢(shì)自然對(duì)發(fā)達(dá)國(guó)家更加有利。對(duì)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而言,關(guān)乎生死存亡的生態(tài)問(wèn)題不過(guò)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圓桌上的政治籌碼而已。這一籌碼歸根到底只服從于資本積累的需要和無(wú)限盈利的目的。“資本控制者所追求的利潤(rùn)、私人財(cái)產(chǎn)保障、低風(fēng)險(xiǎn)等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通常與經(jīng)濟(jì)相對(duì)平等和安全、環(huán)境安全、平等獲得食物等社會(huì)目標(biāo)相沖突”。[11]就此而言,生態(tài)殖民主義就是殖民主義。因?yàn)椋瑢?duì)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來(lái)講,游戲規(guī)則本身比游戲具體內(nèi)容要核心和關(guān)鍵得多。畢竟,在游戲者和游戲規(guī)則之間的關(guān)系中,游戲規(guī)則才是真正的主體。[12]
目前,生態(tài)殖民主義政治化操作生態(tài)問(wèn)題的主要方式如下:(1)發(fā)達(dá)國(guó)家將自己制定國(guó)際政治秩序的政治話語(yǔ)主導(dǎo)權(quán)具體化為國(guó)際交往規(guī)則中對(duì)生態(tài)資源的定價(jià)權(quán),即通過(guò)操縱價(jià)格提高自己的工業(yè)商品價(jià)格、降低生態(tài)資源和初級(jí)產(chǎn)品的價(jià)格,攫取巨大的“價(jià)值剪刀差”;(2)通過(guò)政治脅迫(必要時(shí)還加上軍事打壓)擾亂正常的國(guó)際政治經(jīng)濟(jì)秩序以及與落后的目標(biāo)國(guó)簽訂不平等政治條款,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其生態(tài)剝削目的;(3)構(gòu)建只有發(fā)達(dá)國(guó)家等少數(shù)個(gè)體才能擁有的霸權(quán)政治結(jié)構(gòu),例如,IMF重大議題都需要85%的通過(guò)率,而美國(guó)近年來(lái)投票權(quán)基本在17%左右,因此美國(guó)事實(shí)上享有一票否決的權(quán)力。可見(jiàn),生態(tài)政治化包含了國(guó)際性政策議題的設(shè)定、理論話語(yǔ)的闡釋、發(fā)展路徑的供給等層面的生態(tài)霸權(quán)性的和排斥性的話語(yǔ)、制度、力量,是一種剛性而尖銳的柔性政治,是一種實(shí)體化的制度構(gòu)架。這一點(diǎn),當(dāng)然不同于早期殖民主義簡(jiǎn)單粗暴的“肆意妄為”。
三、超越生態(tài)殖民主義邏輯,構(gòu)筑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屏障
生態(tài)殖民主義給民族國(guó)家的生態(tài)安全造成了嚴(yán)重威脅,尤其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布控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雙重地剝奪了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這個(gè)“緊箍咒”不破除,發(fā)展中國(guó)家就沒(méi)有未來(lái)和希望。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作為正在走進(jìn)世界中央并努力搭建真正公平正義國(guó)際新秩序的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作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理念的倡議者和實(shí)踐者,中國(guó)應(yīng)該且必須為自己、為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為人類探索一條超越生態(tài)殖民主義邏輯的現(xiàn)實(shí)可行的道路,構(gòu)筑自己的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屏障,并為其他發(fā)展中國(guó)家提供有益的和有效的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
(一)規(guī)范生態(tài)資本化,杜絕生態(tài)資本主義化
生態(tài)殖民主義是包含了“生態(tài)資本化”的“生態(tài)資本主義化”,但是“生態(tài)資本化”不等于“生態(tài)資本主義化”。馬克思有“利用發(fā)展資本來(lái)限制超越資本”的思想,鄧小平有“資本手段論”的觀點(diǎn)。而在“資本的歷史優(yōu)勢(shì)”[13]已完全確立的今天,“任何脫離資本談中國(guó)現(xiàn)代化,脫離資本邏輯談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都是不切實(shí)際的”[14]。資本主義不可能“變綠”,可是,資本在可控條件下是能夠?yàn)樯鷳B(tài)文明建設(shè)服務(wù)的。這已經(jīng)為中國(guó)的實(shí)踐所證明。資本積累邏輯的一般原則是增殖逐利,因此,通過(guò)有力、有效地引導(dǎo)資本投到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中,能夠充分使資本化的生態(tài)資源作為積極性質(zhì)的生產(chǎn)要素參與到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中。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行之有效的關(guān)鍵在于,社會(huì)主義的制度優(yōu)勢(shì)能夠駕馭和規(guī)范資本積累邏輯、能夠引導(dǎo)和形塑資本市場(chǎng)行為。中國(guó)的改革開(kāi)放正是在合理科學(xué)地處理了發(fā)展利用資本與限制超越資本之微妙的平衡關(guān)系后,克服了一個(gè)又一個(gè)的發(fā)展難題,從而取得今日之成就的。[15]
(二)夯實(shí)國(guó)有資本,管控境外投資
國(guó)有資本是保障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推動(dòng)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關(guān)鍵經(jīng)濟(jì)力量。國(guó)有企業(yè)是壯大國(guó)家綜合實(shí)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關(guān)系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關(guān)系民族國(guó)家的生存大計(jì),只有堅(jiān)強(qiáng)有力的國(guó)有資本才能提供堅(jiā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保障。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建設(shè)是一項(xiàng)公共化和社會(huì)化事業(yè),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石的社會(huì)主義制度才能真實(shí)地保證該事業(yè)的普遍性和普適性,而只有國(guó)有資本才能在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建設(shè)中“身先士卒”,發(fā)揮關(guān)鍵且主要的作用。的確,不管國(guó)有資本還是非國(guó)有資本,既然是資本就不可避免地遵循資本積累的一般邏輯——盈利。但二者的根本不同點(diǎn)是,非公性質(zhì)的資本以利潤(rùn)為最終且唯一之目的;國(guó)有資本的根本宗旨不是賺錢,賺錢只是服務(wù)人民群眾之根本利益這一宗旨的必要的手段。
境外投資是一把雙刃劍,其正面效應(yīng)和負(fù)面效應(yīng)究竟如何釋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態(tài)度和管理方式。中國(guó)外資主要來(lái)自歐、美、日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顯然,境外資本不是抱著做“生態(tài)慈善”的目的來(lái)到中國(guó)。所以,中國(guó)必須在引進(jìn)、利用外資的過(guò)程中保持足夠的警惕,防范其對(duì)中國(guó)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脅和損害。當(dāng)然,這需要中國(guó)完善各項(xiàng)機(jī)制體制和政策法規(guī),通過(guò)制度建設(shè)和制度引導(dǎo),鼓勵(lì)、利用、引導(dǎo)外資積極參與中國(guó)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事業(yè),化消極為積極、變被動(dòng)為主動(dòng)。
(三)加強(qiáng)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管理,提升國(guó)家生態(tài)現(xiàn)代化治理能力
完善與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有關(guān)的貿(mào)易和投資制度,不給生態(tài)殖民主義向中國(guó)延伸以漏洞可鉆。為此,應(yīng)該把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納入法治軌道,加快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重點(diǎn)領(lǐng)域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建立和健全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監(jiān)管體系、法律體系、應(yīng)急體系、預(yù)警體系、救援體系,完善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管理制度,著力提升國(guó)家生態(tài)現(xiàn)代化治理能力。增強(qiáng)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硬件設(shè)施”,提高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軟件韌性”。一方面,要運(yùn)用現(xiàn)代信息科學(xué)技術(shù)建構(gòu)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系統(tǒng),全面提增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知識(shí)化、信息化、智能化、可控化水平,加快建設(shè)環(huán)境污染源監(jiān)控管理信息系統(tǒng)、環(huán)境保護(hù)管理信息系統(tǒng)、環(huán)境質(zhì)量監(jiān)測(cè)管理信息系統(tǒng)、核安全與輻射管理信息系統(tǒng)、環(huán)境應(yīng)急管理信息系統(tǒng)等;另一方面,強(qiáng)化社會(huì)和公民維護(hù)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責(zé)任意識(shí),提升社會(huì)和公民履行維護(hù)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責(zé)任的能力,增強(qiáng)社會(huì)和公民在逆變環(huán)境中的反應(yīng)、承受、適應(yīng)和迅速恢復(fù)的能力,培育社會(huì)和公民在環(huán)境災(zāi)難和環(huán)境壓力面前具有堅(jiān)不可摧的韌性和彈性。
(四)警惕生態(tài)殖民主義“變種”,防止生態(tài)殖民主義“近親”
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變種”和“近親”是指,國(guó)家與國(guó)家之間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的邏輯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了國(guó)內(nèi)化的和國(guó)內(nèi)地區(qū)化的趨勢(shì)。[16]因?yàn)椋@種情況已經(jīng)在中國(guó)境內(nèi)有一些征兆了。所以,有學(xué)者十分擔(dān)憂地指出,生態(tài)殖民主義在中國(guó)的變相存在,例如把東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達(dá)地區(qū)的污染挪移到中西部等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欠發(fā)達(dá)地區(qū),使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落后省市成為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達(dá)省市的“污染避難所”。[17]國(guó)內(nèi)的這一情況與國(guó)際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具有結(jié)構(gòu)上的“家族相似性”。今天,中國(guó)正在進(jìn)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從重?cái)?shù)量規(guī)模的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模式升級(jí)為重質(zhì)量效益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方式,東部沿海地區(qū)開(kāi)始“騰籠換鳥(niǎo)”。在國(guó)家整體布局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戰(zhàn)略布局下,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是實(shí)現(xiàn)全社會(huì)共享發(fā)展成果、發(fā)揮經(jīng)濟(jì)生態(tài)資源比較優(yōu)勢(shì)的重要戰(zhàn)略舉措,是一項(xiàng)利國(guó)利民的國(guó)家大計(jì)。同時(shí),也的確存在把一些技術(shù)含量較弱、資源消耗較多、環(huán)保達(dá)標(biāo)較差、生產(chǎn)效益較低的產(chǎn)業(yè)梯度式地轉(zhuǎn)移到中西部地區(qū)的現(xiàn)象。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國(guó)內(nèi)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省際地區(qū)之間的公平正義,不能及時(shí)有效地實(shí)施綠色生產(chǎn)和進(jìn)行綠色監(jiān)管,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就會(huì)退化為污染轉(zhuǎn)移。因此,應(yīng)該充分保障國(guó)內(nèi)生態(tài)領(lǐng)域的省際地區(qū)公平正義,不能陷入“落后就要被污染的發(fā)展陷阱”[18]。
(五)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促成全球生態(tài)善治
促成全球生態(tài)善治、實(shí)現(xiàn)全球生態(tài)正義是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就實(shí)踐而言,超越生態(tài)殖民主義需要堅(jiān)持“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相統(tǒng)一、“全球生態(tài)權(quán)利和全球生態(tài)責(zé)任”相統(tǒng)一、“享受生態(tài)紅利和補(bǔ)貼生態(tài)赤字”相同一的原則。這些原則要求每一個(gè)國(guó)家都應(yīng)該根據(jù)自己享有的權(quán)利大小承擔(dān)對(duì)等的責(zé)任。各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所處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相應(yīng)的社會(huì)發(fā)展水平不同,因此獲得的權(quán)利和承擔(dān)的責(zé)任也應(yīng)有所差別。雖然直到今天,國(guó)際社會(huì)都沒(méi)有形成一個(gè)有效應(yīng)對(duì)全球生態(tài)問(wèn)題的治理體系,但是作為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和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社會(huì)主義的中國(guó)應(yīng)該同廣大發(fā)展中國(guó)家一起,在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促成全球生態(tài)善治的實(shí)踐中,為世界人民做出新貢獻(xiàn),以逐步破除由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不平等的國(guó)際經(jīng)濟(jì)政治生態(tài)的等級(jí)秩序。在積極參與包括生態(tài)在內(nèi)的全球治理的同時(shí),與不公正勢(shì)力進(jìn)行有利有力的堅(jiān)決斗爭(zhēng),推動(dòng)實(shí)現(xiàn)互惠共贏的國(guó)際機(jī)制,為攜手建構(gòu)合作共贏、 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態(tài)治理機(jī)制而努力。[19]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正是中國(guó)領(lǐng)航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促成全球生態(tài)善治的光輝實(shí)踐。和諧是中國(guó)政治和文化的核心追求,這意味著,中國(guó)的全球生態(tài)治理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主導(dǎo)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有本質(zhì)區(qū)別:中國(guó)明確反對(duì)國(guó)際生態(tài)殖民主義,堅(jiān)決反對(duì)任何國(guó)家對(duì)任何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權(quán)和生態(tài)安全權(quán)的剝奪,積極布局和踐行契合國(guó)際正義原則的生態(tài)外交策略,對(duì)生態(tài)殖民主義保持足夠警惕,全力推動(dòng)國(guó)際政治民主化建設(shè),努力打破發(fā)達(dá)國(guó)家布控的生態(tài)殖民主義話語(yǔ)霸權(quán),在競(jìng)爭(zhēng)與合作中增強(qiáng)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營(yíng)造國(guó)際生態(tài)優(yōu)質(zhì)環(huán)境。總之,中國(guó)要在錯(cuò)綜復(fù)雜的外交架構(gòu)中推進(jìn)生態(tài)外交戰(zhàn)略,增強(qiáng)生態(tài)文明話語(yǔ)權(quán),提升國(guó)際影響力,在維護(hù)全球生態(tài)正義的同時(shí),擔(dān)負(fù)起保障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促進(jìn)社會(huì)健康發(fā)展的民族重任。
注釋:
① 阿爾弗雷德·克勞士比認(rèn)為,歐洲的殖民者對(duì)新大陸(美洲、澳洲、非洲等地)的成功殖民,得益于他們偶然或者蓄意將舊大陸的動(dòng)植物、病菌等帶到了新大陸,使得新大陸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口發(fā)生了重要轉(zhuǎn)換。歐洲殖民者帶去的很多病原體感染了當(dāng)?shù)厝丝冢斐闪舜罅康娜丝谒劳觯@種人口毀滅更甚于武器。所以,阿爾弗雷德·克勞士比便用“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概念描述這一事實(shí)。由此可見(jiàn),阿爾弗雷德·克勞士比的“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概念是基于純粹生態(tài)學(xué)角度的。
② 詳見(jiàn)郇慶治《“碳政治”的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邏輯批判及其超越》(載于《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6年第3期)。
③ 譯文:“世界上越來(lái)越多的窮人吃肉。這意味著他們會(huì)活得更長(zhǎng)、更健康,但這對(duì)環(huán)境來(lái)說(shuō)是個(gè)壞消息。”
參考文獻(xiàn):
[1] 洪大用.環(huán)境公平:環(huán)境問(wèn)題的社會(huì)學(xué)視點(diǎn)[J]. 浙江學(xué)刊,2004(4):67-73.
[2] J B Foster. The New Age of Imperialism[J]. Monthly Review,2003(3):55.
[3] 董慧.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一個(gè)初步考察[J].江海學(xué)刊,2014(4):60.
[4] 歐庭高,王也.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技術(shù)安全爭(zhēng)論的深層思考:兼論現(xiàn)代技術(shù)的不確定性與風(fēng)險(xiǎn)[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1):49-53.
[5] Merchant C. The Death of Nature: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164.
[6] Roy Rappaort. The Flow of Energy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J]. 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71(225):122.
[7] Weiskel T. Agents of Empire: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mperialism[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Winter 1987,11(4).
[8]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tài)危機(jī)與資本主義[M].耿建新,宋興無(wú),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8.
[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3.
[10] 郇慶治.“碳政治”的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邏輯批判及其超越[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6(3):24-41.
[11] 理查德·羅賓斯.資本主義文化與全球問(wèn)題[M].姚偉,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148.
[12] 伽達(dá)默爾.哲學(xué)解釋學(xué)[M].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14.
[13] I·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guān)于一種過(guò)渡理論[M].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1.
[14] 田輝玉,張三元.資本邏輯視域下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J].現(xiàn)代哲學(xué),2016(2):32.
[15] 葉險(xiǎn)明.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初論[J].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2014(3):19-26.
[16] 劉順.資本邏輯與生態(tài)正義——對(duì)生態(tài)帝國(guó)主義的批判與超越[J].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1):16.
[17] 解保,李哲.馬克思對(duì)資本主義工業(yè)的生態(tài)批判[J].鄱陽(yáng)湖學(xué)刊,2011(1):63.
[18] 俞可平.生態(tài)治理現(xiàn)代化越顯重要和緊迫[N].北京日?qǐng)?bào),2015-11-02(17).
[19] 趙艷.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多維共識(shí)[J].中國(guó)石油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36(2):52-56.
責(zé)任編輯:陳可闊
Ecologic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XIONG Xiaoguo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Abstract: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Ecological colonialism is both an ecological category and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ategory. Its essence is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depr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 righ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which is a "new" colonial form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on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ecosystem, systematic plunder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sign of ecological barriers. The generated logical system is that eurocentrism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ecological circulation system is the material basis,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is the logical main line, and ecological politiciz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Ecological colonialism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e must surpass ecological colonialism and build a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o promot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ecological colonialism;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capital logic; ecological justice
收稿日期: 2020-10-04
基金項(xiàng)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項(xiàng)目(20XJC710010);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專項(xiàng)項(xiàng)目(2019PTYB01)
作者簡(jiǎn)介: 熊小果(1986—),男,重慶巴南人,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yàn)轳R克思主義、生態(tài)哲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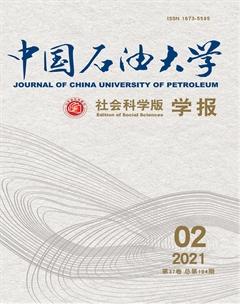 中國(guó)石油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2期
中國(guó)石油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年2期
- 中國(guó)石油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馬克思人與自然關(guān)系思想及其對(duì)當(dāng)代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啟示
- 基于企業(yè)家學(xué)習(xí)的國(guó)際機(jī)會(huì)識(shí)別研究
- 稅收競(jìng)爭(zhē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
- 論我國(guó)城鎮(zhèn)管道燃?xì)馓卦S經(jīng)營(yíng)模式轉(zhuǎn)型
- 我國(guó)城鎮(zhèn)燃?xì)馓卦S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糾紛表現(xiàn)及解決機(jī)制研究
- 20世紀(jì)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慶油田開(kāi)發(fā)建設(shè)的決策與準(zhǔn)備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