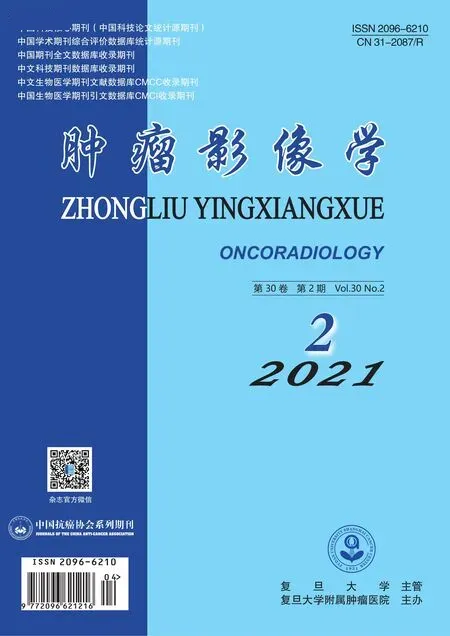腹膜后妊娠超聲誤診1例
陶久志,周毓青,龔菁菁,孫 琦,王 博
上海市長寧區婦幼保健院超聲醫學科,上海 200051
1 資 料
患者,女性,39歲,已婚。2019年11月27日,因停經47 d,不規則陰道出血26 d,下腹隱痛2 h于上海市長寧區婦幼保健院就診,查尿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陽性,血β-HCG為10 908.9 mIU/mL,經陰道彩色多普勒超聲于宮內宮外檢查未見妊娠證據。2019年11月29日免疫檢驗報告顯示血β-HCG為1 0877.80 mIU/mL。當日行經陰道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宮內未見孕囊,子宮內膜雙層厚度6.4 mm,雙卵巢未見明顯異常,附件區未見明顯的異常腫塊,主診醫師結合病史高度懷疑異位妊娠,于是請另一醫師協助檢查,亦未探及宮內宮外妊娠征象;再次請上級醫師檢查,于子宮后陷凹極偏左部位見一混合性回聲,大小為21 mm×18 mm×18 mm,邊界尚清,其內見一無回聲,大小為18 mm×15 mm×13 mm,伴表面及內部星點狀彩色血流(圖1);盆腔內未見明顯積液。臨床以“異位妊娠可能”急診收住入院。入院后經緊急術前準備行腹腔鏡下探查術及經陰道診刮取環術。經陰道診刮取環術中探得子宮前位,取出γ形環1枚;刮出少量組織物,肉眼未見絨毛。腹腔鏡術中見子宮正常大小,表面完整,活動可;雙側輸卵管、卵巢未見異常增大,未見活動性出血及破口;左側骶韌帶下方見一3 cm×3 cm×2 cm囊性增大突起,其表面略凹陷、中央見一0.5 cm破口,破口處見少許鮮紅色血跡,未見活動性出血(圖2),切開后肉眼可見絨毛組織;盆腔內另見棕色稀薄液體5 mL。術中診斷為異位妊娠(腹膜后妊娠),并予病灶切除,手術順利。術后3 d血β-HCG下降至1 345.60 mIU/mL,病情平穩后予以出院。術后5 d病理學檢查報告示宮腔少許破碎子宮內膜呈增生反應及鱗狀上皮;腹膜后病灶組織內見少量幼稚的絨毛組織伴退變(圖3)。術后10 d復查血β-HCG為60.90 mIU/mL,術后17 d復查血β-HCG正常。

圖1 腹膜后妊娠經陰道超聲檢查圖

圖2 腹膜后妊娠腹腔鏡下所見病灶

圖3 腹膜后妊娠病灶的病理鏡檢圖
2 討 論
腹膜后妊娠是指胚胎或胎兒位于腹膜腔以外的部位,是極罕見的特殊類型異位妊娠,母體病死率高[1];一般胚胎或胎兒不能存活,但國外有研究[2]報道1例腹膜后足月妊娠,最終經剖宮產分娩1名健康男嬰。另國外研究[3]報道了1例孕23周因無腦兒畸形引產失敗后剖腹手術證實為腹膜后妊娠。
腹膜后妊娠的受精卵可種植于后腹膜、閉孔窩、下腔靜脈與主動脈間、腹主動脈與左腎動脈交界處、髂總動脈分叉處等腹膜外部位[4-5]。常規的婦科超聲很難探查到這些部位,加之腹膜后妊娠患者的臨床表現與一般部位的異位妊娠無明顯特征性差異,故術前的定位鑒別診斷較困難。綜合分析文獻報道的腹膜后妊娠確診病例,均為對臨床可疑異位妊娠的病例擴大超聲掃查范圍后發現,其中部分病例(3例)可在胰腺后下方、腎下極、腹主動脈旁(相當于髂血管分叉處)等處發現較典型的胚囊(內見胎芽及卵黃囊),但術前均提示為腹腔妊娠,而未考慮腹膜后來源[6-8];部分病例(3例)經陰道超聲發現較低位置的腫塊,術前均診斷為一般異位妊娠[5,9-10];計算機體層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能定位腫塊位于腹膜后,結合病史能提示腹膜后妊娠,但有可能將停經史不明確或影像學表現不典型的病例誤診為腹膜后腫瘤或胰頭假性囊腫[11-15];1例腹膜后妊娠因HCG持續性增高術前被誤診為絨毛膜癌[16]。
腹膜后妊娠的具體病因尚不明確,高危因素主要包括輸卵管切除術后、既往子宮穿孔史、多次異位妊娠史、多次人工流產史、輸卵管炎及機械性損傷、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4,13]。其發病機制可能為以下幾種:① 輸卵管妊娠破裂或流產后仍然具有活性的滋養細胞脫落到腹腔,并向腹膜后種植生長;② 輸卵管切除術后如果輸卵管末端與腹膜后間隙形成瘺管,則宮腔與腹膜后直接相通,胚胎有可能由宮腔自發轉移至腹膜后而發展成為腹膜后異位妊娠;③ 腹膜缺損,因先天缺損或因腹膜慢性炎癥、子宮內膜異位灶等形成缺損,可能導致受精卵轉移至腹膜后生長。也有作者認為,受精卵或其脫落細胞可能經血管淋巴管轉移至腹膜后,然后種植生長,與婦科惡性腫瘤、滋養細胞腫瘤的血行轉移及宮頸癌、子宮內膜癌等的淋巴轉移類似;或受精卵游走于腹腔時受腸管的壓迫及蠕動等影響,種植并生長于腹膜后[4-5,9]。本研究患者無不良孕產史及手術史,發病機制更傾向于①或③。
本研究超聲聲像圖沒有特異性表現,腫塊位置偏而深,且腫塊不大,經陰道及經腹部超聲檢查均極易漏診。對患者先后檢查的3名超聲科醫師結合病史未輕易放棄對病灶的尋找,最終由上級醫師在擴大掃查范圍的情況下發現了異常腫塊,但僅提示了異位妊娠可能,未能提示腹膜后妊娠。對位置較高或偏一側的腫塊,經陰道超聲受掃查范圍及角度的影響常常無法探及,掃查范圍無法做到無限制的擴大,腹部超聲檢查也很難發現病灶,給診斷帶來困難。腹腔鏡術中反復探查大網膜、腸管及腸系膜表面均未能發現異常,術中再次通過經陰道超聲定位腫塊其聲像圖及部位同術前無明顯變化,根據超聲定位的方向,婦科醫師并沒能立即找到病灶,最后由婦科上級醫師探查發現左側盆壁骶韌帶下方腹膜突起,戳動突起部位,超聲定位聲像圖隨之而動,因此確定病灶并成功切除;如病灶部位的后腹膜光滑完整,手術探查相對不易發現病灶,手術難度也會增加;如病灶鄰近大血管或重要器官,手術風險較高;因此術前準確定位尤為重要,需警惕意外損傷,必要時行多學科協作手術[5,7-8]。國內研究[13]報道1例血β-hCG>9 000 U/L、孕囊大小約4 cm、孕囊位置與腹主動脈關系密切的腹膜后妊娠患者于CT引導下行穿刺注射甲氨蝶呤(MTX)治療成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手術風險[13];國外也有研究[17]報道MTX治療腹膜后妊娠失敗,最終接受手術治療[17]。因此根據個體情況不同,對腹膜后妊娠可考慮行MTX治療后再行腹腔鏡下病灶清除術,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手術風險的發生[5]。
本研究超聲診斷過程提示,超聲檢查必須緊密結合臨床病史,對于病史提示妊娠而超聲檢查不能找到宮內、宮外妊娠證據者,需警惕特殊或罕見部位的異位妊娠,應擴大掃查范圍。對于超聲檢查不能發現明確病灶的患者,應建議其行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重點觀察腹腔其它部位及腹膜后部位有無異常腫塊。而對于沒有配備CT、MRI的婦產專科醫院,在妊娠診斷不明確、病灶位置不明確的情況下,患者生命體征平穩時可建議轉院診治;患者不配合轉院或病情危急不宜轉院者,應在腹腔鏡或剖腹探查術前備好外科手術會診和輸血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