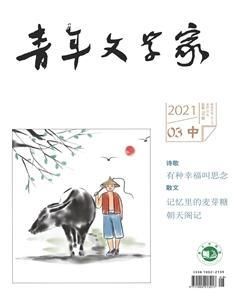論史鐵生文學創作的死亡主題
摘? 要:死亡,是人生里最真實最深刻的宿命。它促使人類認真地思考人的價值以及人作為人的本質規定,一個從不思考死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生,也不可能獲得深刻的啟悟。因此死亡是文學創作永恒的主題。史鐵生的文學創作,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他的筆下,書寫了對生命和死亡的深刻體驗與感悟,以及對苦難、命運、信仰等的沉思默想,而“過程哲學”則是他整個思考的核心命題。
關鍵詞:史鐵生;接受死亡;思考死亡;超越死亡
作者簡介:林雋(1985-),女,漢,廣東汕頭人,大學本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8-0-02
縱然世界如何變遷,有一條規律是不會改變的,那便是生死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千百年來,人們大都在回避死亡,卻又不得不面對死亡;思考死亡,卻畏懼死亡。或許,在我們年少的時候,覺得死亡對我們來說是那么的遙遠,甚至遙遠得模糊。而同樣在年少輕狂的年紀,作家史鐵生,卻已經對這一命題有了深刻的思索與體悟。
一、接受死亡
作為一個“活到最狂妄的年紀而忽地殘廢了雙腿的人”,史鐵生真切地體味到了人生的無常和苦難,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作者這樣寫道:“我終日躺在床上一言不發,心里先是完全空白,隨后由著一個死字去填滿。”當我們看到現在還好好活著的史鐵生時,可以試想一下,當初他在經歷了一番“生存還是毀滅”的痛苦抉擇后選擇活下去的勇氣,可見要不要繼續活下去,為什么而活,一直是史鐵生苦苦思索的問題。
(一)擺脫殘疾的束縛和宿命的掙扎
史鐵生以殘疾為主題的作品里, 求死是試圖擺脫痛苦的沖動。“雙腿癱瘓后,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么勁!”“我一連幾小時專心致志地想關于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心和方式想過我為什么要出生。”
通常,如果生的恐懼戰勝死的恐怖,那么,他就會毅然地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史鐵生并沒有放任這種頹廢的情緒蔓延,因為,幾近絕望并不意味著沒有希望,之所以想到死,那是因為覺得生的不公平,之所以覺得生的不公平,那是因為我們還有欲望,活得更好的欲望。他在《我與地壇》里寫道,“可我不怕死,有時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時候,——說對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兩回事,有時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來就不怕死的人是沒有的。我有時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 可我為什么還想活呢? 因為你還想得到點什么、你覺得你還是可以得到點什么的。”正是這樣對生與死的探究之后,讓史鐵生明白了:對待苦難和困境,惟有平靜地接受。在既定的事實面前,接受比逃避更需要勇氣,只有在接受的前提下,才能有機會去和它周旋,才有機會去解決它。
事實上,每個人的人生路都是在不斷與苦難、困境甚至是死神抗爭的過程,所以學會接受我們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比如說身體的殘缺,比如說差別,當然也包括死亡。只有這樣,才能尋求精神的平靜,而精神才能從逃避與恐懼死亡的奴役中解脫出來。
由于自身的殘疾意識,讓史鐵生的作品中有一種宿命的情懷。而死亡,無疑是人生中最終的宿命。“人生來不想死,可是人生來就是在走向死。”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現“上帝”一詞,人生就像一場戲劇,而人的命運全都在上帝所設定的腳本里。正是由于這種宿命的觀點,讓他的筆下的死亡描寫變得坦然與超脫;死亡是永遠不可逃脫的宿命,既然是宿命安排好,是上帝交給的一個事實,那么,我們就要學會接受,而后超越和對抗。
二、思考死亡
在生存事實上死亡是每個人的必然歸宿,如何擺脫死亡的恐懼,去消解、克服死亡意識的摧毀,是史鐵生在接受了死亡的不可抗拒性后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死亡的意義——由消極到積極
死亡是唯一可以與生存相提并論的話題,想理解和穿透死亡不是容易的事的“然而人什么都可以躲過,唯死不可以逃脫。”明白了這點之后,史鐵生開始去理解死亡,“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當死亡的價值被遮蔽,生命的意義就變成了純粹的世俗的日常生活,變成維持時日”,因此,超脫出來的史鐵生,開始去思考死亡的意義,在史鐵生看來,死亡是必須的,沒有了死亡,哪來生的可貴,沒有了死亡,又怎么會去珍惜短暫的生命。正是由于死亡,才使生的意義有了對照,正是對生命的長度有了限制,才能使我們更好地把握住生命的寬度。那么,既然結局的不可顛覆性,我們對生命更應該關注的,就不是去擔心最終死亡的結果,而是要去思考如何活的問題,如何使生命有意義有價值的問題了。這樣一來,史鐵生更多的是把死亡的消極意義轉變為積極意義,把死亡當作人生的動力和意義的來源。
(二)死亡意象的內在含義
在史鐵生的作品里,有好多人物形象都涉及到老人與孩子。比如說《我與地壇》中那對15年來依然恩愛的老夫妻;《毒藥》中住在島上的老大夫和他的孫子。史鐵生曾說過:“我覺得老人和孩子是最具詩意的。”出生前的世界和死后的世界,在史鐵生看來,都是虛無的。而老人與小孩,正是最接近這兩極的,“老人與小孩”這一對生死辯證意象的設置說明了生和死只是生命的開始與結束之。既然開始是從虛無中來,最后也是回到虛無中去,那死亡和出生一樣,變得不再可怕。
讀史鐵生的作品,總讓我感受到一種澄澈清明的境界,他對死亡的描寫是如此達觀和溫暖,既看到自身生命的中斷又看到它的延續,在生生不息的生命長河中,“我”在其中生生不息輪回不已。在他筆下的死亡,由暗黑變為明亮,由冷酷變為溫暖,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入了永恒,真正走向了人們常說的“天人合一”。
三、超越死亡
對待死亡,史鐵生不僅停留在坦然接受和思考上,而是在超越,也就是要永遠讓生命保持一種不斷想超越困境的向上的飽和狀態,生命在有限的長度內便取得了精神意義上的真正無限。事實上從面對死亡的困惑到坦然理解死亡的必然性,可以看到,史鐵生的作品并不旨在教化,企圖為人類的困境開出什么療救的藥方,而是更多地傾向給人一種溫潤感,給人精神層面上的慰療。
(一)過程哲學——從目的回歸到過程
在史鐵生的死生哲學里,過程哲學是不能忽視的一節,而這,也是回答如何超越死亡這個問題的一個基點。
史鐵生的許多文章都在宣揚一種過程之美,一種“過程”即“目的”的存在,企圖從過程中去尋找生命的意義,比如在《好運設計》中說道:“事實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過程。一個只想(只想!) 使過程精彩的人是無法被奪剝的,因為死神也無法將一個精彩的過程變成不精彩的過程,因為壞運也無法阻擋你去創造一個精彩的過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變成一個精彩的過程,相反壞運更利于你去創造精彩的過程。”這是史鐵生“過程哲學”的宣言。人生的意義不在目的,而在過程。所以我們不應該把人生的意義設定在終極目標上,設定在成功上。
生命意義的呈現從終極目的轉向實踐過程,而當目的被放低而過程被凸出的時候,個人生命的歷程就顯得異常重要起來。生存的意義也少了一些功利色彩,增添了幾分活著的審美樂趣。史鐵生做到了這點,從而以精彩的過程戰勝了死亡的誘惑。而從“目的”回歸到“過程”的這一心理體驗,正是對死亡的一次超越。
(二)大自然的啟發——從個體人生到宇宙人生
在看到目的的虛無與絕望,完成了從目的轉向過程這一質的超越后,史鐵生又把眼光放到了更高的層次——宇宙。從個體人生升華到與宇宙人生,又是對死亡的另一次超越。
史鐵生的文學作品,經常提到一處景物——地壇,它是史鐵生雙腿殘疾后經常去的一處場所。在史鐵生眼里,地壇與自己有許多心靈的契合點,同樣有著被社會遺棄的命運,可蒼老荒蕪的地壇卻并不衰敗且處處涌動著生命,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寫自然。地壇荒蕪但不衰敗的景象,讓史鐵生聯想到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大自然也在經歷著新陳代謝的過程,新生,是在舊事物毀滅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在大自然中,死亡,是新生的前提,是萬事萬物保持活力的一個重要保證。只有生生死死,才能生生不息。而正是在這種無邊無際的空間和無盡無休的時間中的生生不息,死亡的恐懼慢慢消除。
(三)信仰的真諦——精神的仰望
在如何超越死亡的問題上,史鐵生始終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自我,然而死亡畢竟是一個人的“個體事件”,最終需要個體的自我認識去超脫,于是史鐵生從宇宙的高度回歸到個體上,從個體的角度看待死亡,史鐵生又是用什么來超越的?用“神”。“什么是神,其實就是人自己的精神。”而這“神”其實就是信仰。周平國先生是這樣描述對史鐵生的理解的“看到并接受人所必有的限制,這是智慧的起點,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沒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脫,沒有超越,智慧就會淪為犬儒主義。可是,一旦尋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會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
在苦難極處仍未放棄希望,在困境之時仍有所啟盼,這便是信仰的內核,這就好比“天堂”,我們從一出生就在走向它,卻永遠也走不到它,你若永遠地走向它,你隨時都在它的“光照之中”。這,就是信仰的精神力量,也是對苦難和死亡的一種超越。
四、總結
史鐵生是一個生活的沉思者,他隨時可以從極細小極平常的生活現象出發進入玄思冥想,思緒神游于神秘無極之地,馳騁于宇宙大化之境。他屢次經歷過人生的困境,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但他沒有自怨自艾,在與死亡問題的對話上,他從接受到超越,所涉及的角度從個體到宇宙,再由宇宙到個體;他把人生的目的放低,將生命的過程凸顯出來。在他的文章里,讓我們讀到了面對人生困境的勇氣,懂得了信仰的真諦——精神的仰望;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訴我們,只要走下去,就會有路,就會有希望。他有一雙寬厚的手,觸摸的是我們干枯的心靈,手之及處,春暖花開。他亦有一顆勇敢的心,常常省查自己的內心,他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執著追問,對苦難和死亡的苦苦探求,都是他所給予我們的精神財富,他把自己看輕了,但在我們眼里,他卻是厚重的。
參考文獻:
[1]史鐵生.靈魂的事[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 社,2005,21~247.
[2]肖百容.直面與超越:20世紀中國文學死亡主題研究[M].湖南:岳麓書社,2007,127~135.
[3]王堯.在漢語中產生入死[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173.
[4]周國平.安靜[A].胡山林.從苦難走向信仰—史鐵生的心路歷程[C].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