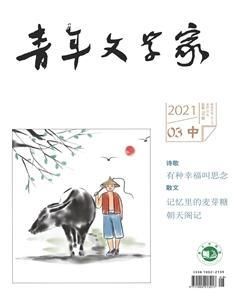從“三言”看馮夢龍融雅于俗、明俗暗雅的雅俗中和
摘? 要:馮夢龍編選的“三言”是中國古代短篇通俗白話小說的瑰寶,馮夢龍嘗試勾連精英模式與民間審美模式使得“三言”兼具民間傳統中對俗的追求與文人品格中雅的意蘊,開啟了文學雅俗結合新范式。本文將從內容趣旨、小說語言、藝術結構三個方面探討“三言”中的雅俗雙重性問題,這也是“三言”最顯著的文化特色。
關鍵詞:馮夢龍;三言;適俗;奏雅
作者簡介:王安溶(1997-),女,漢族,江蘇徐州人,蘇州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8-0-05
馮夢龍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學的搜集、改編、創作,他的通俗文藝作品涉及小說、民歌、戲劇、筆記小品、雜著等諸多領域。因此,馮夢龍被看作明代通俗文學大家,“三言”傳達了市井市民的思想意識。這種認識并非毫無根據,但如果只關注到“三言”在通俗化上的嘗試與價值而忽略其中的廟堂意識、文人文學成分,那就是對馮夢龍的誤讀,勢必無法認清復雜文學現象的本質。馮夢龍正是通過融合民間傳統與文人文學,提高了“三言”美學層次,使之成為適俗奏雅、雅俗共賞的典范。
一、馮夢龍“市井文人”的小說雅俗觀
明末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江南市鎮興盛,出現了“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的全民重商潮流。在這股潮流中,大量農村人口和城市居民成為手工業主和大商賈的雇工,從而形成了市民階級群體,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思想觀念既不同于傳統士人,也有異于農民階級。像馮夢龍一樣的 “市井文人”混跡于市民當中,這些文人有著和下層市民相似的意識與志趣,他們既是市民的精神領袖,又深受市民意識的熏染,形成文人市井化與市井文人化的局面。可以說,馮夢龍市井文人的身份使他的文學活動必然蘊涵俗文化的因子。加之明中后期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出版蓬勃發展,蘇州的刻書商有幾十家之多,他們除了刻印文人所需的經史子集與應考讀物,也刻印大量通俗讀物,面向市井,滿足市民階級的需求,借此獲利。“三言”就是馮夢龍應賈人之請而編輯整理,在士商互動下,馮夢龍的創作有面向市民群體娛情適俗的需要。馮夢龍思想來源涵蓋豐富,除了市民階層思想的熏染,李贄性情論的絕假存真與陽明心學的關懷世事都使得馮夢龍走向俗文學的創作。然而,商業發展也會使世人墮入好貨好色的媚俗泥潭,進步思想與落后因素共生的社會需要一套適俗以化俗的創新性話語來挽救世道人心,馮夢龍適俗奏雅的審美動機就此形成。
雅俗共賞的“三言”是馮夢龍多元化價值取向的創作嘗試。在馮夢龍以前,小說難以尋求雅與俗的平衡點,始終處境尷尬,難以贏得文學尊嚴與地位。宋元話本使馮夢龍看到一塊雅俗調適新天地,小說是可以成為“六經國史之輔”的。馮夢龍認為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因此要通過“觸里耳”以“振恒心”,“觸里耳”即是馮夢龍對俗的追求,具體來說,馮夢龍對適俗的要求就是讀之令人“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2]但適俗絕不是媚俗,馮夢龍對雅的品格也有明確的闡述,“雅行不驚俗,雅言不駭耳,雅謔不傷心”[3],從雅的一面出發,有意剔除小說中的媚俗成分,與低級審美拉開距離。僅有適俗的效果和雅正的品格都不是馮夢龍的目的,“三言”的書名“喻世”、“警世”、“醒世”直接體現了馮夢龍志在化俗奏雅的良苦用心,在《醒世恒言》序中,他說“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4]“導愚”和“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的目的能否實現,關鍵在于“適俗”是否成功。也就是說,“觸里耳”的適俗是手段,“振恒心”的施教奏雅是最終目的。在“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中,令“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5],以達到不驚俗、不駭耳、不傷心之雅。這也是“三言”雅俗整合的主要表現,然而馮夢龍的雅俗調適不止于此,除了內容形式的適俗與主題趣旨的奏雅,在小說的語言和藝術結構上,馮夢龍也做出了雅俗結合的嘗試。
二、觸里耳而振恒心:內容主題的雅俗結合
(一)小說之資于通俗者多
馮夢龍指出圣賢經典“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彥,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6]普通百姓市民很難得其要領,往往只會“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后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而用淺顯通俗的語言“當場敷演”卻可以得到感人“捷且深”的效果。基于通俗的要求,“三言”一百二十篇中,題材不再局限于王侯將相、才子佳人、鬼神志怪,而是選取耳目之內的“庸常之奇”以適俗。李贄說“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于平常也。”[7]世人皆知牛鬼蛇神為奇,卻常常忽略俗人俗事俗情也能常中出奇。三教九流、油鹽醬醋、街頭巷尾,在平常市井生活的敘寫中添加富有特征、一波三折、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的描寫更能使人“拍案驚奇”,進而實現馮夢龍導愚濟世的理想。其中,商業活動與女性婚戀題材是“三言”中最具特色的“庸常之奇”。
深受“商人重利”、“商賈末流”觀念影響的中國文學在對商人群體進行藝術抒寫時,審美慣性使得商人群體備受抨擊。直到明中后期,崇商、好貨已成為社會普遍心理,商人不再是“義”的對立面,傳統四民士、農、工、商的秩序已變更為士、商、農、工的新秩序,經商是善業而非末流的觀念深入人心,普通市民對于經商生活尤其是商賈致富經歷更是充滿好奇,因此經商生活題材小說正是馮夢龍適俗的利器。據筆者統計,主要表現商人形象及生活的小說,《喻世明言》6篇,《警世通言》5篇,《醒世恒言》9篇,這還不包括以商人為配角、偶爾涉及商人的篇目。其中,有集中表現商賈細民追逐錢財、發家致富的。《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的施復本是個養蠶的小手工業主,但他極其渴望發家致富,夫妻二人“省吃儉用,晝夜運營”不到十年就有數千金積蓄,搬進更大的居所擴大生產規模,家業愈發興盛。《徐老仆義憤成家》中老仆阿寄在毫無經商經驗的情形下,帶著主母的十二兩銀子經商,最終為主婦掙下家業而發家致富。《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汪革憑借辦鐵冶、開酤坊發家。《劉小官雌雄兄弟》中劉方靠經營布店發財致富。《宋小官團員破氈笠》一篇則展現宋小官由落魄世家子弟涉足商業,冒險起家全過程。在經商題材篇目中,商人形象也不再僅限于重利輕義的奸商,而是顛覆儒家輕視商賈的傳統塑造了市井細民喜聞樂見的義商形象,他們誠信經營、濟世救人、宅心仁厚。《劉小官雌雄兄弟》中“劉公平昔好善,極肯周濟人的緩急。”劉德身為商人不重利,反而重商人與顧客間的情分,誠實經營、待人寬厚是他的經商特色。在素昧平生的老軍病倒之際,掏錢為其醫治并將其厚葬。《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中的商人李秀卿與女扮男裝經商的黃善聰皆以誠相待,兩邊買賣毫厘不差。《轉運漢遇巧洞庭紅》中的文若虛賤賣夜明珠后寧可自己吃虧,也誠實守信不再向波斯人討要更多銀兩。士商互動是“三言”商業題材引人入勝的又一招牌。隨著明末商人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有錢而無社會地位的商賈可以通過聯姻以富博貴,貧寒的文人士子可以通過聯姻得富且貴。《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是最具代表性的士商互濟篇目,表面看來是男婚女嫁的俗套,實則是富商之女嫁給貧寒有才書生的特殊婚姻,從中可以窺見晚明社會婚姻觀與價值追求的異變。不僅如此,科舉不第的文人也擺脫了“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思想,《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楊八老越國奇逢》、《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都有棄儒從商的情形。如此士商互動符合明末市民的意識與期待,無論“內圣外王”還是經商從利,只要有利可得,方式不必計較。可以說,“三言”中的全新的商人題材是馮夢龍尚奇適俗的一塊金字招牌。
與時代思潮、市民意識相通的情愛婚戀題材是馮夢龍“適俗”的又一個陣地。明中葉后,好貨、好色之風日盛,市民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個性欲求的強烈滿足,“書生落難,小姐搭救,考取功名,奉旨完婚”的俗套已經無法適俗,大膽展露男女情愛、擺脫婚姻宿命論等反映庶民真實情感世界的題材成為市井細民喜聞樂見的文藝樣式。“三言”中有大量沖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膽追求愛欲的婚戀故事。《閑云庵阮三償冤債》中的陳玉蘭,《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中的李鶯鶯,《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的劉素香。她們大膽主動地追求自己地心愛之人,是自主意識的覺醒和張揚。此外,這類題材還贊揚了才貌雙全、膽識過人的女性,《蘇小妹三難新郎》中的蘇小妹“聞一知十,問十答十”,出眾的才華不遜于男子,才名使她贏得了美滿的婚姻。《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中的黃善聰、《劉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劉方都靠女扮男裝,憑借機智與膽略將生意經營得風生水起。這些沖破“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束縛的形象正符合晚明市民對以情抗禮的期待。“三言”中對妓女內心世界的關照更是難能可貴,據筆者統計,“三言”中出現的妓女有16人。晚明是一個縱欲奢靡的時代,一時間娼妓滿布天下,文人與妓女的交往更加大膽直接,市民對這群貌美才高的飄零女子也有更多的好奇與想象。妓女的身份似乎規定了她們就是朝秦暮楚、放蕩輕節,但玉堂春、杜十娘、莘瑤琴等重情重義、渴望從良、具有反抗精神的顛覆性形象產生了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是至情時代思潮的一個縮影,更是馮夢龍適俗以教化世人的教材。
(二)曲終之奏,要歸于正
馮夢龍以尚奇適俗為手段,適俗背后的導愚是他的真正目的。他說“忠孝為醒,而悖逆為醉;節儉為醒,而淫蕩為醉;耳合目章,口順心貞為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囂為醉……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之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8]馮夢龍認為世人皆醉,他嘗試用“三言”中適俗的故事即市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暗遞導愚的教化,“醒”天下,“醒”世人。而勾連適俗與化俗導愚的是“情教”,晚明日益僵化空洞的程朱理學已經無法有效約束迷醉的世人,而馮夢龍獨創的“情教”以情為基,動之以情,使人自覺無情化有、私情化公,進而拯救世風,因為“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9]可以說,馮夢龍的“情教”實際上正是試圖將禮教性情化,重新詮釋封建禮教,把禮教建立在情的基礎上,追求一種自然行于理又自然發乎情的理想境界,卻忽略了封建禮教和情有著天然的沖突,因此這種以“情教”勾連適俗與化俗導愚的嘗試更多的是書齋式的烏托邦理想。一方面馮夢龍是李贄的追隨者,對孔孟抱有嘲諷的態度,肯定婦女才智、獨立的人格,是時代的叛逆者,但另一方面,馮夢龍“醒天”卻不能“破天”,作為儒士,他還是自覺肩負起社會責任,文以載道,導愚也就大多限于忠孝節義的倫理層面,帶有封建說理的成分,這就導致了馮夢龍思想的矛盾復雜性。
“三言”中有不少作品抨擊了見利忘義、謀財害命、薄情寡義的行為,丑惡之人最終受到了懲罰,如《陳御史巧勘金釵鈿》、《蘇知縣羅衫再合》、《沈小官一鳥害七命》。也有作品勸誡世人謙虛謹慎,不可心高氣傲惹是生非,如《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勸告市民重義守諾的篇目占據“三言”的六分之一,其中《羊角哀舍命全交》、《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等都起到了“振恒心”捷且深的教化效果。然而,馮夢龍在涉及婚戀、貞操等問題時又顯現出封建倫理說教的傾向。在婚戀觀方面,盡管馮夢龍贊揚女子沖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縛,但他同時將這種勝利歸為清官的支持、父母的開明。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玉郎和慧娘的成功結合正是太守的開明與官府的支持,這是從側面肯定了封建秩序。除此之外,馮夢龍認可一夫二婦、雙妻團圓的婚姻模式,《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楊八老在家在外各一位妻子相伴反而被認為是情理之中。男子可以雙妻圓滿,而女性卻要從一而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王三巧失貞后,盡管蔣興哥身上展現出晚明市民意識中通脫開明的一面,但馮夢龍依然安排王三巧由妻變妾作為懲罰。《張寧妾》中知府張寧死后,兩個年僅十六歲的小妾卻要封門守節,為情似乎談不上,馮夢龍卻禮贊備至。在忠孝觀方面,“三言”贊揚勸導市民孝悌的同時也中不乏對父母的“愚孝”與對朋友的“愚忠”。《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宋金患病被岳父拋棄,妻子被迫改嫁,但夫妻團圓后,宋金仍說“但記恩,莫記怨。” 《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楊八老多年離妻別子,杳無音訊,然而兩個兒子一旦發現他是生身之父便抱頭痛哭,使之安享榮華。《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中為了朋友間的再見面的約定不惜棄家舍命,近乎違背人倫。
雖然“三言”內容形式的適俗與主題趣旨的奏雅結合得略顯生硬,甚至在“曲終奏雅”中還含有封建消極思想成分,但馮夢龍受到時代、篇幅的限制,達到如此境界已實屬不易,“三言”在內容主題中閃現的人文主義光輝仍尤為可貴。
三、語韻則美于聽:小說語言的雅俗共賞
(一)話須通俗方傳遠
針對天下文心少里耳多的情況,馮夢龍反對“尚理或病于艱深,修詞或傷于藻繪”[10]的文學形式,提出“話須通俗方傳遠”的藝術原則。“三言”大量使用民間俗諺語、延用說話藝人表達模式、運用通俗活潑的散文描摹人物,一方面拉近了與市民的距離;另一方面,通過貼近市民階層的審美,引起共鳴,以施情教。
民間俗諺語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口頭語言的精粹部分。“三言”中使用俗諺語之多、范圍之廣,在前代小說創作中是為少見,開啟了明代擬話本小說喜用俗諺語的先例。據筆者統計,“三言”平均每部俗諺語100條,每篇或多或少涉及俗諺語。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頭”生動刻畫用心險惡、唯利是圖的薛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預示蔣興哥夫妻破碎的情感。《大樹坡義虎送親》中有“奉勸人行方便事,得饒人處且饒人”、“一人立志、萬夫莫奪”,“一女不吃兩家茶”、“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有“一夜夫妻百夜恩”、“一客不煩二主”。《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中有“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以上這些俗語警句的運用透視世態人情,使得作品充滿質樸生動的生命力。
“三言”諧于里耳的語言還表現在延用說話藝人的表達模式上。“話說”、“卻說”、“話分兩頭”、“且聽下回分解”、“閑話休提”等標志性說話套路帶有話本敘述語言的層次性特點,推進藝術情節的展開,承上啟下的同時模擬民間說話時面對面交流的氛圍,使得村夫稚子、里婦估兒更易沉浸其中,是“觸里耳”的關鍵紐結所在。
“三言”雖經馮夢龍的藝術加工有不少由俗趨雅的文人痕跡,但為了“不致有嚼蠟之誚”,“三言”追求自然通俗的語體。在人物的刻畫上,馮夢龍常用流暢的口語白話生動展現人物特征,揭示人物隱秘的心理。《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將張舜美輾轉反側思求佳人的煎熬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害得那婦人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將王三巧被薛婆蠱惑時羞愧卻又蠢蠢欲動的心理生動呈現。《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成功刻畫了范巨卿為義舍命有情有義的形象,“用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平白流順、三言兩語就勾勒出張范二人超越生死的友情。
(二)不雕琢而味足
“向下看”的文化下移趨勢要求“三言”語言自然通俗,但對于過于俚俗甚至“鄙俚淺薄,齒牙弗馨”[11]的媚俗語言,馮夢龍極力反對,提出“不雕琢而味足”的標準,于平白淺順的通俗語言中點綴文人典雅之氣,達到俗中透雅的審美意境。
“三言”語言的雅化傾嘗試主要表現在詩詞韻文的穿插使用上。馮夢龍常用韻文精致勾勒小說情節鋪展的環境、景色或背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戈戟九邊雄絕塞,衣冠萬國仰垂衣。太平人樂華胥世,永保金甌共日輝”以典雅韻文交代了燕京的繁盛熱鬧景象,引出杜十娘與李甲的交往。《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甲馬從中立命,刀槍隊里為家。殺戮如同戲耍,搶奪便是生涯”凝練精巧地描摹出百姓一直以來忍受的苦楚。“三言”中對人物的刻畫采用韻散結合的方式,《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以“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勾畫出杜十娘的艷容。《唐解元一笑姻緣》中借唐伯虎一首詩作引出唐伯虎的身世與高才。《蘇小妹三難新郎》里的蘇小妹閑來斗嘴皆用文氣盎然的韻文,烘托才女的智慧才學。“三言”詩詞韻文往往還用于點化主旨、總述內涵。《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才離地獄忽登天,二子雙妻富貴全。命里有時終自有,人生何必苦埋怨?”點出人生境況自有天意。《賣油郎獨占花魁》以“春花處處百花新,蜂蝶紛紛競采春。堪愛富家多弟子,風流不及賣油人”贊美市民沖破傳統婚戀觀的自由愛情。總之,詩詞的滲入,提升了“三言”的典雅之氣,不至于平鋪直敘、殊傷雅致。韻散結合的語言達到“不事雕琢而自然曲盡事物之情”的境界,呈現出雅俗中和之美。
另外,對于宋元話本中說話人粗俗露骨的野性敘述,“三言”斟酌字句將其隱去并滲入含蓄儒雅的文人教養,如《閑云庵阮三償冤情》由《戒指記》改訂,情節意旨不變的基礎上,減少了色情成分增加了委婉風流。《柳耆卿詩酒玩江樓》中的柳永本是潑皮無賴,行止使人讀來“齒牙弗馨”,而馮夢龍改訂后的《眾名姬風流吊柳七》隱去了鄙陋的情節與露骨的語言。
四、事韻則美于傳:藝術結構的雅俗調適
(一)無聊極至,亦奇亦真
宋元話本人物不多,情節單薄,多為單線結構。為了迎合村夫稚子、里婦估兒的審美意趣,最終達到“觸性性通,導情情出”的效果,馮夢龍對“三言”情節的編排大費心機,對敘述藝術大加擺弄,突出情節沖突感、緊湊感,多為雙線、多線結構,篇幅也達到一萬字以上。
“三言”適俗的精巧設計集中體現在擅用“物象道具”上。所謂“物象道具”是指在結構上貫通情節、在題旨上深化意蘊的實物。“三言”中的“物象道具”通常于一篇故事中反復出現,與人物、情節、主旨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這樣的實物也超越了物象本身的敘事意義,擁有了深層象征指向。用“物象道具”連綴故事雖不是馮夢龍首創,但在前代小說戲劇中,由于人物、情節簡單且集中,“物象道具”并沒有發揮重大作用,也沒有得到特別的關注。“三言”中選取的實物通常本身具有隱喻指向,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百寶箱正是指向杜十娘自身金玉般的人格價值;《范鰍兒雙鏡重圓》中的鴛鴦鏡本就承擔男女情愛見證的功能。另外,實物兜兜轉轉物回原主也是“三言”常用的敘事藝術,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蘇知縣羅衫再合》、《黃秀才檄文玉馬墜》。以下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說明擁有隱喻指向的“物象道具”通過物回原主串聯情節、點化題旨。此篇實物“珍珠衫”作為貼身衣物,本身具有曖昧與情愛的隱喻指向,蔣興哥將珍珠衫贈與妻子王三巧,王三巧卻在蔣興哥外出經商時與陳大郎偷情并贈他珍珠衫,戲劇性的是接下來蔣興哥與陳大郎偶然結識,看到珍珠衫明白妻子的背叛,忍痛休妻,陳大郎病故后珍珠衫落于已改嫁蔣興哥的平氏手中,王三巧嫁于后夫后又與蔣興哥重逢決定再續前緣,蔣興哥遂將珍珠衫重贈王三巧。在這個故事中,正是珍珠衫促使蔣興哥發現妻子的二心,觸發全篇情節展開,珍珠衫重回王三巧手中,意味著曾經失足的她因真情尚存與丈夫破鏡重圓,這正是以情反理時代思潮的縮影,珍珠衫是承載情與理的抗爭的載體,點化出真情至上的題旨,通篇也因珍珠衫的串聯而情節緊湊集中、新巧通俗,為市井細民所喜。
(二)頗存雅道
馮夢龍對宋元話本體制的改造使得“三言”成為獨具特色的書面文學形式,正如凌濛初所說的“頗存雅道”。體制規范化的“三言”兼具了民間說話與文人文學兩大文學資源,為后世話本作家提供了一個范本。
宋元話本的題目多以人物、事件隨意命名,字數不等,而“三言”題目的選取則經過馮夢龍的精心推敲,采用對仗工整的對偶命名,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新橋市韓五賣春情》與《閑云庵阮三償冤債》。題目的選取不僅限于對偶工整,還要考量兩個相連題目在內容上的勾連關系,如《單符郎全州佳偶》與《楊八老越國奇逢》皆是一夫二妻團圓模式,《羊角哀與舍命全交》與《吳保安棄家贖友》都是贊揚友情義氣的內容。這種命題方式一改宋元話本擇題的隨意性與粗糙性,滲入了文人審美的范式之美。
入話是宋元說話藝術中正話開始前的一道準備程序,通常由詩詞或故事組成,用以拖延開場時間以待聽眾落座。入話作為說話藝術的成分,在書面文學創作中本應失去價值,但馮夢龍卻進一步改造完善入話,使“三言”在體制上更具文人規范,主要表現為在宋元話本中,入話可有可省,馮夢龍在編纂“三言”時將缺失的入話補上,《柳耆卿詩酒玩江樓》中本無入話,“三言”的《眾名姬風流吊柳七》就以孟浩然錯用詩詞終身不被用的故事作為入話添入。另外,即使前代話本故事中有詩詞或故事作為入話,但其內容多與正話不相干,僅僅用以愉悅聽眾、暫緩開場,而“三言”中經馮夢龍改造的入話皆與正話緊密相連,或點明創作動機或點明導愚的勸誡教化思想,如《范巨卿雞黍死生交》開篇以一首《結交行》作為入話詩詞,以便引出秀才張邵與范巨卿結下死生之情的正話,也點明結交最難,義重于生死的教化主旨。《賣油郎獨占花魁》開篇以一首《西江月》作為入話詩詞,道出風月場中有錢有貌不如知情識趣,又以鄭元和與亞仙的故事印證善于幫襯、著意揣摩比財貌更得人心,而后才接入識趣真摯的賣油郎抱得美人歸的正話。
五、小結
“三言”通俗而典雅的形式與所表達的內容完美結合,達到了語韻、事韻的統一,具有中和之美的審美意蘊。當然,“三言”雅俗相宜的嘗試除了表現在題材趣旨、小說語言與藝術結構這三個主要方面,在小說審美趣味與諸多細節上也滿溢出雅俗共賞的韻味,而對于“三言”中頗受爭議的部分倫理說教,在今天看來未免腐朽可笑,但在馮夢龍所處的時代與環境,這些教化也有著凈化時代的感染力與震蕩人心的美學沖擊力。馮夢龍以適俗奏雅的姿態開啟文人介入話本小說創作的新局面,雅與俗的相互纏繞成為明清白話小說的文化特色,雖然文人的參與越來越使話本小說失去原本潑辣質樸的原始生命力,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清代話本小說走向衰微,但必須看到話本若只是作為民間技藝口耳相傳,僅有村夫稚子、里婦估兒的參與和接受,那么最終難免悄然自滅,連短暫的興盛也很難出現。
“三言”是民間審美蓬勃自發的原始生命意識與精英文化自覺的理性控制交融的呈現。露絲·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創造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社會群體的選擇,而選擇就形成了“文化模式”,我們需要肯定馮夢龍在勾連精英模式與民間審美模式上所做的探索性努力。
注釋:
[1]聶付生:《馮夢龍研究》,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2][4][5][6]高洪鈞:《馮夢龍集箋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頁,第80頁,第81頁,第83頁。
[3]馮夢龍:《古今譚概》,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19頁。
[7]李贄:《復耿侗老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頁。
[8][10]馮夢龍:《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第4頁。
[9]馮夢龍:《情史》,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第5頁。
[11]馮夢龍:《喻世明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參考文獻:
[1]傅承州.馮夢龍與通俗文學[M].大象出版社,2000.
[2]繆泳禾.馮夢龍和三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M].上海書店,1984.
[4]石麟.話本小說通論[M].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
[5]王增斌.明清世態人情小說史稿.中華文聯出版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