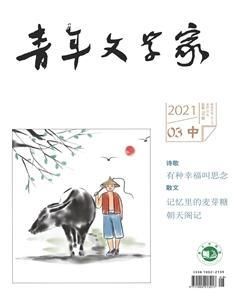萬化禪心入丹青
摘? 要:王維的山水詩雅淡清新,散發悠悠禪意,他將個人對禪理佛趣的獨到感悟不著痕跡地注入自然山水的感性形式中,達到“不用禪語,時得禪理”的至高境界。詩中的禪意主要表現在詩人對空寂罄澄,悠游散朗的禪境,物我兩忘,萬化冥合的禪心以及言近旨遠,微言妙諦的禪機的追求上。其山水禪詩開創了詩歌“神韻交融”的新境界,對后世文壇影響深遠。
關鍵詞:王維;山水詩;禪意;美學境界
作者簡介:李爽(2000-),女,漢族,江蘇鹽城人,揚州大學文學院本科,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師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8-0-02
畫境和禪意是王維山水詩美學境界的重要維度,王維秉承“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的禪宗觀,將自然界的一機一境化作一片禪心,融入丹青畫境之中。其詩中蘊含著的悠遠的禪意哲思和獨特的人生態度值得后世不斷地去發掘、咀嚼和開拓。
一、禪境:山水空靈
王維以“空”觀萬物,其筆下描繪的林泉山石、云鳥花月,大都表現了空寂罄澄,悠游散朗的美學境界。
1、空寂罄澄
王維詩中的禪意,集中表現為對空寂罄澄境界的追求。空,是禪宗的核心理念;靜則是達到佛我合一最高境界的法門。王維在超然物外的空寂中體悟禪意,使詩歌格調高遠悠廣。在其近四百首的存詩中,“空”字大致出現了90余次,與山、林、谷等意象相關聯,打造了一個空寂無為的精神境界。
其中,“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更是婦孺皆知的妙句。詩人以開闊的視野勾畫出晚秋微雨后山林清新怡人的風景。“空山”兩字一出,就將人帶入一個空靈遠俗的世界,使全詩都籠罩在一片清悠澄靜的氛圍中。這里的空,不是空無一物的光禿死寂和荒蕪蕭索,而一種滌盡了繁華與浮躁的干凈澄明,是一種潛藏生機與活力的靜謐美好。山“空”使人心“空”,心空才能賞常人不可觀之景,覺常人不可聽之音,感常人不可觀之微,悟常人不可得之慧,以達到禪宗“明心見性”的旨歸。
2、悠游散朗
王維山水詩中的禪意,還表現為悠游散朗,閑適自如的境界。
禪宗吸取了老莊的無為思想,認為“萬法本閑人自鬧”,但想悟道,便要清心,方能達到禪宗所稱道的“任性逍遙,隨緣放曠”的境界。王維晚年半官半隱棲居輞川山林,徜徉青山綠水之間,過著閑適悠游的生活。其膾炙人口的《終南別業》一詩,便是詩人閑適逍遙的生活和曠達隨緣的心態的傳神寫照。
其中“行到水窮處, 坐看云起時”被譽為千古佳句。詩人緣溪而行,隨興而至,卻不經意間行至山窮水盡之處。同樣的情形,不禁讓人想到魏晉時期的名士阮籍,常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途窮興闌乃是人之常情,更何況現實中郁郁不得志之士。率意獨駕雖看似瀟灑不羈,卻更顯失意之悲涼。而王維卻并不因山窮水盡而打破內心的平靜,他既無興闌之索然,也無探幽之執著,于是干脆坐觀云起,不為物拘,與禪宗所謂“自由自在,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如出一轍。俞陛云贊其詩境“有一片化機之妙”。
禪宗所倡“但求任心自在, 快樂無憂”的境界,不僅體現在王維的生活和心態中,更是潛移默化地滲透進他對山水的審美關照里。他筆下一花一木,無不展示著他超然灑脫的人生態度: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靜謐的山林中,盛開的桂花悄然無聲地從枝頭脫落飄飛,悉簌地擦過詩人耳畔,凝神諦聽,花開花落,盡是天籟之音。“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泛舟湖上,漫隨天外,去留無意,全然忘機,看天空去卷云舒。“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雨夜秋山,燭火微明,靜謐之中聽果落蟲吟,禪味野趣盎然。“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綠萍滿池,風吹楊柳,柳枝掃開微隙,弄皺一池春水……更有《辛夷塢》一詩,被譽為“清幽絕俗”的“入禪”之作。在遠離塵囂的山澗旁,辛夷花靜靜地盛開又默默地凋零,無人欣賞它的綻放,也無人傷懷它的隕落,然而它并不在意這些,只是順應自然的本性,綻放凋零,無悲無喜,絢爛之至又終歸平淡,在花開花落的更迭間闡釋禪的真諦。東坡《十八羅漢頌》嘆其境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得其任世界自在興現之妙。在這些詩中,自然界的萬物都安恬平和,得其所趣,這無不是作者悠閑恣意的心態的寫照。
二、禪心:萬化冥合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古代的文人大多都具有濃厚的山水情結。大自然鬼斧神工所造就的奇山異水是文人最忠實的知音,它們以博大的胸懷為文人提供了一個怡情悅性的精神家園。
然而,詩人們有意無意間往往將入世情緒帶到自然中,情寄山水卻放不下現實種種,并不能處在與花鳥魚蟲平等的地位關照萬物。他們或是以仰望的謙卑關照永恒的萬物,顯得個體的格局促狹,引發詩人心靈的自我矮化;或是以俯瞰的傲然睥睨“低等”的生命,滑入狂妄自大、悲天憫人的虛幻中,使心靈難以承受現實之重。無論是哪一種情形,詩人與自然之間都隔著一層屏障,難以真正體會山水自然中凝聚的智慧和真諦。
王維真正把自己的身心融入自然之中有別于將山水作為短暫排遣工具的文人墨客,他對山水的傾心已達到了世俗兩忘的境界。在《戲增張五弟·其三》中,詩人表明了自己的心跡:“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云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詩人能夠真正摒棄一切俗塵雜念,以無待、忘我、平和、曠達的姿態徜徉在自然的懷抱中,與云霞為伴,與鳥獸相親,以山水為師,與萬化冥合,全然達到禪宗所謂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至空之境,才能真正會自然之趣,悟禪理之妙,使詩歌達到常人難以企及的超然之境。
三、禪機:微言妙諦
王維將佛學經義完美地滲透進詩歌的生命中,其中的禪機不僅體現在詩歌的內容主旨上,還從詩人高超純熟的表現手法中多有流露。
1、即目入詠
王維將禪宗“現量觀”貫徹到了詩歌創作中,在表現自然之美時,大多采用直寫白描的表現手法,即目入詠,將觸目所及的景物原生態地呈現給讀者,較少運用比喻、擬人、夸張等藝術加工手段,也極少對自然景物作帶有明顯思維痕跡和主觀色彩的評判。
如《輞川閑居》:“青菰臨水拔,白鳥向山翻。”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一幅清腴明朗的輞川風景圖。翠菰、綠水、白鳥、青山相互映襯,色彩清新明朗;青菰臨水,白鳥翻飛,一動一靜,一近一遠,交相輝映。詩人以敏銳地捕捉到山水之美和自然之趣,以白描的手法托出,表面上似乎是樸素的敘述,實則將自己精微鮮活的感覺印象最為直接地傳達了出來,細節描寫更是觸發讀者無限的聯想遐思。
又如《山居秋暝》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一動一靜間愈顯其靜,一鬧一幽中愈顯其幽。此句初讀,似與王籍“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細品才發覺王維的詩在意境上更勝前人一籌。王籍的表達過于直露,更像是在說明一個精深的哲理,缺少了留白空間,其意境不是由讀者自己產生的體會,而是詩人在體驗景物特點后經過咀嚼、取舍后剩余給讀者的。而王維沒有用“更”“愈”等帶有明顯思維痕跡的字詞,而以畫家筆法將眼中所見之景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把其中無限想象的美好空間留給讀者,使得詩歌含蓄雋永、意味無窮。
2、動靜相宜
“禪是動中的極靜, 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動靜不二, 直探生命的本原”。王維受般若靜觀的影響,在其詩文中將動靜結合的“藝術辯證法”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試看以下詩句:
聲喧亂石中, 色靜深松里。
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詩人描繪大自然幽靜的景色,并不一味地從空寂無聲上發力著筆,而是敏銳地捕捉到來大自然的天籟之音,把握住主體和客體之間動靜相宜的契合點,奏出一曲靈動和諧的山水清音。不僅沒有沖淡整個環境的僻靜幽邃,反而愈加襯托出靈山秀水的清幽空明,自然萬物的盎然生機,將心靈和自然契合無間的渾然之美表現得淋漓盡致。
3、六識互通
佛家認為,人有六識,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識間融匯相通,便可使其所了辨的“色聲香味觸法”彼此間相生互轉。體現在文學作品中,便是通感手法的運用。王維巧妙地利用六識間的挪移互通,突破思維的定勢和語言的局限,化抽象為具體,變平實為生動,創造出奇妙而生動的美學意境。
如《山中》一詩中的“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詩人觸目所及皆是青山蒼松翠柏,翠色濃重,似流欲滴,仿佛化作一片翠霧包裹著置身其中的行人,沾濕了人的衣襟。一個似幻似真的“濕”字將視觸感覺相互糅雜,將視覺上的翠通感為觸覺上的濕表現出來,從而將山中濃烈的翠色變得可觸可感。又如《過香積寺》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一句,詩人將耳聽目視之景,用“咽、冷”的觸覺來表達,寫聲寫色逼真如畫。再如“綠艷閑且靜,紅衣淺復深。”“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里。”用“閑”“靜”來繪“色”,以聽覺、感覺來寫視覺;“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澀。”以“澀”來摹歌,用味覺表聽覺……通過六識間的聯通轉化,王維將客觀世界中看似尋常的景色,新穎生動地搬進山水詩里,意趣幽玄,引人遐思,妙在文字之外。
結語:
王維的山水田園禪詩,無論從題材內容方面還是藝術技巧方面都對后世文壇影響深遠。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詩宗,他的詩歌對中唐詩人尤其是大歷詩人影響最為深刻。王維從觀照自然的一機一境中悟道明理,以最常見的意象來表達精妙的詩思,為后世宋詞的創作樹立了一個標桿。其詩歌空靈灑脫的意境對后世的文論也影響深遠,清代王漁洋所標舉的 “神韻說”就是受到了王維山水詩的啟發。王維以澄凈之心觀照自然,以隨緣之心對待人生,對現代人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精神文明普遍失落的當下,摒棄浮躁,回歸本心,實現生命“詩意的棲居”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謝思煒:《禪宗與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
[3]周汝昌:《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4年.
[4]王維撰,陳鐵民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5]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