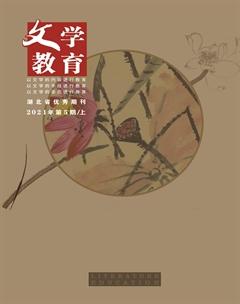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制謎”與“解謎”

當一個孩童或少年初次面對世界時,他總會有許多的疑慮,因為每一個現象都包蘊著他從未見過的人世風景,每一次邂逅都內含著無窮無盡的人性謎題。就像曉蘇《上個世紀的疙瘩》中那個13歲的少年楊叉,他經歷了種種迷茫、尷尬、困惑,最后豁然開朗,深切地領悟到了成長中的傷心與力量。
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楊叉都遇到了令人疑惑的事情。地點依然是曉蘇心愛的“油菜坡”:
在初春,楊叉為了給父親取暖去挖樹疙瘩。他發現了一個碩大的柏樹疙瘩,因鋤頭出了問題沒法挖出來,同去的小伙伴馬燈又不愿意幫忙,他只好將疙瘩掩蓋起來去上學,等他放學再去時,疙瘩失蹤了,馬燈拒不承認;
在夏天,楊叉親眼見到了一樁令人不解的“盜竊案”:鐵環憤怒地揪著梁山的衣服,一口咬定那是他偷的自己丈夫的迷彩服,梁山一口否定,兩人相持不下;
在秋天,楊叉在白蠟家的玉米地附近放牛,見到憨人趙匡無償地幫助白蠟掰玉米棒,累得滿頭大汗,毫無怨言;
在冬天,油菜坡又發生了一件怪事,眼看快過年了,麥成家的豬被人偷了。麥成找到“嫌疑犯”吳光論理,卻差點被打得半死。就在這個季節,楊叉發現他在春天丟失的柏樹疙瘩在馬燈家里熊熊燃燒,香氣四溢……
在小說中,曉蘇進行了巧妙的時間設置,不但讓故事發生在世紀末——一個除舊布新的關鍵節點,而且讓諸種怪事均勻地分布在每個季節,所涉之物與季節變化相關,也與村莊中的人際關系緊密纏結,敘事由此從“時間”滑向“人事”。這些怪事都關涉到“偷盜”“丟失”,最終又在這一年年末也是世紀末的深冬得到了令人喟嘆的解答。
這個時間設置具有重要的人類社會學的原型隱喻:一個少年在時間的循環中被各種陌生之物所纏繞,在成長中一一找到了答案,并最終走向成熟。楊叉將以上怪事形容為“疙瘩”,百思不得其解:“打一個比喻吧,這一連串蹊蹺的事情就像是一個又一個的疙瘩結在我的心頭,讓我無法解開。”冬天到來時,當他在馬燈家發現了那個“失蹤”的柏樹疙瘩時,捂了一整年的一連串內心的“疙瘩”也解開了。“說完柏樹疙瘩,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想多說了,再說就畫蛇添足了。……我認識到,人這一輩子,無論碰到什么樣的疙瘩,終究都會解開的。”因此,梁山有沒有偷衣服、憨人趙匡為什么幫白蠟干活、豬小偷到底是不是吳光,答案不言自明,它們就呈現在敘事邏輯里,其所關涉的人性之惡、人性之謎也逐一敞開。
從曉蘇以往的小說來看,他很擅長“制謎”,但通常不會主動“解謎”,而是通過種種佐證旁物,讓“謎底”不證自明。比如《回憶一雙繡花鞋》中老石匠溫九收到的“繡花鞋”到底是哪位巧娘子所送,《我們的隱私》中的“我”、妻子、麥穗各有什么秘密,《酒瘋子》中的懦弱男人為何突然理直氣壯地指點江山,都是讀者在閱讀中打上的一個個問號。曉蘇設置下這些問題,目的不是為了解答。他通過時間的力量、旁人的回憶、主人公自陳心路歷程等方法,將答案隱然而鮮明地浮凸出來。在這些“側寫”“旁觀”“追憶”等敘事路徑的背后,鋪展著作家柔軟的心性,以及面向浩渺人世、對人間事了然于心又不忍捅破點明的那一份寬仁,一種深刻的共情力。
《上個世紀的疙瘩》也承續了這種側面“解謎”的風格。通過少年在成長中的領悟逐一識破周遭的“謎語”,這是“成長敘事”最迷人的景致,就像巴赫金所說的那樣:“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由于少年所見到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因此故事便自動地攜帶著讓人驚奇的陌生化色彩;又由于少年愛思考,那些“怪事”的細節便被逐一拆開、放大和反復琢磨,得到了“厚描”式的呈現,并在少年的內心和生活中持續發酵。
小說的另一重魅力在于,它并未以“成熟”的洞悉了悟代替“成長”的費力思量。讀者跟隨著楊叉對萬物萬事均感好奇的目光,仿佛又經歷了一次不斷刷新經驗的成長,比如第一次與柏樹疙瘩正面相逢,少年的身體、感官、認知都在全方位地打開。可以說,小說所書寫的“謎語”是少年楊叉的人生第一次,也是人類經歷過的無數次。個人化體驗由此上升為普泛化的成長經驗,在“制謎”與“解謎”的敘事節奏里演繹著人性復雜的曲折轉圜,以及恒常而無盡的人生悲喜劇。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