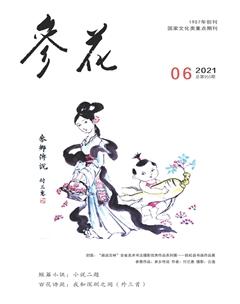從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荊棘鳥》中的女性
摘要:考琳·麥卡洛的《荊棘鳥》以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爾夫的愛情為主線,描述了克利里家族三代女性追求愛情和與命運抗爭的過程,女性從沉默屈服于命運到極端的斗爭,再到兩性的和諧發展,實現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荊棘鳥》 女性主義 解放
一、引言
《荊棘鳥》是澳大利亞女作家考琳·麥卡洛的代表作,講述了克利里家族三代女性不同的命運和情感經歷,女性在男權社會中不斷成長與解放,從沉默到覺醒再到成熟的艱難歷程,體現了女性提升自己的歷程。
二、女性解放之旅
“有一個傳說,說的是有那么一只鳥,它一生只唱一次……從離開巢窩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尋找著荊棘樹,……它把自己的身體扎進最長最尖的棘刺上,……放開了歌喉……這是一曲無比美好的歌,曲終而命竭……因為最美好的東西只能用深痛巨創來換取……”正如小說的開篇講述的傳奇故事,四位女性人物為了獲得真愛即使付出巨大的犧牲仍然執著地追尋著。
(一)菲奧娜·克利里奧娜·克利里
菲奧娜·克利里奧娜·克利里和瑪麗·卡森是小說中最早出現的兩位女性,雖處同一時代,但她們的性格卻截然不同,通過對二人的分析,揭示了她們所受壓迫和早期的覺醒。菲奧娜·克利里是克利里家族的第一個重要女性形象,她美麗、勤勞,受過良好的教育。菲奧娜·克利里出生在新西蘭一個傳統的父權制貴族家庭,父權意識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根深蒂固,女性只能作為“他者”或“從屬者”依附于男性。菲奧娜·克利里的出身注定她在那個時代和其他女性一樣,不能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她必須順從父輩為其選擇的門當戶對的婚姻。然而作為家中獨生女,菲奧娜·克利里并沒有遵循父親的安排,而是愛上了有婦之夫帕吉漢,菲奧娜·克利里的不幸從她愛上已婚男人那天開始,這種悲劇的根源實際上是父權制度對人性的壓迫,尤其對女性的壓迫。這段戀情顯然違反了傳統社會規范,為了維護家族的聲望和自己的愛人,未婚先孕被迫嫁給了貧窮低微的剪羊毛工帕迪。在男權社會,女性被禁錮在家庭中,扮演慈愛的母親、忠誠的妻子,服侍丈夫、照顧孩子、做家務是已婚女性的重要職責和義務,作為克利里家族的女性家長,菲奧娜·克利里毫無怨言地履行這些義務。對菲奧娜·克利里來說,真愛比任何“美德”都重要,這一舉動說明菲奧娜·克利里內心深處很想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菲奧娜·克利里的女性意識的雛形。然而菲奧娜·克利里的女性意識十分模糊和不完整,除了婚后的順從和沉默,她有限的女性意識表現在對命運的屈服,屈服于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社會規范,對婚姻中的父權壓迫她從未反抗,從菲奧娜·克利里的經歷可以看出她確實有過一種女性意識,曾經勇敢地追求過自己的真愛,試圖主宰自己的命運。
(二)瑪麗·卡森
與菲奧娜·克利里同時代的瑪麗·卡森則是小說中性格最鮮明的人物,她是帕迪的姐姐,出生在愛爾蘭一個貧苦家庭。瑪麗聰明、獨立、上進,她深知像她這樣的人命中注定要嫁給一個普通的丈夫,生育幾個孩子,一輩子做不完繁重的家務。瑪麗拒絕遵守社會規范,她有著改變自己命運的強烈意識,不遠千里來到澳大利亞,“憑著一張臉,一個身子和一個比人們認為女人應該有的更聰明的頭腦”迷住了新南威爾士最大的德羅海達莊園主邁克·卡森并深受寵愛。丈夫去世后,她立即成為澳大利亞內陸地區最富有的女人。她的勇氣、自信和智慧使她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和極高的社會地位,這些物質條件極大地幫助她改變了命運,使她成為自己的主人。瑪麗·卡森是男權社會里獨立奮斗的女性代表,作為獨立女性,她拒絕被其他任何男性控制,因此她沒有再婚,一旦再次成為某個人的妻子,她得將一切控制權交給那個人,再婚是她自由和獨立的障礙。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她是德羅海達至高無上的“女王”,這對于父權制度下的女性是無法想象的。在男權社會中,由于男女二元對立的主導意識形態,女性的性別角色通常限定在私人領域,在男性主導的文學傳統中,女性形象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惡魔”。賢淑、純潔、順從的傳統女性被視為完美的“天使”,顯然瑪麗并不是一個“天使”,而是一個令人討厭的“惡魔”,她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瑪麗·卡森扮演的角色在她那個時代只適合男性,作為德羅海達的統治者,她的工作完全超越了女性的領域,擁有了男性才有的權利和地位,雖過著寡居生活,但她從未放棄愛情。瑪麗的形象完全顛覆了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反映了女性開始積極爭取自由和獨立。
她對神父拉爾夫有著強烈的情感和愛,也從不掩飾自己的感情。當拉爾夫到達德羅海達時,她“毫無表情的眼睛突然變得靦腆而明亮,瑪麗·卡森幾乎在傻笑。”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即所謂的“他者”,是不允許主動追求男性的,女性追求男性是違背道德規范的行為,更不用說一個老婦人向年輕的神父求愛了。然而瑪麗·卡森徹底藐視傳統道德與禮教,從她愛上拉爾夫的那一刻起就迫不及待地表達她的愛意,“你是我見過的最迷人的男人”,這種愛甚至導致了她對梅吉的憎恨。作為女性,瑪麗積極勇敢地去愛,不管瑪麗追求愛情的方式是否正確,她在女性解放運動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她不屈于服男性權威,也不屈服于命運,她聰明獨立、不屈不撓,對生活和命運始終有著明確而積極的態度。在婚姻是女人命中注定的時候,她成功利用它為自己爭取了更好的生活。在事業上,她表現出非凡的能力,在愛情中,她讓男人成為她的欲望對象。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她的斗爭并不徹底,一方面她的想法充滿排他性,完全排除了男性和男性權利。女性主義者總是試圖建立一種和諧的兩性關系,讓男人和女人能夠平等愉悅地生活在一起。瑪麗過分強調女性的權利和地位,男性被置于相對的一面,成為壓迫女性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瑪麗所做的是對男性權利的復制和模仿。由于極端和局限性,瑪麗無法實現女性主義的最終目標,因此她不可能擁有幸福的生活。
(三)梅吉
梅吉是《荊棘鳥》中的女主人公,唯一渴望的就是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這種渴望完全符合“女性的完美”的傳統要求,是一個“完美的女性角色”,然而梅吉的一生從童年開始就充滿苦難,因為貧窮在學校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母親菲奧娜·克利里因為她是個女孩而忽略她。梅吉人生中經歷的第一個重大影響來自對神父拉爾夫的愛,梅吉九歲時和家人搬到澳大利亞,見到拉爾夫,她“張著嘴站在那里,張大了嘴看著他,好像在看上帝”。拉爾夫也立刻注意到了梅吉,梅吉漸漸對拉爾夫產生了愛慕。與此同時,拉爾夫也愛上了梅吉,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純潔的,但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愛情的失敗。瑪麗·卡森出于嫉妒和仇恨將所有的遺產一千三百萬英鎊留給了拉爾夫,以便教會能欣賞他。經過痛苦的掙扎,拉爾夫的野心戰勝了愛情,拉爾夫的宗教信仰犧牲了梅吉的幸福,拉爾夫離開了梅吉。梅吉自我意識還沒有被喚醒,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她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實現自己的家庭夢想,梅吉嫁給酷似拉爾夫的盧克。當梅吉看清盧克自私的真面目時,與盧克的不幸婚姻讓她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她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女兒賈絲婷出生后拉爾夫再次離開。梅吉不再是被命運困住的女性,而成為有著堅強意志和抗爭精神的獨立女性。在上帝那兒偷來的一個星期里,梅吉完全得到了拉爾夫的愛。梅吉懷上了拉爾夫的孩子,她認為懷孕是反抗的開始,梅吉離開盧克,結束了這段不幸婚姻,回到德羅海達,生下了兒子戴恩。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梅吉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自我意識已經覺醒,她終于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了,通過這種方式,她在與上帝和不公平的命運抗爭。
梅吉的轉變也表明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澳大利亞女性變得更加勇敢和成熟。兒子戴恩長大后立志成為神父,這對梅吉是巨大的打擊,她的斗爭并沒有完全成功。作為一個普通的女人,梅吉不能擺脫社會束縛,女性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賈絲婷
賈絲婷是克利里家族的第三代女性,出生和成長在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時期,受此影響,賈絲婷個性鮮明,一直努力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17歲時她決定去悉尼當演員,“除了舞臺我還能在什么地方放聲大笑、喊叫和大哭呢?”賈絲婷充滿了反叛精神,試圖打破女性在家庭中的束縛,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事業,對婚姻的態度更是充滿蔑視,“哭天抹淚,像叫花子似的度過我一生嗎?像某個連我的一半都不如,卻處處以為不錯的男人低眉俯首嗎?”賈絲婷對于女性貞潔的態度更是大膽,在男性主導的世界,女性的純潔被視為重要的美德之一,婚前失去貞潔會被家庭和社會拋棄。“我不打算把它留給婚姻”,她主動選擇“誰將獲得這個榮譽”的男人,而不是等待被選擇。她獨特的性格和獨立自主的行為表現了新時期女性在獨立方面的進步。然而到此她還沒有完成女性成長的任務。為了反抗男性的統治,她拒絕愛情和婚姻,這不是女性主義的理想目標,只有徹底消除男女之間的差異,女性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和成長,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幸運的是賈絲婷后來遇到了愛人雷納,在他的幫助下,她意識到幸福婚姻的重要性,以及與男性和諧關系的重要性。賈絲婷嫁給了雷納,婚姻并沒有阻礙她的自由和獨立,她可以繼續她的演藝事業。在克利里家三代女性中,賈絲婷是唯一最終獲得幸福的人,兩性和諧的實現最終證明了女性的真正成長。
《荊棘鳥》中女性成長的故事是澳大利亞女性追求平等和解放的縮影,女性從屈服于命運到極端的斗爭,再到兩性的和諧發展,就像“荊棘鳥把自己刺在最長最鋒利的脊梁上,卻依然唱著世界上最甜美的歌。”這是女性對幸福的強烈愿望,最終她們能夠追求真正的幸福,實現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
參考文獻:
[1]韓秀蓮.苦難的召喚——從女性自我意識角度解讀《荊棘鳥》的寓意[J].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5):25.
[2]方曉梅.覺醒與抗爭:解讀《荊棘鳥》中的女權主義思想[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2007(3):82-83.
[3]考琳·麥卡洛.荊棘鳥[M].曾胡,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申衛華,女,泰州機電高等職業技術學校,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英語翻譯)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