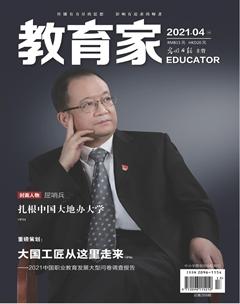深度挖掘知識,巧策提升素養(yǎng)
潘利峰
文言文承載了大量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也體現(xiàn)了漢語發(fā)展的軌跡,是現(xiàn)代漢語語義、語法的基礎(chǔ)。文言文是語文教學(xué)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現(xiàn)實(shí)情況是,文言文教學(xué)耗時多,收效少,已成為學(xué)生語文學(xué)習(xí)的一大難點(diǎn)。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文言文的難處在于不明語義、不懂語法、不解文化,教學(xué)的難點(diǎn)自然也與之密不可分。這其中語義是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正因?yàn)樗幕A(chǔ)性,以致長期被忽視,因?yàn)榛A(chǔ)性知識側(cè)重于識記和理解,而不明知識的內(nèi)涵和聯(lián)系,學(xué)生記憶也難,理解也難,考試運(yùn)用更是難上加難。
華中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郭元祥教授提出深度教學(xué)理念。他認(rèn)為,以教育學(xué)立場的知識觀和發(fā)展性的學(xué)習(xí)觀為基礎(chǔ)。注重發(fā)揮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動性,強(qiáng)調(diào)完整深刻地處理知識,增強(qiáng)學(xué)生知識學(xué)習(xí)的意義感、自我感和獲得感。“完整”即突出知識的聯(lián)系性,包括知識內(nèi)部、相鄰知識之間甚至跨領(lǐng)域知識之間的聯(lián)系,“深刻”表明知識是教育的載體,通過對知識的來源、內(nèi)涵等深入挖掘,提升學(xué)生的思維能力。在文言文語義知識體系教學(xué)中引入深度教學(xué)理念,能夠很好地為學(xué)生樂學(xué)、學(xué)好文言文打開一扇大門。
智設(shè)情境,深度激趣,提升體驗(yàn)感
文言文學(xué)習(xí)最大的問題就是真實(shí)語言情景的缺失,學(xué)生日常閱讀、交流、寫作基本不太可能使用文言文,整個大的社會環(huán)境也缺少文言文生存的土壤。在這種背景下,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文言文,積累文言字詞語義,心理上是抗拒的。盡管關(guān)于文言文教學(xué)激趣的研究并不少見,但幾乎沒有在語義探索上還原文言語境。
漢字是漢語語義的基本單位,而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基本特征實(shí)際上傳遞的是語義系統(tǒng),強(qiáng)調(diào)字形和語義的關(guān)聯(lián),探索其語義可以從字形入手。筆者曾經(jīng)在課堂上為給學(xué)生區(qū)別“從”“比”“北”三個字的基本意思,先告訴學(xué)生這三個字構(gòu)字部件都是兩個“人”,并且都是會意字,通過不同組合來表示各自意思,然后指定兩組(每組兩人)上講臺通過組合分別造出這三個字。通過演示,學(xué)生發(fā)現(xiàn),“從”是兩個人一前一后,所以其基本義是“跟隨、跟從”;“比”是兩個人并排,并排在一起,高矮胖瘦可立辨,所以其基本義有“并列、并排”和“比較”;“北”是兩個人背靠背,背向而行,越走越遠(yuǎn),所以它應(yīng)該是“背”的本字,其義有“背離”等。以對這三個漢字的意義探究,引導(dǎo)學(xué)生認(rèn)識漢字的造字邏輯,以此可以去分析更多的漢字,這不僅促進(jìn)了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與提升,而且增強(qiáng)了其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認(rèn)同。
真正的深度激趣一定要能夠激發(fā)學(xué)生的求知欲望,在老師精心創(chuàng)設(shè)的一個個學(xué)習(xí)情境中,以現(xiàn)有知識符號作為探索的起點(diǎn),積極參與知識解構(gòu)、意義重建,探索發(fā)掘?qū)W科知識的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學(xué)科思維能力,提升學(xué)科素養(yǎng)。
追根溯源,深度挖掘,激活意義感
將意義下沉,通過研究漢字的語義密碼,發(fā)掘漢字文化本身的魅力,激活學(xué)生學(xué)習(xí)過程的意義感,也不失為促進(jìn)文言文有效學(xué)習(xí)的途徑。
漢字的創(chuàng)造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就必然帶來漢字的發(fā)展滯后于語義的更新,也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一個漢字表達(dá)多個意思的現(xiàn)象,這種情況在以單語素構(gòu)詞為主的文言文中尤其常見。文言詞語絕大多數(shù)都是多義詞,這是導(dǎo)致文言語義教學(xué)難度大的根本性原因。但是,一個詞語盡管有多個含義,這些含義并不是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而是有一條聯(lián)系的紐帶,這條紐帶多數(shù)情況下是其造字之初所表示的最基本含義,稱之為本義。通過合理聯(lián)想,可以迅速積累甚至推導(dǎo)更多的含義。例如,在解析“牧”的含義時,甲骨文、篆書的形狀都是一個人手持鞭杖作驅(qū)牛之狀,《說文解字》解釋為:“牧,養(yǎng)牛人也。”這里解釋的就是其本義,在此基礎(chǔ)上自然引申出“放牧”這個動詞義項(xiàng);牧牛者,需要管理一群牛,這就又進(jìn)一步引申出“管理”“主管”“統(tǒng)治”的意思;一個地方的最高管理者可稱“牧”,這就是劉備任“豫州牧”中“牧”的意思;這樣一條意義發(fā)展的線索,也可以看出古代社會統(tǒng)治者的治理理念——將人當(dāng)成動物來管理。從本義入手,合理聯(lián)想,探索文言詞語意義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既可以方便記憶,也能夠幫助學(xué)生打開合理推斷的思路,閱讀過程中遇到不懂的字,自己也可以嘗試合理推斷。
在對文言詞語追根溯源的深度挖掘過程中,學(xué)生順循表意文字的造字技術(shù)和規(guī)則,深入探尋先民造字動因和心理,這樣就把漢字符號轉(zhuǎn)變成了意義系統(tǒng)。一個字表達(dá)哪一個基本含義、表達(dá)哪一些后起意思,都是有合理邏輯的。
連線結(jié)網(wǎng),深度聯(lián)想,培養(yǎng)自我感
語義的學(xué)習(xí)積累必須要形成知識網(wǎng)絡(luò),才能對文言文閱讀理解起到推進(jìn)作用。知識的網(wǎng)絡(luò)化過程必須由學(xué)生自己完成,教師的價值應(yīng)該體現(xiàn)在方法的指導(dǎo)和技能的傳授上,以及在必要的時候作一些知識的糾正。教學(xué)的終極目的是學(xué)生的成長,包括知識的獲得、能力的提升、素養(yǎng)的形成等學(xué)科學(xué)習(xí)方面,也包括審美的涵養(yǎng)、人格的養(yǎng)成等人的素養(yǎng)方面。
在語義知識連線結(jié)網(wǎng)的過程中,教師應(yīng)該尊重學(xué)生的個體差異,積極鼓勵學(xué)生利用他們熟悉和擅長的方式進(jìn)行組網(wǎng)。在日常教學(xué)過程中,比較常用的方式是讓學(xué)生畫語義演變的“進(jìn)化樹”,直觀明了,簡單易行,對于圖像思維發(fā)達(dá)的同學(xué)特別實(shí)用。以本義為主干,其他后起義項(xiàng)為枝干畫一棵語義發(fā)展的進(jìn)化樹,將其義項(xiàng)網(wǎng)絡(luò)化;有一定文言功底的同學(xué)也可以嘗試使用自創(chuàng)語段鏈接語義。
知識網(wǎng)絡(luò)的構(gòu)建不僅限于一詞多義,也可以運(yùn)用到有關(guān)聯(lián)的詞語之中,通過相同或不同的比較來構(gòu)建編織知識網(wǎng)絡(luò)。比較難辨的“即”和“既”,即便是在現(xiàn)代文背景下的使用中,學(xué)生也多有混淆,根本原因是學(xué)生基于本義的知識網(wǎng)絡(luò)沒有構(gòu)建起來。“即”和“既”甲骨文寫作的構(gòu)字部件也是一樣的,都是左邊一個“豆”(古代盛食物的器皿),右邊一個“人”,所不同的是“即”右邊的“人”彎腰靠近食物,而“既”右邊的人是張嘴打著飽嗝背對離開食物,“即,象人就食;既,象人食既”。“即”的意思多與“將食”這個原始義項(xiàng)有關(guān),如“將要”“靠近”“登上”等都是將食時伴隨或準(zhǔn)備的動作,就是現(xiàn)代漢語中 “即使”也是一個假設(shè)(或尚未存在)的條件;而“既”的義項(xiàng)也多與“食飽”這個原始義項(xiàng)有關(guān),如“完畢”“結(jié)束”“盡”“已經(jīng)”是食飽之后動作的延伸。現(xiàn)代漢語中“既然”也是一個已經(jīng)存在的條件。
需要注意的是,聯(lián)想一定是符合語義發(fā)展邏輯的合理聯(lián)想,其依據(jù)是文言文詞語造字賦義的基本規(guī)則,包括相似比喻、相容聯(lián)想、相關(guān)代用、相因推演。初學(xué)時可以引導(dǎo)學(xué)生在已知多個義項(xiàng)的前提下辨別本義,以及各個其他義項(xiàng)之間的引申關(guān)系,從而將所有義項(xiàng)有機(jī)聯(lián)系起來。
讀寫互滲,深度運(yùn)用,增強(qiáng)獲得感
嘗試引導(dǎo)學(xué)生進(jìn)行文言創(chuàng)作也是一條不錯的深度學(xué)習(xí)的途徑。寫作是各種知識的綜合運(yùn)用,需要學(xué)生以對文言語義的充分掌握為基礎(chǔ),還包括文言語法的基本習(xí)得,以及文言表達(dá)習(xí)慣的認(rèn)識和古代文化的一定了解。根本上,寫作是學(xué)生對古漢語文化綜合提升基礎(chǔ)上的語義表達(dá)。郭元祥教授認(rèn)為,具有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的課堂教學(xué)絕不是把知識僅作為一種事實(shí)或結(jié)論告訴或傳遞給學(xué)生,而是對具體知識作深入的文化分析,向?qū)W生表達(dá)出來或引導(dǎo)學(xué)生探究知識的文化屬性、文化思想、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維方式,體現(xiàn)出知識對學(xué)生的文化影響力,真正達(dá)成“轉(zhuǎn)識成智”“以文化人”的目的。
對于文言文寫作引導(dǎo)的內(nèi)容和主題要有選擇性。首選短小傳記,可以寫自傳,也可以為一位熟悉的古人立傳。原因有二:一是傳記比較簡單,格式相對固定,課本和課外閱讀中有大量可供借鑒的藍(lán)本;二是高考選文多為傳記,學(xué)生可以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運(yùn)用傳記中出現(xiàn)的一些高頻詞鞏固對語義的把握。
文言語義是文言文閱讀理解的基礎(chǔ),但基礎(chǔ)不等于淺顯,或者說任何知識,如果只視之為符號,那它本身自是沒有深度可言,特別是這些基礎(chǔ)性的知識。但深度教學(xué)理念告訴我們,知識只是教學(xué)的起點(diǎn),或者說是素材,決不能作為教學(xué)的終點(diǎn),否則學(xué)生素養(yǎng)的提升將難以實(shí)現(xiàn)。將書本知識轉(zhuǎn)換成學(xué)生的個體知識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傳授,要讓學(xué)生有一個沉浸式的習(xí)得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最終實(shí)現(xiàn)知識學(xué)習(xí)的充分廣度、知識學(xué)習(xí)的充分深度和知識學(xué)習(xí)的充分關(guān)聯(lián)度。
(本文系廣東省教育科學(xué)“十三五”規(guī)劃課題——“基于高中生核心素養(yǎng)提升的深度教學(xué)與課堂評價研究”,課題編號:2019ZQJK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