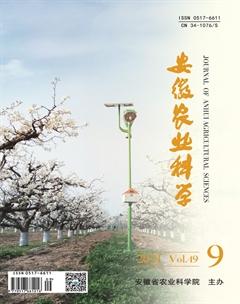中國農村扶貧歷程與2020年后反貧困趨勢及對策
王恒 朱玉春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經歷了救濟式扶貧、體制改革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參與式扶貧和精準扶貧階段,在實踐中逐漸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道路,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明顯減少,貧困發生率顯著下降。2020年后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基本消除,將由絕對收入貧困轉向農民工貧困、城市貧困、多維貧困和特殊群體貧困等相對貧困問題。回顧和梳理中國貧困特點、扶貧歷程和政策演變,分析中國新時期扶貧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有助于為2020年后新時期扶貧政策的制定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農村;反貧困;扶貧政策
中圖分類號?S-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21)09-024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09.065
Abstract?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founded,China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relief-type poverty alleviation,institutional reform-type poverty alleviation,development-type poverty alleviation,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ractice,it has gradually explored a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rural poor population was obvious cut down,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has dropped significantly. After 2020,absolute poverty of rural areas will be basically eliminated in China,and relative poverty will shift from absolute income poverty to migrant worker poverty,urban poverty,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poverty of special groups.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poverty alleviation history and policy evolution in China,and analyzing the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will help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after 2020.
Key words?Countryside;Anti-poverty;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1],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根據不同時期貧困的性質和特點,建立起貧困縣、貧困村和貧困戶的三級扶貧瞄準機制[2],在不斷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反貧困道路,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貧困發生率顯著下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精準扶貧工作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不斷改進扶貧思路和模式,2012—2019年,農村貧困人口從9 899萬下降到551萬,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0.6%[3],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20年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基本消除后,收入差距擴大、城市貧困、多維貧困、特殊群體貧困等相對貧困問題將日益嚴峻。如何實現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的有效銜接,從消除絕對貧困向建立減緩相對貧困的長效運行機制轉變,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基于此,筆者試圖回顧和總結中國農村扶貧歷程和政策演變,探析新時期中國貧困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以期為后脫貧時代扶貧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以及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反貧困提供中國經驗和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1?中國農村扶貧歷程及政策演變
1.1?救濟式扶貧階段(1949—1977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基礎薄弱,公共設施建設落后,自然災害頻繁,處于普遍貧困狀態,人民群眾面臨嚴重的生存溫飽問題。政府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救濟式扶貧策略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4],以“外部輸血式”扶貧策略為主。1952年,國家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土地分配,使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基本消除農民無地的狀態[5]。1956年底,國家在農村建立起人民公社化制度,對農村貧困群體和特殊群體等提供社會救濟、自然災害救濟和優撫安置等實物救濟[6],解決其溫飽問題,同時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業金融服務和推廣農業技術服務。通過救濟式扶貧,人民群眾溫飽問題得到有效緩解,為農村經濟發展和緩解貧困發揮了重要作用。197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1.7倍,未達到溫飽線的農村人口占比下降50%[7],城鄉居民收入明顯增加,城鄉居民生活顯著改善。
1.2?體制改革式扶貧階段(1978—1985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由于當時農業經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求,農民生產積極性較差,出現普遍性的農村貧困現象。按1978年貧困標準(100元),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有2.5億,分別占全國總人口和世界總貧困人口的26%和25%,貧困發生率為30.7%[8],我國實施了以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為主要目標的大規模體制改革式扶貧開發工作,扶貧政策主要是“輸血式”扶貧為主,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民收入大幅提高,極大緩解了當時農村嚴重的貧困現象,農民溫飽問題逐步得以解決。1983年,中央將甘肅定西、河西和寧夏西海固(“三西”地區)集中連片地區建設列入國家計劃,重點改善“三西”地區農業基礎設施條件,穩定解決貧困農戶的經濟來源和溫飽問題[6]。1984年,國務院提出要幫助我國“老、少、邊、窮”地區盡快改變貧困面貌,實施以工代賑,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有效提高貧困人口收入[5]。1978—1985年,我國農村經濟快速增長,生產力快速發展,農民年人均收入累計增加264元,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1.25億,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15.9%[9]。
1.3?大規模開發式扶貧階段(1986—1993年)
在改革開放背景下,中西部偏遠落后地區由于資源約束和地理位置偏遠,農村貧困形勢嚴峻,城鄉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明顯,各地區發展極不均衡。198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貧困地區經濟開發工作的通知》,提出1986—1993年扶貧開發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10]。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通過加大政策扶持,采取多種方式對18個連片特困地區進行幫扶[10]。通過大規模開發扶貧,農村貧困狀況顯著改善,農民收入穩步提高,1986—1993年,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6元增加到484元,農村貧困人口由12 500萬減少到8 000萬,貧困發生率從14.7%降低至8.7%[10]。
1.4?綜合開發式扶貧階段(1994—2000年)
隨著中國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國家扶貧開發的有序推進,貧困人口逐漸向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傾斜,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因病因災返貧率高[11]。為了盡快解決剩余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確定了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目標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基本解決農村8 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12]。通過扶貧到村到戶、定點幫扶和對口幫扶等扶貧機制,以開發式扶貧和參與式扶貧相結合,引導社會公共參與,注重激發貧困人口主動脫貧的積極性[13],實現“內外造血式”扶貧開發機制,扶貧取得顯著成效。1994—2000年,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8 000萬減少到3 209萬,貧困發生率由8.7%下降到3.4%,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基本解決[14]。2000年底,貧困地區通電、通路、通郵、通電話的行政村分別達到95.5%、89%、69%和67.7%[15]。
1.5?參與式扶貧階段(2001—2010年)
2001年,國務院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目標是到2010年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的落后狀況[16],確定14.8萬個扶持重點貧困村,以整村推進、產業扶貧和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扶貧方式為主[13],對貧困人口進行“造血式”扶貧,有效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建立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廢除農業稅費,使農民醫療有保障,減緩農業生產負擔[7]。按2008年貧困標準(1 196元),2001—201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9 422萬減少到2 688萬,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2.8%[17],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明顯改善。
1.6?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階段(2011—2020年)
2011年至今,扶貧開發工作進入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階段。2011年,國務院印發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確定了832個扶貧開發重點縣,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18],通過異地移民搬遷、整村推進、產業扶貧和革命老區建設等專項扶貧計劃對重點縣和貧困村進行精準扶貧。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建檔立卡和動態管理,注重“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精準扶貧工作機制。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做好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改善深度貧困地區發展條件,增強貧困農戶發展能力,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增強脫貧地區“多元造血”功能[19]。2011—2018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2 238萬減少到1 660萬,貧困發生率從12.7%下降到1.7%[20]。
2?中國農村反貧困成就和對世界意義
2.1?中國農村反貧困成就
2.1.1?農村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貧困發生率明顯下降。按1978年貧困標準,1978—2007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2.35億;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29.1%;按2010年貧困標準,1978-2018年,中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54億;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95.8%[20]。
2.1.2?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我國農村地區在道路、交通、飲水、通訊等物質生活方面顯著改善,居民生活條件顯著提升。2018年,農村居民住宅外道路為水泥或柏油路面、管道供水入戶、垃圾集中處理、飲用水集中凈化處理、使用衛生廁所的農戶比重分別為75.4%、79.7%、83.6%、65.3%和56.0%[21],貧困地區通電的自然村接近全覆蓋,通電話、通有線電視信號、通寬帶的自然村比重分別達到99.2%、88.1%和81.9%,農村居民食品消費和耐用品消費顯著增加,居住環境顯著改善[3]。
2.1.3?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面提升。貧困地區農村教育快速發展,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明顯提升;農村醫療設備和養老服務體系不斷改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使農村居民醫療花費顯著下降;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不斷完善,老年人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滿足;農村居民文化生活不斷豐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加強[21]。
2.1.4?農村居民收入顯著提升,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收入分配制度不斷完善,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升,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分別為39 251元和26 1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分別為14 617元和12 124元,城鄉居民收入明顯縮小[21]。
2.2?中國反貧困對世界的意義
消除貧困是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共同目標。按照2011年世界銀行標準(1.9美元/天/人),1981-2013年,世界貧困人口累計減少11.27億,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31.4%;中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8.53億,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86.4%,中國貧困人口占世界貧困人口總數從46.38%減少到3.28%,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累計超過70%[22]。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困人口減少最多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中國減貧經驗和實踐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截至2015年,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 0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向69個國家提供醫療援助,幫助120個發展中國家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23]。現階段,全球極端地區的反貧困任務形勢依然非常嚴峻,據統計,2015年全球無法獲得基本的衛生服務的人口有仍有23億,有8.92億人露天排便,婦女在懷孕或分娩期間死亡30.3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人數為590萬,面臨水資源短缺超過20億人,超過30億人口無法獲得清潔的烹飪燃料和技術[24]。2016年,全球仍有8.15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患有瘧疾的有2.16億人,五歲以下的兒童發育遲緩的有約1.55億[25],中國扶貧經驗可以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中國智慧和方案。
3?2020年后中國貧困變化趨勢
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顯著改善。1978—2018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4元增加到39 251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14 617元[26],城鎮居民家庭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21.3%和28.4%[20]。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及資源分配不均問題,農村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低收入群體在生活水平、社會福利和社會地位等方面處于明顯劣勢地位。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69倍,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3.2?農村貧困向城市貧困過渡
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城市反貧困的最主要方式,但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及消費水平等影響,城鎮最低生活保障處于較低水平。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農民工群體無法在城鎮均等享受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部分群體缺乏或喪失就業機會,低收入群體、失業人員和下崗工人等群體收入沒有保障,可能成為新的城市貧困群體。按絕對貧困線貧困標準(3.1美元/天/人),2015年我國農民工收入和消費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07%和12.3%[27],以相對貧困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一半)計算,農民工收入和消費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6.33%和65.61%,相對貧困線下的農民工貧困形勢更加嚴峻[28]。因此,城市貧困問題不容忽視。
3.3?深度貧困地區仍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
深度貧困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偏遠,自然災害多發,多數屬于限制開發區和環境保護區,教育、醫療、生活條件和社會保障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滯后,脫貧人口因病因災返貧或處于貧困線邊緣人口極易陷入貧困狀態。2016年底,“三州三區”貧困人口占全國貧困人口總量的8.2%,貧困發生率約16.7%,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7倍[29],有1.67萬個村貧困發生率超過20%,因病、因殘致貧人口分別占貧困總人口的42.3%和14.4%,65歲以上貧困人口占17.5%。因此,2020年后貧困時期深度貧困地區相對貧困形勢依然嚴峻。
3.4?收入貧困向多維貧困轉變
收入貧困視角下的貧困人口快速下降,現階段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有顯著提升,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壁壘,農村的教育質量、醫療資源、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等多維福利問題突出,與城鎮還有較大差距,因病、因學、因災致貧返貧現象時有發生。2017年,貧困地區使用安全住房、管道供水、衛生廁所和清潔能源的農戶比重分別為58.1%、69.6%、32.7%和35.1%,飲水有困難的農戶比重為10.8%[30]。2020年后我國農村地區的多維福利問題將是新時期反貧困面臨的嚴峻挑戰。
3.5?特殊群體的貧困問題將更加嚴重
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村留守人口主要為婦女、兒童和老人,“空巢老人”、“空心村”等現象有增無減,導致農村落后現象逐漸凸顯,老年貧困問題已經成為長期制約農村地區發展的現實問題。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17.8%,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31],2030年占比將達到25%,農村人口的總撫養比將達到94%,老年人口撫養比為63%[32],農村老年人貧困脆弱性增強,老年貧困形勢將更加嚴峻。由于離異、喪偶等原因,導致貧困女性化成為反貧困應關注的問題。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特殊的弱勢群體,尤其是西部貧困農村地區兒童的貧困現象明顯高于城鎮,農村將大量光棍也容易產生貧困問題,精神障礙和殘疾人等群體貧困現象將更加突出。
4?2020年后中國反貧困政策展望
4.1?扶貧政策向城市貧困過渡
2020年后,農民工、低收入群體和下崗工人等將是城市貧困的主要人群。應提升城鄉公共服務水平,針對不同貧困群體和致貧原因制定差異化的扶貧政策,統籌城鄉社會救助體系,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和就業服務體系,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和再教育,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消除城鄉相對貧困。
4.2?重點促進深度貧困地區的發展
2020年后實施反貧困政策時,應因地制宜,把鄉村振興戰略與精準扶貧政策相結合,增加對深度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大力發展特色優勢農業產業,通過產業扶貧帶動貧困人口脫貧致富,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脫貧能力,注重“造血式”扶貧。重點改善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注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4.3?提升貧困人口的多維福利
新時期扶貧政策應該重點在教育、醫療、生活條件和社會保障等多維福利方面對貧困地區進行傾斜。提升農村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促進城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降低學齡兒童失學率,阻斷貧困代際傳遞。開展勞動技能培訓和勞務輸出,增強貧困人口的就業技能和競爭力[33]。完善村級和鎮級醫療設備衛生服務設施,建立完善的疾病防御體系和醫療服務網絡體系。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加強推進“廁所革命”和安全飲水工程;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加強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加快推進移民搬遷工程和危房改造工程[33],全面提升貧困人口的多維福利和公共服務。
4.4?加大對特殊貧困群體的扶貧力度
新時期老弱病殘、婦女和兒童等特殊群體將是農村貧困的主要群體,健全老年人口社會救助體系,為部分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口提供特殊社會救助,同時關注老年人口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26],提升農村貧困人口的醫療保障受益水平。提高各項社會福利,使殘疾人和精神障礙者生活有所保障。對農村光棍、懶漢以精神扶貧為主,注重“扶智”與“扶志”相結合,激發其內生脫貧動力,提升其生存能力和生活信心[34]。設立農村公益性就業崗位,如農村清潔員、生態林管護員等,促進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完善與提升[26]。
5?結語
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扶貧成就雖然顯著,2020年后,我國反貧困重點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壁壘,提升城鄉一體化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戶多維福利水平,避免脫貧人口再次返貧和代際貧困發生,減緩老弱病殘等特殊群體貧困狀態,從關注衣食住行等顯性貧困到關注精神、能力和文化等隱性貧困過渡,實現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的有效銜接,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EB/OL].[2020-05-25].http://www.gov.cn/zhengce/2014-01/25/content_2640104.htm.
[2] 唐麗霞,羅江月,李小云.精準扶貧機制實施的政策和實踐困境[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51-156.
[3] (受權發布)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2020-03-06)[2020-05-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
[4] 周揚,郭遠智,劉彥隨.中國縣域貧困綜合測度及2020年后減貧瞄準[J].地理學報,2018,73(8):1478-1493.
[5] 黃承偉.中國扶貧開發道路研究:評述與展望[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3(5):5-17.
[6] 陳標平,胡傳明.建國60年中國農村反貧困模式演進與基本經驗[J].求實,2009(7):82-86.
[7] 邢中先,張平.中國扶貧70年: 基于實現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4):8-15.
[8] 劉娟.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回顧、成效與創新[J].探索,2009(4):87-90.
[9]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概要[EB/OL].(2006-11-19)[2020-05-25].http://www.gov.cn/zwhd/ft2/20061117/content_447141.htm.
[10] 程承坪,鄒迪.新中國70年扶貧歷程、特色、意義與挑戰[J].當代經濟管理,2019,41(9):1-9.
[11] 鄭長德.中國西部民族地區貧困問題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3(1):7-11.
[12]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EB/OL].(2016-07-14)[2020-05-25].http://www.cpad.gov.cn/art/2016/7/14/art_343_141.html.
[13] 王博,朱玉春.改革開放40年中國農村反貧困經驗總結——兼論精準扶貧的歷史必然性和長期性[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6):11-17.
[14] 趙慧珠.走出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的困境[J]. 文史哲,2007(4):161-168.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EB/OL].(2005-05-26)[2020-05-25].http://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293.htm.
[16] 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EB/OL].(2016-09-23)[2020-05-2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3/content_5111138.htm.
[17] 楊宜勇,吳香雪.中國扶貧問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J].中國人口科學,2016(5):2-12,126.
[18] 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EB/OL].[2020-05-25].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19]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EB/OL].[2020-05-25].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9/27/nw.D110000renmrb_20180927_1-01.htm.
[20]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8)[M].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21] 國家統計局.農村經濟持續發展 鄉村振興邁出大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三[EB/OL].(2019-08-07)[2020-05-2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7_1689636.html.
[22] 孫詠梅,秦蒙.高速經濟增長會自動消減貧困嗎?——新中國成立70年取得的減貧效果評價[J].教學與研究,2019(5):14-25.
[23] 國家統計局.扶貧開發持續強力推進 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五[EB/OL].(2019-08-12)[2020-05-2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12_1690526.html.
[24] 2017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EB/OL].[2020-05-25].https://m.huanqiu.com/r/MV8wXzEwOTk5MjY1XzEzNF8xNTAwMzg0MDAy.
[25] 聯合國. 2018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EB/OL].[2020-05-25].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progress-report/.
[26] 張永麗,徐臘梅.中國農村貧困性質的轉變及2020年后反貧困政策方向[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6(5):129-136.
[27] 陳志鋼,畢潔穎,吳國寶,等.中國扶貧現狀與演進以及2020年后的扶貧愿景和戰略重點[J].中國農村經濟,2019(1):2-16.
[28] 郭君平,譚清香,曲頌.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測量與分析:基于“收入—消費—多維”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18(9):94-109.
[29] 黃康生:加大力度推進“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EB/OL].(2017-08-29)[2020-05-25].http://www.rmzxb.com.cn/c/2017-08-29/1755433.shtml.
[30] 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8) [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31] 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的通知[EB/OL].[2020-05-2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06/content_5173930.Html.
[32] 孟向京,姜凱迪.城鎮化和鄉城轉移對未來中國城鄉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J].人口研究,2018,42(2):39-53.
[33] 王恒,王博,朱玉春.鄉村振興視閾下農戶多維貧困測度及扶貧策略[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4):131-141.
[34] 汪三貴,曾小溪.從區域扶貧開發到精準扶貧——改革開放40年中國扶貧政策的演進及脫貧攻堅的難點和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2018,39(8):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