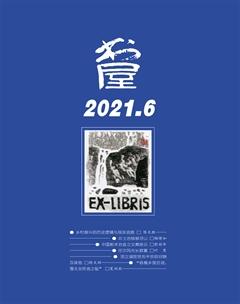任爾風光長寂寞
葉雋
在留德學生中德文化研究會這批人物中,金井羊(1891—1932)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存在,他字其眉,是江蘇寶山人,德國基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歸國后在政、學兩界都有任職,曾擔任政治大學、中國公學、交通大學、光華大學等教席,鐵道部參事與政務司司長等。無論是在思想見地還是事功行世方面,他都可算是卓爾不群的人物,可惜年及不惑即逝,實在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對他的生平經歷,友人有這樣言簡意賅的描述:“生而岐嶷,齠齡喜究物理,從同里前輩游,驚為偉器;學于縣小學,及上海民立、南洋兩中學,欿然不滿,課外探討攻苦至昏厥。君父春波先生,懼苦學傷其生也,乃資令東渡日本,使以游為息。君至日,專攻政治經濟,畢業于中央大學。初入學,見講義簡略,不滿其志,更沉潛于專門巨著,嘗以二月之力,畢英穆勒氏經濟學,俯讀仰思,欣然神會。當是時德為天下雄,學說稱最,君更入上智大學,習德文二年,造詣甚深。畢業返國,各校爭招延,君曰:我學未足以為人師,堅謝不就;杜門伏案,厲學不輟,四年如一日。嗣得請于春波先生,赴德入弗蘭克福大學,更轉基爾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可以得見少年金井羊的才華橫溢而好學深思,而他的學習成績也是顯而易見的,先留日后留德,符合那代人求知向學之路徑,蔡元培、馬君武的相關表述當皆為共鳴;由法蘭克福轉往基爾,則先與王光祈、宗白華等聚會而有發起“留德學生中德文化研究會”的事業,后則為陳銓之早期校友兼學長;至于治學思路,則與朱偰頗有不謀而合之處,即雖擅長文史,卻寧以經世之學如政治、經濟為專業。
留德時代,金井羊曾與俞頌華等交往。俞頌華自己也記錄下與金井羊等一起去聽泰戈爾訪德演講的情形。當時是1921年,他先是6月6日到法蘭克福,在金井羊處與宗白華相見。6月12日,俞頌華與金井羊、宗白華、王光祈、張夢九等一起去聽泰戈爾演講,他這樣記錄道:“臺(泰)氏是日所講的大意是說,歐戰之后,人心厭亂,所以各國提議解除武裝和互相聯合,創造國際聯盟,以防止未來的戰爭,這就是西方帝國主義不能再自由發展的明征了,但是設若根本的精神生活不變,而想望世界和平,則必失敗。因為西方以前的社會組織不啻為人類爭權攘利,損人利己的工具,所以組織愈擴大,組織力愈強,擾亂世界平和勢力亦愈加雄偉。這種基于‘力基于滿足淺薄狹隘的物質的欲望的組織不變,世界哪里能夠有和平之望。然則世界的和平是無望嗎?他說這也不然,只要擴張犧牲、博愛、自治、自由、自主種種寶貴的精神,使精神生活高尚的理想發展,把基于貪得無厭、損人利己本位的組織改變,而基于愛的組織,那時世界就有保持和平的可能了。”如此我們可以大致想見那代留德學人在此期的文化活動,就金井羊而言,他還是頗有興致積極參與的,當時這批朋友對泰戈爾訪德頗有期待與討論,將其視為東、西文化交通的標志之一,此處不贅。
1924年歸國后,金井羊曾在張君勱主持的自治學院任教,所以與張氏關系頗密,這其中與共享的留德背景或也不無關系。金井羊在滬上歷任多校,充任教授,社會地位較高,收入亦可,所以能雇傭家教。后來成為知名學者的錢仲聯回憶說:“我到上海后,曾在金井羊教授家中任家庭教師。”另外一件事也值得提及,羅隆基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后又為光華大學解聘,其間胡適為之奔走,曾拜托過金井羊,因其與陳布雷交好,可見金氏并非籍籍無名之輩。金井羊還頗通醫術,曾幫助廬隱之夫郭夢良治病:“會金井羊先生頗知醫理,見君(指郭夢良,筆者注)精神疲苶,舌苔極厚,因驚曰:‘此病勢非輕,非請醫調治不可。廬隱因懇其代請中醫診治。”后來又遷入上海寶隆醫院,請德醫診斷,雖不治而亡,但可以見出金井羊的醫道及其背后的德國背景。
1932年,當金井羊辭世之際,很多人撰文悼念。錢基博以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的名義草擬了《祭陳行救金井羊先生文》:“嗚呼行叔,魂兮歸來。瀛海濤涌,云馬既憒。亦有井羊,霜凋夏綠。容貌堂堂,身長立玉……”這或許多少還帶有校方色彩的表述,那么友人之譽則確實表現出其過人之處,相當不俗,譬如“近歲寡交游,然得心知一人焉,金君井羊是已。君粹于學,達于事,論學論政,麆麆有序,合于理而不戾于時;私意中國猶可為者,以君之學行才識,必受大任而有大成就。”期待不可謂不高。而且并非寰澄一人如此說法,胡善恒也稱:“人的一生,在有幾個道義的朋友,可以做學問物理上的商量,這種情感比任何經濟上的欲望,政治的熱心,家庭的安慰,尤為深切。近幾年來,去世的朋友很有幾人,而我心中的傷痛,實以井羊之死為最難堪。”胡善恒與金井羊經歷頗似,也是早年留學日本英倫,是拉斯基弟子,歸國后歷經政、學兩界,既為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等教授,也經歷仕途,曾任湖南省、廣東省財政廳長、行政院會計長等,都是經濟官員。更重要的是,“井羊之有許多朋友,個個朋友都以井羊之死為最傷心”,一個人能做到這點,是相當不易的。黃炎培(1878—1965)這副挽聯或許更能表現出金井羊的學養氣度和人格風襟:
如此世變,如此國難,天奈何奪此清才以去;
敬君學養,敬君器識,吾矢愿依君遺書而行。
這些朋友都非平常人物,而均能以如此高標評價金井羊,雖免不了逝后褒揚的成分,但仍非泛泛虛應之辭,由此可見其絕非池中之物。這樣的前賢人物,是值得后世追念的。金井羊與潘光旦是知交,兩人曾在政治大學、光華大學等同事,所以潘光旦專門撰文悼念,其中解釋說:“先生平日雅不欲以文字沽譽,故著述行世者不多見。”這可以見出金井羊雖為大學教授卻著述零落的原因,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作品,譬如以金其眉(King Gee-Mai)之名在基爾大學提交了博士論文《中國的貨幣制度》,據說還有《集資興國》、《黨政評議》兩書,但未能查到。更重要的,當然是潘光旦對金井羊思想的深刻認識:
先生思想大旨:頗能洞察玄學冥想之弊,而以孔門之人本主義為歸,故嘗曰:“法社會學者孔德氏謂儒家之學為合于理性之宗教,某以為今后茍得有志之士,能含英咀華發揮而光大之,則不難為世界和平立一新基礎也。惜國人說而不行,而西哲方吞云吐霧于所謂‘宇宙觀,與程、朱誤解格物之‘物字,可謂無獨有偶;而其真正根本問題,遂未由解決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其信然耶?”
這段話不但言簡意賅地揭示了金井羊之基本思想,而且顯示了他的博學、敏銳與洞見,一方面能通曉西方新學,譬如以孔德為代表的社會學乃是西方的新興學科,另一方面則更能打通中、西,即合于錢鍾書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通”之理。金井羊不但能閱讀孔德更能把握其思想的妙處,即其很有見地的判斷——儒學確實在基本路徑上通于理性路徑,與歐洲啟蒙思想的理性定位是相通的;而且儒學雖非宗教,但卻未必完全沒有宗教的面相,這也是日后韋伯將“儒教與道教”并列的原因。當然,從這段論述中可以看出金井羊的實踐品格,即更看重的是如何“起而行”,對西哲之沉于宇宙觀討論、國人之空言不行,都不以為然。但這可能也有其一定之誤區,因為哲人的職責本就在于“袖手談心性”,所謂的“哲學王”更多是一廂情愿而已,知識世界與現實世界是兩個不同的運行場域,各有其不同規則,像馬克思謂:“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但后來者秉承哲思而開辟實踐路徑,則確實應是為人類文明拓新道的不二法門,譬如孫中山強調“知行關系”就是一個例證。
潘光旦還提及了金井羊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先生哲學思想之見于文辭者尤難得,此為先生致侯城先生書中之最后數語,實為先生之絕筆,誠吉光片羽矣。書中于‘西哲二字下并附注曰:‘某以為不通自然科學與史學,而言哲學,是自欺欺人者也,故始終未加深究。其平居接人論學,虛懷若谷,大率類是。”這里涉及對知識整體與學科分割的關系,尤其是知識關聯性問題,確屬高見。其實凡學皆通,對于作為人類認知高端的哲學來說,尤其需要“博覽綜觀”,如此自然科學考究自然規律、歷史學理解人類文明,確實是不可或缺的知識支撐;當然文學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像德語文學這樣本就承載著極為重要的哲思功能的文本,更不應被放置在哲學之外考察。但總體來說,雖寥寥數語,已可見金井羊的知學深思,非常人可比也。這一點也得到胡善恒的印證:“他(指金井羊,筆者注)認為中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在現今決談不到實現何種理想上的烏托邦,所以他說‘欲將現在笨重而復雜的政治機械一肩挑去,實非易事,不細思,亂發言,烏乎可,這是一個意志與理智的問題,決非感情問題。井羊是富于理想的人,而且是情感動蕩人,沒有一天不是想把國家如何整理起來,但是他發現了在事實上有兩個絕大的障礙橫亙于前。”其一是“全國人民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其二是“道德的墮落”,且與前者互為因果。此處則表現出金井羊側重現實、關注起而行的面相,但又絕非空穴來風,而是與他的深層思考密切相關的、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場域,確實需要這樣的“明白人”去行動!所以,1929年,金井羊選擇棄學從政,到鐵道部任職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這“固然是受朋友的拖扯,實在也是他自己認為應當如此。最初他做鐵道經濟設計的事項,繼而任參事,繼而兼任債務委員會的委員長,繼而又任財務司長,一年之內,頻經遷職,正因為他之做事,是有原則,有理想,而又注意實際。有些朋友說井羊不應當做官,批評者自去批評,但是井羊以為對于國家服務,是國民應盡的職責,還可以從此中獲得實際的經驗,好卻除一般空疏的理想”。從金井羊的基本思路來看,挺身入局也是他起而行的一種選擇,所以也是順理成章;而且他也確實有治事能力,做出了一些頗見功效的“政績”,但其生病辭世則與其生性職業也恐非全無關系,所謂“先生體質素健,惟平居或勤自修,或為人慮事,或推論時局,精力虛耗亦多”,或也委婉點出其命門所在。如何惜身護體,對于精英人物來說也是一個永恒的命題。
沈恩孚是當時滬上名流,曾任同濟大學校長等職,其兩子沈有乾、沈有鼎分別是心理學、哲學學者,外甥潘光旦是社會學家。他悼詩稱:“正向淞波吊國殤,又悲志士欲沾裳!童季早識黃江夏,時政能傷賈雒陽。七葉家聲貂系貴,五常才調馬真良,秋風惆悵羅溪水,珍重楹書話故鄉。”以長輩前賢的身份作此評價,不可謂不高不重,“國殤”、“志士”均是鐘鼎之詞,可見潘光旦對金井羊的學養敬重并非空穴來風,既有自身認知的一面,恐怕也不乏時人包括前輩之共識。1933年5月,擔任中央大學兼任教授的俞大維,則捐款創設了“金井羊先生紀念獎學金”,以表達對金井羊的紀念深情,或可為金井羊的品格、友誼與貢獻略作注腳。
像金井羊這樣的人物,在中德關系史上恐怕未必在少數,他們未以大名顯,也未以著述彰,但卻絕非沒有意義。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很容易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甚至“大歷史中的沉默者”,這不是他們的損失,而是后來者自身的遺憾,因為我們忽略了本不該忘卻的可能精神資源。若非關注僑易群體而重新審視若干留德群體,進入到法蘭克福的“中德文化研究會”學人群,我恐怕也難得深度介入作為個體的金井羊,但打撈這樣的“無名”其實是研究者題中應有之意,不僅是為了前賢,也是為了后世與自身。金井羊雖英年早逝,但臨終淡定如常,留遺囑曰:“中國非有人焉能建立一新倫理學,則一切事業悉談不到。在心方面應取涅槃之樂與無入而不自得之精神,而將一切迷信一切非分之想完全破除;在行方面,則當抱定勤儉忠實四字。”這里我們可見出金井羊的胸襟見識都非凡響,其雖立定于起而行的事業,但絕不忽視坐而思的意義,尤其是對于新理論的學術建構方面,深抱期待,可見其作為一個教育家和學人的氣象;而對于倫理學的重視,尤其是“新倫理學”的概念提出,實在是有重要意義。他大概不會不知道留德前輩蔡元培所撰《中國倫理學史》以及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這種倫理學理論建構的思路應有其學脈線索,但將其視為中國未來事業之樞紐,自非明斷敏銳之眼光通識不能為,故不可不有以思之。
金井羊因其留德背景,所以自然對德意志有特殊感情,故他與德國的關系也值得記上一筆。“十九年,德國工業協會應我國政府請,遣實業團來華考察,周歷粵、蘇、浙、鄂各大埠,北行至平、津及于關外。當道使君款禮團員,口講指畫,昕夜編纂中、外文書,備極況瘁。德人極推重君,非君語不信。返國后,立華事研究會,為中德合作基礎”。此處可以見出金井羊是很善于實務運作的,在和德方的交往中不僅能長袖善舞、折沖樽俎,而且能獲得德方信任如此,真可謂是經濟外交的好手。當然,金井羊并非為事務而做事務的職業官僚,他是有著背后的深意的,“君嘗謂中國經濟落后,非盡量用外資借技術以辟利源,不能圖存。德自歐戰后,與我訂平等條約,尤有利無損。故極注重實業團事,勞瘁不辭”。
俞鳳韶早年隨張靜江赴法經營實業,當過通運公司與通義銀行的經理,后又歷任民國時代滬上之政經要職,所以是一個有國際眼光的人,他認為:“君(指金井羊,筆者注)學有本原,博而能通,受董尼士及馬克韋勃爾影響最深。與人言,淵溢泉涌,絕無拘沫、墨守之習,亦從不作浮光掠影之語。”這里揭示的學術資源值得關注,應為德國學術上的兩位社會學大家即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與韋伯(Max Weber),這也可以理解,因金井羊留德之際所學即為經濟學,這些學者的著作很可能就是他的學業必修課。但既入德邦,不可能不受到其大哲巨擘之精神影響,譬如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居謂德意志民族的菲斯脫領導思想為勃興運動之原,乃慨然于國之作者。君愛國至摯,非無心于著述,惜授學從政,不遑有作,天又不假以年,使君為中國之菲斯脫也”,可見金井羊不僅對費希特心有敬重,而且也存效仿之意,這樣一種勾連東西方文化,也跨越政治、經濟、文化邊際的“心理相通”其實是很值得揣摩回味的文明史現象,所謂“十年報國心肝,溘然竟棄人間世。風凄雨苦,蕭條四壁,惟余圖史。耗矣神州,哀哉吾黨,罷聞博議。痛遺書半篋,燒燈檢點,空飄墜,人情淚”。真是極為形象地描繪出一代英杰的凄涼悲劇,他們的報國心志,他們的挺身入世,他們的憂思長默,雖然談不上是金戈鐵馬、轟轟烈烈,但同樣也是可歌可泣、值得緬懷!走筆至此,涌到心頭的竟是這樣一句:“任爾風光長寂寞!”相對于那些未必深刻卻能贏得俗世聲名的人物,金井羊的哲思深沉其實意味深長,他的寂寞甚至匿聲正說明了我們研究者的淺薄與短見。而像這樣的現代留德學人或許未必就在少數,他們就如同藏在沙下的金子值得去深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