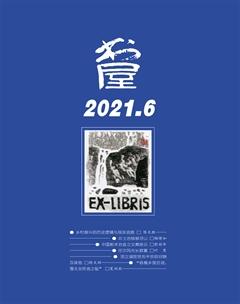看《東普魯士日記》,尋作者的故鄉
程丹梅
2018年的夏天,我決定去原東普魯士現為波蘭版圖上的著名的地區瑪蘇潤Masuren度假。
我之所以選擇那里,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由于一本書,一本很薄很薄的書。但在我看它時,我卻明明感到了它的厚重。
這本書已經發黃了,似乎有過再版,但我手里的則是1967年4月的第一版,書名叫《東普魯士日記——一個醫生的1945—1947》,作者是一個叫漢斯·格拉芙·馮·萊恩道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的人,他是一名醫學專業的外科醫生,于1941年底在東普魯士的因斯特堡地區醫院擔任助理醫生。萊恩多夫沒有被選入國防軍,因為他在醫院不可或缺。他的那本書講述的是1944年至1945年夏天發生在當時屬于德國的東普魯士一些地區的事情。
它的開頭是這樣的:戰爭之前我的東普魯士故鄉還是很美的。“無法想象,發生了什么,沒有人敢把可怕的猜測說出來。但是,在夏天過去鸛鳥們準備飛走前,它們知道等待它們的是什么,也不保守它們的秘密。在村子里到處有人站在那里向天上觀望,看大鳥們自信地繞著圈飛,這應該是走前告別的儀式。每個人都在這個光景里有著同樣的感受:是的,你們現在飛了,我們呢?我們和這個國家將會怎么樣?”這個開頭似乎注定了一個未知的命運。
隨后,天空有飛機轟炸著,人們運珍貴的東西,貨運車站難民長龍,頃刻間,一連串炸響,田間里馬死了,冒著熱氣,一個賓館炸成了如紙做的道具……港口有輪船運難民,擠滿了人等候離開。萊恩道夫目睹了為國王堡(Konigsberg)進行的戰斗以及這座城市被占領的經歷:“我看到了那個叫國王堡的城市是如何成了一片片廢墟,以及等待逃難的火車是怎樣載著長龍般的難民離開,而當地人不得不扔下的各種祖傳家什逃走的情形。接著,俄國的坦克進入了國王堡這一帶,一些還是孩子的十六歲甚至十四歲的孩子就去當兵抵抗去了,他們還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每天都有受傷的人,裸露的身體流著血,大街上也常見死尸,戰地醫院里手術不斷……一些不想逃難或不想分離的親人就紛紛服毒自殺……”
描述人們服毒的情節與段落很刺人心:一位實習醫生的父母不可想象三十年的幸福夫妻要分開。一天,等實習醫生再去看父母時,發現二人已經死在床上。就在實習醫生沉默禱告之后準備出門時,卻被門外的一個女人絆倒,只聽那女人呼喊著對他說:快救救他吧!她的丈夫把煤氣閥門打開了。
醫院遭到炮彈,院長被炸死,醫院的傷員不斷增加。有坦克隆隆駛過來,軍隊女指揮官下命離開該地區,護士長問可否違反命令不離開?一個個被救護車運來的傷員躺在地板上,太多了,救不過來。憐憫和同情已經不足以表達什么了。大街上人們壘起磚瓦和用逃跑了人的汽車來當阻擋物。
我記憶很深的還有一段:一個老婦人抬著祖傳的矮柜在大街上希望誰能幫她運往火車站。或者你買了它也行,她這么說著。也有扔在大街中央的老鋼琴,誰還顧得了那么多呢?
“數月來,大炮和低空飛機轟炸了這座被封鎖和摧毀的城市之后”,萊恩道夫在醫院、掩體和地窖中照顧受傷的人、患病的人和即將分娩的婦女,并給病人讀經。即使在國王堡被征服之后,他仍沒逃離這座城市,這也是出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在1945年4月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這是什么,我問自己,我們在這里正在經歷什么?這仍然與自然的野蠻或復仇有關嗎?也許與復仇有關,但又有不同之處……這些人,像我們一樣,來自何處呢……,與特定民族或種族無關……”萊恩道夫道出了一個事實:戰爭的受難者永遠是無辜的老百姓。
戰爭使數日之前還是自己家鄉的地方變成了陌生人的占領地,大批德國人成為難民被驅趕。東普魯士的冬天寒冷至零下二十六攝氏度,逃難的人半途死傷無數。據統計,二戰中被驅趕而成為背井離鄉的德國難民大約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四百萬,其中兩百萬人在逃難和被驅逐的途中死去。
萊恩道夫最后不得不與國王堡的德國人一起作為難民被驅逐到另外的拘留營,并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繼續他的醫療工作,忍受該城市遭受饑餓、流行病和大規模的死亡。后來,他費盡氣力地穿越馬路與野地到達了東普魯士西部和西普魯士的交界地,那是他兒時訪問祖父母常去的地方,他在殘酷的條件下非法生活在剩余的德國難民、波蘭人以及占領軍之間。1947年,他踏上了前往德國之路。
萊恩道夫這個姓氏在德國很有聲望,不僅因其為貴族,也是因為這個家族的遭遇和反納粹的歷史。1944年,萊恩道夫的母親因站在一位正直的牧師朋友一邊而被納粹逮捕,后來在1945年她和長子向西逃亡時遭到紅軍士兵的槍擊。萊恩多夫的表弟海因里希·格拉夫·馮·萊恩道夫-施泰諾特是一位抵抗戰士,他在參與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希特勒行動失敗后被吊死。
這么具體地看一份二戰前后東普魯士和人物的記錄,我還是第一次。關于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從任何一本教科書上找到,但那卻是大輪廓的,似乎個人歷史在這里微乎其微。所以,當我踏上原東普魯士的瑪蘇潤的土地上時,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感受的時候到了。
自一踏上瑪蘇潤這個地區,我就發現萊恩道夫日記中的地名早已換了波蘭名稱和語言了。偶爾的城鎮里,依然能看到不少雕刻德文字母的教堂以及典型德國風格的房屋,甚至在一片湖區,還留有德國人建的吊橋,至今依然以手動與機械結合的操作方式讓行人和車輛經過。我不知這些地點是否萊恩道夫都走過,我也不知他從占領軍某駐地逃出來時經過的小鎮或叢林今在何方。
但是,我卻還是找到了萊恩道夫家族的老莊園,那個原德文Steinort今波蘭語Sztynort的地方,莊園中央有一個正在修繕的黃墻紅頂的宮殿。從橫向綿長的建筑規模和風格上,依稀看得出早年這里主人的身份與地位以及富庶的程度。有資料顯示,這個宮殿自1420年就屬于萊恩道夫家族,據說在1941到1944年間,宮殿的一半曾被當時的德國外長馮·利伯特勞普占用過。宮殿最后一個擁有者就是那位抗擊希特勒的英雄萊恩多夫的表弟海因里希·格拉夫·馮·萊恩道夫。
我站在那里,看目下的這個宮殿,它可以說很破敗,墻皮也剝落了不少,裸露出里面的紅磚赫然醒目;所有的窗子都沒有玻璃,也幾乎都被一塊塊塑料布遮蓋著,或者用木板釘著;醒目的建筑中間部分并列著如教堂一樣上呈半圓的三個窗子,它們的角型外框,已經不見原色。這時,我看到了停在建筑前面的一輛橘紅與灰色相間的工地車,車后箱上伸將出來一根銹跡斑斑的鐵梁……我曾在一篇關于宮殿的材料中讀到過這樣的記錄:自1945年以來,紅軍長期占領該宮殿。1950年間,在宮殿中還成立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包括經濟部門在內的整個設施曾由某個奧地利人掌握,然后在1995年又交給了華沙游艇經營者。這座殘舊建筑物的最大寶藏是中間部分的彩繪和雕刻,以及巴洛克式木制天花板。最近的資料顯示,2009年11月,“波蘭-德國文化保護和紀念碑保護基金會”收購了這座宮殿。當然,還有一個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這便是:2009年6月22日,在海因里希·格拉夫·馮·萊恩道夫一百周年誕辰的時候,曾有一個紀念碑在這里落成,而紀念碑的奠基儀式就是在這座宮殿里舉行的。
我很幸運地找到了紀念碑,它就在宮殿的旁邊的一片樹蔭下。紀念碑由一塊完整碩大的橢圓形石頭與一片正方形刻字的黑色大理石組成。刻出的字是波、德雙語,上面寫道:以此紀念海因里希·格拉夫·馮·萊恩道夫(1909—1944),Steinort宮殿最后的主人和7月20日抵抗希特勒納粹運動的戰士一百周年誕辰。
紀念碑前面有一塊用小方磚壘出的地方上,擺有一個棕色的陶瓷罐子,里面插著當時田野里正盛開的花——白色的野菊,黃色的滿天星,紫色的串花和藍色的騎士頭盔,配有綠色的松枝,顯然這里有人照管或者常有人來敬拜。另外,有一個不銹鋼花瓶里面是人工花束,這在波蘭的很多墓地常能看到,花色很耀眼,有淺藍的蝴蝶蘭,有橘紅和白色的喇叭花,還有藕荷色的叫不出名稱的。靠近紀念碑底座處還有一個紅玻璃罩的燈籠形蠟燭燈,估計有人在此點亮過。不過,即便不劃火柴,在陽光的照射下,那個燈籠狀的通體紅色也很亮,很醒目,就像是一個和平的火炬。
我站在那里靜默了數分鐘,還將附近草坪上采摘的小小奶油花放在了紀念碑前。我知道我那嫩黃的奶油花過不到幾分鐘就會打蔫、枯萎,但是我對英雄的敬意已經表達。我同時還意識到,我原本為尋找《東普魯士日記》作者萊恩道夫蹤跡而來的目的不僅達到了,而且我還認識了他家族中的一位烈士,這是意外收獲,這讓我更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