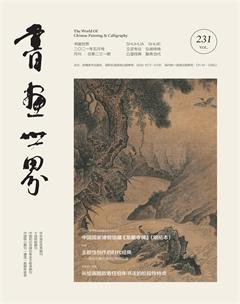淺探五體兼擅
賀雨萱
關鍵詞:書法;五體
學書者能否五體兼擅呢?首先需要明確筆者在此所討論的“兼擅”特指五體皆為書法史中的第一流水平,而非只是達到略優于同時期書家的程度。張懷瓘在《書斷》中評價王羲之:“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助。”然而,王羲之并無篆隸作品流傳下來,以證明他在此兩種書體領域也是歷史上最具創造力的大家。事實上,可以說幾乎找不到五體皆為第一流的書家。那么這是為何呢?
我們先討論如何能成為歷史上第一流的書家,無論其兼擅幾體。“吾書比之鐘、張:鐘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1]65王羲之認為,張芝的草書水平在他之上,原因是張芝的技藝更加精熟。由此可以看出,書圣心中的第一流書家需要技術精熟。“至如鐘繇隸奇,張芝草圣,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1]75孫過庭在《書譜》中也表示,鐘繇與張芝因為專精一體,所以才能夠達到無與倫比的境界。為何精熟是創作一流作品的重要條件呢?“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茍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諳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1]84孫過庭認為,只有技術精熟,才能夠做到“意先筆后”,自然從容。通過大量的心手訓練,書者心手配合自如,以至于玄妙契合,創作時“無間心手,忘懷楷則”[1]89。這里存在一點看似矛盾之處:既然通過大量訓練達到技藝精熟,從而能夠做到“意先筆后”,為何又說創作時“無間心手,忘懷楷則”呢?筆者認為:所謂“意先筆后”,指書者運筆純熟,在創作時能夠通過運筆實現其創作構想。就好像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必定要具備超強的駕馭語言的能力,才能以語言為工具,勾勒出符合自己想象的那樣一個世界。“意先筆后”就是指書家通過精熟的技術,逐漸實現創作構想的過程。這個“意”即創作構想,是作品整體的理念。而“無間心手,忘懷楷則”中的“楷則”是書寫的法則,指書者在正式創作中要忘卻范式,不被法式束縛。精熟的技藝在日常訓練中早已成為書家的下意識,是一種應激反應。唯其如此,下筆才能“瀟灑流落,翰逸神飛”。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何為“精熟”。“精熟”是一種經過長期積累而形成的下意識反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鐘、張之余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1]69孫過庭為達到技藝精熟,二十多年堅持訓練。眾所周知,書寫過程本身是一種手部運動,要達到書法技藝熟練,就要經過大量的訓練,從而形成手部肌肉記憶,產生一種類似運動員經過訓練后形成的肌肉應激反應。“在許多運動實踐中,……所有這一切并非完全由大腦來進行控制,因為我們做動作時有空白—無思索階段,若加入過多的大腦指揮,動作反而失常。很多動作是在動作‘慣性的作用下完成的,這個‘慣性就是‘肌肉記憶。”[2]61這里所說的“無思索階段”可以用來解釋前文所提到的“無間心手”狀態。“一個動作的掌握是不斷練習的結果。至于能夠記住一個動作,就是肌肉收縮程序的動力定型,……并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被固定下來。有過運動經歷的人都有體會,一些已掌握的動作,如果放慢速度、減緩用力來做,結果是變形甚至遺忘。……假如按照學習和練習該動作時的速度、力量進行前后動作的練習,會很容易地將所遺忘的動作連貫出來。這是儲存在肌肉中的肌收縮過程程序化的模式在特定的條件下被喚醒之故。”[2]62在創作時,只有在這種最舒適的狀態下,書家才能表現得優異,不然就會用筆猶疑、滯澀,無法做到“瀟灑流落,翰逸神飛”。那么這個關鍵的“下意識動作”是單一化的還是多樣化的呢?這個問題決定了書家是否可以五體兼擅。因為我們知道,五種書體的手部運動方式是不一樣的,盡管行書、草書非常接近,可我們只須以篆書為例,便可得出五體運動方式不同的結論。筆者認為,“下意識動作”必定是單一的,因為如果是多樣化的,那么也就不能夠稱其為“下意識”。因為“下意識”意味著不假思索,而多樣化意味著必須進行選擇,選擇意味著要經過思考,哪怕只是瞬間的思考,也表明并非“下意識”。經過以上推理,我們可以得出書家有且只有一種最舒適的“下意識”書寫動作,也即用筆方式。而書家只有在這種最舒適的狀態中,才可能“心手雙暢”,創作出書法史上一流的作品。假設一個書家同時存在兩種“下意識”手部動作,下筆的一瞬間,兩套“下意識”爭勝,無異于左右手互搏,近乎走火入魔。因而,“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真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1]174姜夔在《續書譜》中也表達出歐陽修、顏真卿以楷書筆法表現草書,李邕、李建中以行書筆法表現楷書。筆者認為,正是因為書家只能用自己最適應、最熟悉的下意識動作進行創作,所以不能五體兼美。正如歐陽修在創作其風格強烈、彪炳千古的楷書時,只適用一種下意識手部動作,當他創作草書時,無法擺脫這種動作慣性,而這種動作對創作草書來說并不是最優選擇,并不是一種“心手雙暢”的“下意識”,因此就無法創作出書法史上最優秀的草書作品。
然而,“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1]75書家依然可以通過學習諸體,吸收精華,熔鑄一爐,在一種書體中展現出五體的風貌,也不失為一種兼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