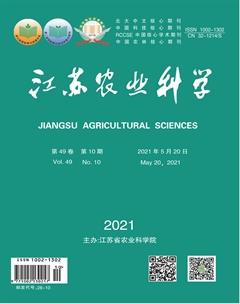丘陵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反思
熊熙 張仕超 文可可 劉競宇

摘要: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因國家及區(qū)域政策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不同而異,面臨著合作博弈風(fēng)險,它較傳統(tǒng)農(nóng)戶在土地、人力、資本、技術(shù)、信息、金融、社會等資源要素方面更具優(yōu)勢,使其成為丘陵山區(qū)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核心載體。從國家戰(zhàn)略和區(qū)域發(fā)展需求2個方面闡明借力多元主體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時代要求。在此基礎(chǔ)上,揭示了新時代下多元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確定的多維困惑,進(jìn)而對丘陵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的確定進(jìn)行思考與展望。結(jié)果表明,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發(fā)展是實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的國家戰(zhàn)略要求,也是促進(jìn)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產(chǎn)業(yè)扶貧的關(guān)鍵,同時還是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特征所要求,更是由丘陵山區(qū)地域特色及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所決定的。新時代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與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二者不可分割,新型主體須找準(zhǔn)合適的“度”,“度”應(yīng)兼顧主體培育的產(chǎn)業(yè)階段性、要素資源的異質(zhì)性和經(jīng)營類型的差異性。丘陵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解析與重構(gòu)須兼顧3個方面:首先,不同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以引領(lǐng)什么類型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為重點,如何基于要素差異性、功能互補(bǔ)性、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性,處理大小業(yè)主、先進(jìn)后進(jìn)業(yè)主、本地與外來業(yè)主等經(jīng)營主體間的關(guān)系,規(guī)避主體培育中的合作競爭風(fēng)險?其次,針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目標(biāo)轉(zhuǎn)變,丘陵山區(qū)土地生產(chǎn)力水平約束、經(jīng)營主體資源稟賦差異,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演化和產(chǎn)業(yè)類型規(guī)模需求差異,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度”如何把握?最后,實現(xiàn)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路徑是多種形式的,不同階段、尺度、資源稟賦、生產(chǎn)經(jīng)營性質(zhì)、種養(yǎng)品種等所對應(yīng)的最優(yōu)實現(xiàn)路徑應(yīng)有所不同。
關(guān)鍵詞: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鄉(xiāng)村振興;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
中圖分類號: F327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1)10-0006-08
農(nóng)業(yè)乃民生之根本,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背景下,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受到嚴(yán)重威脅,“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是亟需解決的問題,也是推進(jìn)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面臨的現(xiàn)實障礙。新型經(jīng)營主體是新時代引領(lǐng)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突擊隊、著力點,發(fā)展多樣化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更是增加新型農(nóng)民收入、提高農(nóng)業(yè)效益的重要途徑。在多年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政府工作報告等政策文件中多次指出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從國家層面上不斷推進(jìn)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作為世界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基本趨勢[1],國內(nèi)外諸多學(xué)者從構(gòu)建適宜性評價指標(biāo)體系、適度規(guī)模測算、規(guī)模效益評價、驅(qū)動因素分析、規(guī)模經(jīng)營意愿和模式,以及土地流轉(zhuǎn)、生產(chǎn)投入、鄉(xiāng)村勞動力流出對規(guī)模經(jīng)營有何作用等方面展開研究,但針對“度”的問題仍存在許多疑惑和爭論。在我國,丘陵山區(qū)地理條件“先天不足”,相較平原地區(qū)而言,新型農(nóng)業(yè)體系建設(shè)較緩慢、實現(xiàn)規(guī)模效益難度更大。因此,在大力推進(jìn)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和鄉(xiāng)村振興的關(guān)鍵時期,因地制宜引導(dǎo)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發(fā)展格外重要。厘清國家戰(zhàn)略和區(qū)域發(fā)展對多元主體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時代要求,揭示新時代下多元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確定的多維困惑,進(jìn)而對丘陵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的確定進(jìn)行思考與展望,對推進(jìn)丘陵山區(qū)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鄉(xiāng)村全面振興更是具有重要意義。
1 借力多元主體發(fā)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時代要求1.1 既是新時代下踐行鄉(xiāng)村振興的國家戰(zhàn)略要求,也是加快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產(chǎn)業(yè)扶貧的重要抓手
2018年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指出大力發(fā)展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提倡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這是將小農(nóng)戶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關(guān)鍵所在。在此背景下,農(nóng)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進(jìn)一步鞏固完善,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再次提及。同年召開的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議強(qiáng)調(diào)對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等新型經(jīng)營主體加強(qiáng)培育的重要性,將其視為未來扎實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的具體任務(wù),因為這2種經(jīng)營主體與小農(nóng)戶的利益關(guān)系最密切,只有以新型經(jīng)營主體為載體,才能使小農(nóng)戶逐步邁進(jìn)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大格局。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與之相銜接,培育家庭農(nóng)場計劃啟動,著重培育家庭農(nóng)場、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繼續(xù)推進(jìn)農(nóng)業(yè)示范合作社,進(jìn)一步培育產(chǎn)業(yè)化農(nóng)業(yè)企業(yè)及聯(lián)合體,大力建設(sh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園。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及新型經(jīng)營主體應(yīng)作為重點培育對象,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聯(lián)合體同樣應(yīng)重點培育。
為了借力多元主體發(fā)展多樣化的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中央對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如何培育、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應(yīng)如何發(fā)展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自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政府工作報告(十八大、十九大)、中央一號文件(2009、2010、2012、2013、2014、2016、2018、2019、2020年)、《農(nóng)業(yè)綜合開發(fā)推進(jìn)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指導(dǎo)意見》等相關(guān)政策文件、“十三五”規(guī)劃、《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2018—2022年)》中多次提及構(gòu)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相關(guān)政策體系,以融合多元化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多樣化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指出破解“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和“規(guī)模效益”等問題須依托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將其視為踐行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推動者,引領(lǐng)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突擊隊,解決產(chǎn)業(yè)扶貧的著力點,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重要力量。近年來,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在政策大禮包的支持與引導(dǎo)下迅速增長。據(jù)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統(tǒng)計,截至2018年,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農(nóng)業(yè)服務(wù)性組織分別有217.3萬家、近60萬戶、超300萬個。每家(戶)農(nóng)業(yè)企業(yè)、家庭農(nóng)場、專業(yè)大戶經(jīng)營耕地面積平均分別為52.21、11.82、6.81 hm2,而普通農(nóng)戶每戶只有0.50 hm2,全國超過27%的耕地由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不含合作社)經(jīng)營,可見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土地規(guī)模比普通農(nóng)戶更大,且各主體間平均經(jīng)營耕地規(guī)模差異顯著。同時,該報告還顯示在大市場和國際化背景下土地經(jīng)營模式的小規(guī)模、分散化已無法完全符合,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規(guī)模化經(jīng)營水平亟須提高(圖1)。
同時,各級部門共抓落實行動,積極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強(qiáng)調(diào)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重要性。2016年汪洋副總理指出,現(xiàn)代化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領(lǐng)跑者是規(guī)模化經(jīng)營的新型農(nóng)業(yè),應(yīng)加強(qiáng)政策扶持力度,積極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尤其是隨著2016年深入推進(jìn)農(nóng)村土地“三權(quán)分置”,指引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流轉(zhuǎn),大力發(fā)展規(guī)模化經(jīng)營的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并呈現(xiàn)多種形式,這成為面對“新常態(tài)”經(jīng)濟(jì)下強(qiáng)化農(nóng)業(yè)基礎(chǔ)地位、助力農(nóng)民增收、保障國家糧食和農(nóng)產(chǎn)品安全等現(xiàn)實問題的共同愿景。2017年經(jīng)國務(wù)院常務(wù)會議審議,提出鄉(xiāng)村振興的關(guān)鍵是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多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結(jié)合發(fā)展、加快推進(jìn)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原農(nóng)業(yè)部提出通過新型經(jīng)營主體培育工程、支持其參與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支持其對農(nóng)產(chǎn)品進(jìn)行初加工和發(fā)展具有生產(chǎn)特性的服務(wù)業(yè)、開展農(nóng)業(yè)信貸活動、試行農(nóng)業(yè)大災(zāi)保險等多舉措來解決新型農(nóng)業(yè)發(fā)展中所遇到的問題及困難,加強(qiáng)政策支持,促進(jìn)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提升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能力。2018年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鄉(xiāng)村振興應(yīng)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夯實基礎(chǔ)的同時,落實農(nóng)村一、二、三產(chǎn)業(yè)聯(lián)動發(fā)展,強(qiáng)化第一產(chǎn)業(yè)、優(yōu)化第二產(chǎn)業(yè)、靈活發(fā)展第三產(chǎn)業(yè)。這代表鄉(xiāng)村振興應(yīng)抓住產(chǎn)業(yè)興旺這個“牛鼻子”,而產(chǎn)業(yè)興旺須依托農(nóng)業(yè)發(fā)展方式的變化,轉(zhuǎn)變方式的著力點是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即以明確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為前提,各地實行政府獎補(bǔ)措施,支持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引導(dǎo)農(nóng)民依法、合理流轉(zhuǎn)土地。產(chǎn)業(yè)興旺也須要激活經(jīng)營主體、激活各類要素、激活需求市場,即首先重點開發(fā)人力資源,滿足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人才需求,使得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增速。且現(xiàn)階段很多地
方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把培育能引領(lǐng)貧困村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一類新型經(jīng)營主體作為產(chǎn)業(yè)扶貧的關(guān)鍵。2016年5月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發(fā)展計劃司劉北樺副司長在接受《農(nóng)經(jīng)》雜志記者采訪時也曾指出產(chǎn)業(yè)扶貧的關(guān)鍵是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
1.2 不僅是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特征所要求,更是丘陵山區(qū)地域特色及其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所決定
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明顯標(biāo)志之一即規(guī)模效益,而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理論認(rèn)為,規(guī)模效益是在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達(dá)到一定規(guī)模后出現(xiàn)和形成的,并在某一范圍內(nèi)隨著持續(xù)擴(kuò)大經(jīng)營規(guī)模而出現(xiàn)規(guī)模效益遞增的現(xiàn)象。可見,適度規(guī)模理論要求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首先必須形成一定規(guī)模,規(guī)模效益才會顯現(xiàn)并有可能達(dá)到帕累托最優(yōu)水平,但是這并非意味著規(guī)模越大經(jīng)濟(jì)效益就一定越高,關(guān)鍵在于規(guī)模的適度性[2-9]。近年來,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向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轉(zhuǎn)型跨越驅(qū)使山區(qū)鄉(xiāng)村處于比較優(yōu)勢的土地要素被快速激活,進(jìn)而促進(jìn)城鄉(xiāng)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導(dǎo)致鄉(xiāng)村地域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shù)等各種要素的再配置。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旨在強(qiáng)調(diào)各個生產(chǎn)要素的最優(yōu)組合及獲取最佳經(jīng)濟(jì)效益。其中,土地作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最上游的資源要素,其經(jīng)營的適度規(guī)模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水平。而生產(chǎn)力水平達(dá)到一定階段后就必然產(chǎn)生土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生產(chǎn)力水平也決定土地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推進(jìn)速度。因此,在山區(qū)小規(guī)模或超小規(guī)模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只能自給自足,難以獲取最優(yōu)經(jīng)濟(jì)利益,要推進(jìn)山區(qū)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培育以經(jīng)濟(jì)效益最大化為目標(biāo)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是關(guān)鍵。相對于平原地區(qū),地理條件“先天不足”的丘陵山區(qū)傳統(tǒng)農(nóng)戶只有少量土地,且分散成十幾塊,加之受道路、河流、林地、田坎、山梁等自然要素切割,地塊規(guī)模更小,地塊形狀亦不規(guī)則,這種小規(guī)模細(xì)碎化經(jīng)營造成機(jī)械化水平低、新技術(shù)推廣慢、耕作成本高而生產(chǎn)技術(shù)效率低,難以支撐規(guī)模化農(nóng)業(yè)。其中,發(fā)展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基礎(chǔ)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機(jī)械化,但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技術(shù)發(fā)展步伐緩慢的丘陵山區(qū)明顯滯后于平原地區(qū),機(jī)械化水平低下導(dǎo)致農(nóng)戶耕種方式受限,陡坡地面積大,路難修、機(jī)難通,很多田塊農(nóng)業(yè)機(jī)械根本不能到達(dá),且地塊小而分散、田塊落差大、土層薄、形狀不規(guī)則,農(nóng)業(yè)機(jī)械下田難,而低下的機(jī)械化程度造成人工成本增高,生產(chǎn)效率降低,經(jīng)濟(jì)效益不穩(wěn)定,農(nóng)民種糧意愿低。近年來,隨著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市場化的深入發(fā)展,農(nóng)民紛紛外出務(wù)工或遷走,據(jù)相關(guān)調(diào)查報道,目前我國2/3的農(nóng)戶仍是分散經(jīng)營,生產(chǎn)主力不是青壯年勞動力,而是留守老人和家庭婦女,他們在資金、技術(shù)、市場、管理等方面的弱勢難以支撐集約化農(nóng)業(yè),但勞動力的非農(nóng)化為資源的優(yōu)化組合和再配置提供了機(jī)遇,同時伴隨農(nóng)業(yè)勞動力“析出”,加之自然和社會經(jīng)濟(jì)因素的影響,致使鄉(xiāng)村人地關(guān)系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出現(xiàn)耕地撂荒、土地流轉(zhuǎn)、利用轉(zhuǎn)型、鄉(xiāng)村重構(gòu)與綜合整治[10]等,為土地規(guī)模流轉(zhuǎn)實現(xiàn)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土地流轉(zhuǎn)后,“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和“如何把握規(guī)模度”是目前擺在山區(qū)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中的一大難點,實踐證明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快速引入、培育、發(fā)展壯大是破解這一難點的關(guān)鍵,而如何將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吸引到農(nóng)村,因地制宜引導(dǎo)發(fā)展規(guī)模經(jīng)營格外重要。但在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過程中,部分主體常不切實際地圈占大量土地[11],結(jié)果對當(dāng)?shù)睾筮M(jìn)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以及優(yōu)化資源配置產(chǎn)生不良連帶效應(yīng)。因此,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解析與重構(gòu)研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2 新時代下多元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確定的多維困惑 ?近年來,在三產(chǎn)融合發(fā)展、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多元化、農(nóng)戶生計多樣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逐步提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社會化服務(wù)大力宣傳建設(shè)的條件下,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逐漸得到關(guān)注并取得一些成效。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不是單一地追求“規(guī)模”,而是同時強(qiáng)調(diào)“適度”(“適度”并不是追求某一生產(chǎn)要素的擴(kuò)張,而是實現(xiàn)勞動力、土地、農(nóng)資、農(nóng)業(yè)資本、農(nóng)業(yè)科技、農(nóng)業(yè)機(jī)械等所有要素的最優(yōu)組合[12])。即在本地農(nóng)業(yè)活動發(fā)展和社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條件適宜的前提下,采取相應(yīng)的流轉(zhuǎn)方式把農(nóng)戶分散經(jīng)營的責(zé)任田集中到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手中,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模式轉(zhuǎn)化為集約化、規(guī)模化、專業(yè)化的經(jīng)營模式。但是,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度”如何衡量?又如何把握好這個“度”?雖然國內(nèi)外諸多學(xué)者從適度規(guī)模測算、評價體系構(gòu)建、規(guī)模效益評價、驅(qū)動因素分析、規(guī)模經(jīng)營意愿及模式,以及土地流轉(zhuǎn)、生產(chǎn)投入、鄉(xiāng)村勞動力流出對規(guī)模經(jīng)營有何作用等展開研究,但針對這個“度”的問題仍存在許多疑惑和爭論。
2.1 規(guī)模報酬遞增還是遞減?
盡管規(guī)模報酬遞增是研究者和決策者共同期待的結(jié)果,但大部分學(xué)者基于對不同范圍和地區(qū)的實證研究,均否定存在“規(guī)模報酬遞增”,甚至有學(xué)者認(rèn)為“規(guī)模報酬遞減”存在于糧食生產(chǎn)中。如王嫚嫚等通過研究江漢平原354個水稻種植戶,發(fā)現(xiàn)將土地細(xì)碎化和耕地地力的影響納入考慮后,江漢平原水稻生產(chǎn)在此生產(chǎn)模式下規(guī)模報酬不變,且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現(xiàn)象不存在,但農(nóng)戶“理性經(jīng)濟(jì)人”如經(jīng)營規(guī)模大則特征表現(xiàn)更明顯[13]。金生霞等基于河西走廊4市10個縣(市、區(qū))13個鄉(xiāng)(鎮(zhèn))578農(nóng)戶的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河西走廊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處于規(guī)模報酬遞減階段,現(xiàn)有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條件下,該地區(qū)現(xiàn)有規(guī)模遠(yuǎn)遠(yuǎn)小于勞均最優(yōu)規(guī)模和戶均最優(yōu)規(guī)模[14]。同時,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規(guī)模經(jīng)濟(jì)是存在的,如盧華等在研究土地細(xì)碎化對生產(chǎn)成本的影響時,發(fā)現(xiàn)農(nóng)作物生產(chǎn)存在規(guī)模經(jīng)濟(jì)[15]。許慶等基于我國糧食主產(chǎn)區(qū)5省100個村莊1 049個農(nóng)戶的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除了粳稻,其余糧食作物生產(chǎn)均存在規(guī)模經(jīng)濟(jì)[16]。
2.2 “度”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
有學(xué)者認(rèn)為以利潤最大化、以效率最大化作為“度”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應(yīng)是多維度的,包括經(jīng)濟(jì)效益、社會效益、生態(tài)效益的結(jié)合,土地生產(chǎn)率、勞動生產(chǎn)率和資源利用效率的統(tǒng)一[13-18]。從測“度”方法上看,多提出并采用經(jīng)驗法、直觀評估法、生產(chǎn)函數(shù)法、指標(biāo)評價法等,如徐海南運(yùn)用經(jīng)驗法,選取勞均產(chǎn)量、勞均純收入、產(chǎn)量、商品率等指標(biāo),對比不同規(guī)模組生產(chǎn)要素的平均利用效益,進(jìn)而確定蘇南地區(qū)的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19]。張海亮等通過種植業(yè)在現(xiàn)實生產(chǎn)中的實際投工量,測算目前生產(chǎn)力水平及經(jīng)營環(huán)境下,農(nóng)業(yè)對勞動力的需求,進(jìn)而推算出土地經(jīng)營的適度規(guī)模[20]。鄖宛琪運(yùn)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chǎn)函數(shù)模型,研究蘇南、蘇北兩地家庭農(nóng)場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確定標(biāo)準(zhǔn)[21]。汪亞雄運(yùn)用線性回歸分析、投入產(chǎn)出比較分析、勞動力耕地負(fù)擔(dān)分析、勞動力收入比較分析等統(tǒng)計分析方法相結(jié)合計算南方各省農(nóng)戶土地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22]。劉秋香等改進(jìn)灰色系統(tǒng)聚類方法,定量測算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的適度規(guī)模[23]。林善浪指出在勞動生產(chǎn)率、土地生產(chǎn)率、資金生產(chǎn)率三者難以平衡兼顧時,至少保證土地生產(chǎn)率不降低,犧牲土地生產(chǎn)率而單純追求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增加勞均收入,與中國國情不相符[24]。于洋則指出勞動生產(chǎn)率與土地生產(chǎn)率在農(nóng)地規(guī)模經(jīng)營中出現(xiàn)的矛盾,應(yīng)在分工經(jīng)濟(jì)的基礎(chǔ)之上建立,由分工效率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25];程秋萍認(rèn)為這個判定標(biāo)準(zhǔn)只能在實踐中產(chǎn)生[26]。
2.3 三是“度”值存在顯著差異?
周娟認(rèn)為,要素資源稟賦(勞動力、土地、資本)的差異產(chǎn)生了不同的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決策,進(jìn)行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動力與條件在不同類型農(nóng)戶之間差異明顯,以農(nóng)戶類型為依據(jù)推進(jìn)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更適合[27]。程秋萍也指出適度規(guī)模靠某類主體的單一推動或單一意愿必定不能實現(xiàn),不同主體“適度”的標(biāo)準(zhǔn)也不相同[26]。從測“度”結(jié)果看,主要討論農(nóng)業(yè)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勞均、戶均、人均和地塊耕地。有學(xué)者認(rèn)為勞均耕地適度規(guī)模為0.33~0.47 hm2[23],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0.67~1.00 hm2[28-29];有學(xué)者認(rèn)為蔗農(nóng)戶均適度規(guī)模為1.61~1.84 hm2[30],稻農(nóng)戶均適度規(guī)模為5 hm2,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只宜達(dá)到0.66 hm2的臨界規(guī)模[22];有學(xué)者認(rèn)為人均適度規(guī)模為0.22~0.41 hm2[31];有學(xué)者認(rèn)為糧食作物適度規(guī)模為0.67~1.33 hm2、經(jīng)濟(jì)作物適度規(guī)模為0.4~0.6 hm2[32],也有認(rèn)為適度規(guī)模約為7.3 hm2較合適[33];有學(xué)者認(rèn)為1.12~0.35 hm2為水田地塊的適度規(guī)模,1.17~2.82 hm2為旱地地塊的適度規(guī)模[34]。關(guān)乎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的探討則集中在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2類新型主體,如辛良杰認(rèn)為2016年中國糧食類家庭農(nóng)場的適度規(guī)模一般在13~14 hm2,約為全國戶均耕地面積的30倍[35]。韓蘇等認(rèn)為,果蔬類家庭農(nóng)場小規(guī)模、中等規(guī)模、大規(guī)模的最優(yōu)經(jīng)營面積分別為1.33~2.00 hm2、4.67~6.67 hm2或8.00~10.00 hm2、26.67~33.33 hm2[36]。孔令成等提出糧食家庭農(nóng)場最優(yōu)土地投入規(guī)模為8.13~8.40 hm2,其次為11.53~13.07 hm2[37];鄒運(yùn)梅等認(rèn)為,不考慮種糧補(bǔ)貼,在追求產(chǎn)出利潤最大化時家庭農(nóng)場經(jīng)營存在適度規(guī)模,并得出洞庭湖區(qū)家庭農(nóng)場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為9.52~13.23 hm2[38];但關(guān)付新認(rèn)為種糧家庭農(nóng)場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在不同情況下是不同的,家庭自有勞動力占比和家庭農(nóng)業(yè)收入占比決定家庭農(nóng)場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的上限和下限[39]。針對合作社而言,鄭適等認(rèn)為,在考慮植保無人機(jī)技術(shù)采納的約束下,合作社規(guī)模門檻為 2 hm2[40];申云等認(rèn)為,在糧食產(chǎn)量與收入最優(yōu)化下種糧合作社農(nóng)地經(jīng)營規(guī)模一般為40~66.67 hm2[41]。范喬希等對山區(qū)合適耕地經(jīng)營規(guī)模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jì)作物的適度規(guī)模為1.62 hm2、糧食作物的適度規(guī)模為 1.64 hm2,差異不顯著,距離影響較大,0.5 km內(nèi)適度規(guī)模為 1.90 hm2、0.5~1 km適度規(guī)模為2.12 hm2,單位勞動力的適度規(guī)模相差0.2 hm2[42]。
綜上,因目標(biāo)不同、標(biāo)準(zhǔn)不同、地區(qū)不同、產(chǎn)業(yè)不同,主體不同得出的“度”也就不同。發(fā)展土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方向與適度規(guī)模目標(biāo)及其評價體系、標(biāo)準(zhǔn)有關(guān),但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目標(biāo)以“利潤最大化”還是“效率最大化”?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怎樣取舍各標(biāo)準(zhǔn)等仍存在不同見解,至今仍無統(tǒng)一意見[43]。平原地區(qū)資本量充足但耕地緊缺,人力資本較高,資本可替代勞動力,適度規(guī)模大,而丘陵山區(qū)機(jī)械替代勞動力成本較高,適度規(guī)模較小。總體上看,由于大都面向傳統(tǒng)糧油作物從單一傳統(tǒng)農(nóng)戶層面核算,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的面積較小,且由于有的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biāo),而有的以“效率最大化”為目標(biāo),導(dǎo)致即使同一作物類型傳統(tǒng)農(nóng)戶也出現(xiàn)不同適度值。但是,張連剛等指出意愿規(guī)模大小無法用單位土地凈收益解釋,收益最大化不僅僅是農(nóng)戶追求意愿規(guī)模的初衷,規(guī)模選擇還存在“貪大”心理[44]。不難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經(jīng)營中“度”的標(biāo)準(zhǔn)在某些地區(qū)還把握不準(zhǔn),如大規(guī)模土地流轉(zhuǎn)引起土地流轉(zhuǎn)租金迅速上升,從而導(dǎo)致在金融、土地流轉(zhuǎn)中介、農(nóng)保、農(nóng)技推廣等服務(wù)方面難以為新型經(jīng)營主體提供有力保障與穩(wěn)定支持。因此,不同類型經(jīng)營主體應(yīng)根據(jù)自有資源、社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政策、市場等條件,確定相應(yīng)的實際經(jīng)營規(guī)模。生產(chǎn)力水平和生產(chǎn)方式在不同地區(qū)和不同類型經(jīng)營主體之間不盡相同,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影響因素也不同,因此單一形式是不可取的。
3 丘陵山區(qū)新型經(jīng)營主體規(guī)模經(jīng)營“度”確定的時代啟示 ?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向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過程中必然產(chǎn)生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與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是一個動態(tài)概念,如何確定規(guī)模大小,除考慮地區(qū)間的生產(chǎn)共性外,還須兼顧生產(chǎn)力要素層次的特殊性和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形式的特殊性。然而,目前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宏觀政策和理論研究的基本邏輯和價值取向,主要是基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背景下家庭承包經(jīng)營所致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規(guī)模過于細(xì)化分散、土地生產(chǎn)率和勞動生產(chǎn)效率不高的客觀現(xiàn)實,從而開展傳統(tǒng)農(nóng)戶土地經(jīng)營適度規(guī)模的實證研究,主張通過引導(dǎo)農(nóng)地流轉(zhuǎn)促進(jìn)土地規(guī)模經(jīng)營發(fā)展。這種價值取向?qū)τ谵D(zhuǎn)變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理念、加快農(nóng)地流轉(zhuǎn)、發(fā)展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經(jīng)營等都已發(fā)揮正向作用,但同時也帶來土地流轉(zhuǎn)越多越快越好、經(jīng)營規(guī)模越大越全越好等認(rèn)識誤區(qū),且對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與傳統(tǒng)經(jīng)營主體的經(jīng)營目標(biāo)、要素稟賦差異和對經(jīng)營規(guī)模度的地域差異和產(chǎn)業(yè)差異有所忽視。
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因國家及區(qū)域政策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演化的不同而異。在前期調(diào)查研究中認(rèn)識到在“用地、招商、投入、融資、資金、補(bǔ)貼、保險、稅收”等相關(guān)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政策“大禮包”放送下,尤其是隨著“關(guān)于加快培育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推動國家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示范區(qū)建設(shè)的意見”和“鼓勵新型經(jīng)營主體參與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等政策的落地,使得在土地細(xì)碎化、基礎(chǔ)設(shè)施弱、產(chǎn)業(yè)特色不突出的山區(qū)也在不斷發(fā)展壯大,而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園區(qū)就是各類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主戰(zhàn)場,也是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多元化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平臺。資源要素稟賦在不同類型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間存在較大差異。同時,多元化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刺激了產(chǎn)業(yè)多元化發(fā)展,而不同產(chǎn)業(yè)類型下各類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實際經(jīng)營規(guī)模及規(guī)模效益均參差不齊,且大部分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表現(xiàn)出對擴(kuò)大經(jīng)營規(guī)模有強(qiáng)烈的意愿,但受山區(qū)地形復(fù)雜、地塊破碎、優(yōu)質(zhì)勞動力少、周邊地已被其他主體流轉(zhuǎn)等現(xiàn)實條件的約束,找不到擴(kuò)大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切實可行之路,對工程、政策有強(qiáng)烈的訴求。然而,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關(guān)注點集中在新型主體的類型界定、結(jié)構(gòu)變化、優(yōu)勢識別、功能定位、利益訴求、模式探索和驅(qū)動機(jī)制等方面[45-46],并對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尤為關(guān)注[46-47]。汪發(fā)元等認(rèn)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特征的地域性很強(qiáng),但其變化也具有共性,如主體類型呈多元化[48],各類主體數(shù)量不全是增長的,減少過程呈兩極分化,即大規(guī)模和小規(guī)模主體數(shù)量增加而中等規(guī)模主體明顯下降,且各類主體發(fā)展受區(qū)域內(nèi)部發(fā)展條件,如耕地資源稟賦、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土地流轉(zhuǎn)發(fā)生率的影響[43]。此外,政策優(yōu)惠、項目推進(jìn)和制度供給等區(qū)域外部環(huán)境也是影響各類主體變遷的重要因素[44,47,49]。盡管為了摸清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情況,甄別其發(fā)展的堵點,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在全國范圍內(nèi)已開展了6期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指數(shù)調(diào)查研究,這份微觀數(shù)據(jù)充分展示了各類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數(shù)量增長、發(fā)展?jié)摿Α⒕C合績效、帶動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彌補(bǔ)了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研究的數(shù)據(jù)缺失和研究范式的不足。但是,全國的數(shù)據(jù)僅局限于某個時間點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數(shù)量,而未考慮主體數(shù)量增減變化的時空過程和山區(qū)與平原之間的差異性。現(xiàn)有研究雖從微觀層面對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現(xiàn)狀及困境有一定研究[50],但對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變化的時空格局演變過程的研究并不多見,且多元化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的落腳點在于通過規(guī)模化、集約化、組織化生產(chǎn)帶動當(dāng)?shù)靥厣a(chǎn)業(yè)發(fā)展,并提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層次,但從內(nèi)部透視各類主體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也較少,而立足主體要素差異和產(chǎn)業(yè)特性探討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適度規(guī)模問題更少。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應(yīng)因地制宜、因業(yè)而異,不僅要關(guān)注個體數(shù)量增長、質(zhì)量提升,也要強(qiáng)化空間變化,更要體現(xiàn)不同產(chǎn)業(yè)類型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的差異,尤其是在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擴(kuò)大誘發(fā)主體進(jìn)退間的用地沖突,須要明確經(jīng)營主體進(jìn)退的根源,處理好數(shù)量與質(zhì)量的關(guān)系、各類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重視主體間的競爭合作[51]。那么,在山區(qū)多元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如何形成?主體空間上如何配置?主體間要素資源有何差異?主體產(chǎn)業(yè)間有何關(guān)聯(lián)?主體間合作競爭有何風(fēng)險?這些均是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助推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過程中亟待明確的重要課題。
現(xiàn)有研究一般從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單方面展開,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研究主要以個體農(nóng)戶行為為主體,其他類型主體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關(guān)注家庭農(nóng)場和農(nóng)民合作社,碎片化分割研究易顧此失彼,無法順應(yīng)差異化的要素和產(chǎn)業(yè)方向,難以實現(xiàn)對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 “度”的正確把握。首先,鑒于傳統(tǒng)農(nóng)戶與新型主體經(jīng)營目標(biāo)的差異,前者是自給自足型生產(chǎn),追求產(chǎn)量最大化,后者是商品化生產(chǎn),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次,傳統(tǒng)農(nóng)戶與新型主體在要素資源方面存在差異,后者較前者在土地、人力、資本、機(jī)械、設(shè)施、技術(shù)、信息、金融、社會等要素資源方面具有優(yōu)勢;再次,考慮到傳統(tǒng)農(nóng)戶與新型主體在行為選擇方面的差異,前者多限于家庭勞動力,土地使用無須付費,更加愿意選擇種植水稻等傳統(tǒng)作物,相反新型主體更傾向季節(jié)性雇用勞動力,機(jī)械代替勞動力,除了土地費等生產(chǎn)要素投入外,還涉及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投入和銀行貸款等,產(chǎn)業(yè)選擇更傾向蔬菜、糧油、苗木、花卉、柑橘、花椒、水產(chǎn)等多元化種植,更重要的是,收益不僅來源于農(nóng)產(chǎn)品直接收益,還包含產(chǎn)品加工、休閑旅游、文化科教等多元方式等帶來的產(chǎn)品高附加值。因此,須要找出新型主體自己的“度”。同時,多種形式的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須兼顧不同區(qū)域的差異。這些在山區(qū)鄉(xiāng)村新出現(xiàn)的生產(chǎn)主體,與傳統(tǒng)小農(nóng)戶相比,他們在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shù)、市場等資源要素方面更具優(yōu)勢,成為山區(qū)發(fā)展多種形式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主要載體,在鄉(xiāng)村振興、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與產(chǎn)業(yè)扶貧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另外,不同經(jīng)營主體彼此間資源稟賦的差異又決定了其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適度規(guī)模的差異,也意味著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實現(xiàn)存在不同方式。因為實現(xiàn)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可以通過多種形式,不同地域、產(chǎn)業(yè)、距離、階段、資源等條件下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度都有所差異。如在土地分布零散、地勢起伏不平、交通不便的丘陵山區(qū),其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就比平原區(qū)要小一些。換言之,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與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經(jīng)營規(guī)模有別,不僅源于經(jīng)營主體的變化,還因經(jīng)營目標(biāo)的不同,也與生產(chǎn)力水平有關(guān)。山區(qū)農(nóng)業(yè)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不是簡單的擴(kuò)大規(guī)模,而應(yīng)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應(yīng)該是在最佳生產(chǎn)要素、資源配置結(jié)合下的經(jīng)營,具有社會經(jīng)濟(jì)、地域、政策、生態(tài)和技術(shù)意義上的特殊性。那么,適度規(guī)模應(yīng)如何確定,多大的經(jīng)營規(guī)模適應(yīng)當(dāng)前山區(qū)鄉(xiāng)村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不同產(chǎn)業(yè)多大的經(jīng)營規(guī)模是適度的?多大的規(guī)模才算是各個類型經(jīng)營主體的適度規(guī)模?多元化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經(jīng)營規(guī)模為多大才有利?又怎樣實現(xiàn)?這些都是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助力鄉(xiāng)村振興、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產(chǎn)業(yè)扶貧過程中亟待明確的重要課題。
4 小結(jié)
在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開展的進(jìn)程中,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度”應(yīng)找準(zhǔn),適度規(guī)模與主體類型是不可分割的,“度”應(yīng)兼顧經(jīng)營主體培育的產(chǎn)業(yè)階段性、經(jīng)營主體要素資源的異質(zhì)性和產(chǎn)業(yè)類型間的差異性。丘陵山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解析與重構(gòu)須要從以下3個方面著手:第一,不同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以引領(lǐng)什么類型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培育為重點,如何基于要素差異性、功能互補(bǔ)性、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性,處理大小業(yè)主、先進(jìn)后進(jìn)業(yè)主、本地與外來業(yè)主等經(jīng)營主體間的關(guān)系,規(guī)避主體培育中的合作競爭風(fēng)險。應(yīng)該處理好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之間、政府與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之間、傳統(tǒng)農(nóng)戶與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使得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工作能夠更加順利地開展。第二,針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目標(biāo)的轉(zhuǎn)變,丘陵山區(qū)土地生產(chǎn)力水平的約束、經(jīng)營主體資源稟賦的差異,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階段的演化和產(chǎn)業(yè)類型規(guī)模需求的差異,把握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度”。應(yīng)根據(jù)自身特點找準(zhǔn)定位,尋求各類型適度規(guī)模的“度”,為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提供合理的參考。第三,實現(xiàn)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形式是多樣化的,不同階段、地域、尺度、種養(yǎng)類型、資源稟賦、經(jīng)營性質(zhì)所對應(yīng)的最優(yōu)實現(xiàn)路徑應(yīng)有所不同。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當(dāng)?shù)貤l件尋找到適合自己的規(guī)模經(jīng)營,從而提升生產(chǎn)經(jīng)營效率。
參考文獻(xiàn):
[1]臧 濤,呂 曉,張全景. 耕地規(guī)模經(jīng)營問題的國內(nèi)研究述評[J]. 資源開發(fā)與市場,2018,34(2):166-171,224.
[2]曹東勃. 適度規(guī)模:趨向一種穩(wěn)態(tài)成長的農(nóng)業(yè)模式[J]. 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3(2):29-36.
[3]信桂新,楊朝現(xiàn),邵景安,等. 基于農(nóng)地流轉(zhuǎn)的山地丘陵區(qū)土地整治技術(shù)體系優(yōu)化及實證[J]. 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2017,33(6):246-256.
[4]張仕超,魏朝富,邵景安,等. 丘陵區(qū)土地流轉(zhuǎn)與整治聯(lián)動下的資源整合及價值變化[J]. 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2014,30(12):1-17.
[5]梁流濤,翟 彬,樊鵬飛. 基于環(huán)境因素約束的農(nóng)戶土地利用效率及影響因素分析——以河南省糧食生產(chǎn)核心區(qū)為例[J]. 地理科學(xué),2016,36(10):1522-1530.
[6]王微恒,朱會義. 中國省域農(nóng)戶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與地區(qū)專業(yè)化實證分析[J]. 地理學(xué)報,2017,72(2):269-278.
[7]Shao J A,Zhang S C,Li X B. Farmland marginaliz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5,25(6):701-722.
[8]李升發(fā),李秀彬. 中國山區(qū)耕地利用邊際化表現(xiàn)及其機(jī)理[J]. 地理學(xué)報,2018,73(5):803-817.
[9]戈大專,龍花樓,楊 忍. 中國耕地利用轉(zhuǎn)型格局及驅(qū)動因素研究——基于人均耕地面積視角[J]. 資源科學(xué),2018,40(2):273-283.
[10]屠爽爽,龍花樓,張英男,等. 典型村域鄉(xiāng)村重構(gòu)的過程及其驅(qū)動因素[J]. 地理學(xué)報,2019,74(2):323-339.
[11]Takoutsing B,Martin J A R,Weber J C,et al.Landscape approach to assess key soil functional properties in the highlands of cameroon:repercussions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for land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J].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2017,178:35-44.
[12]柳曉倩,王長安,伍駿騫. 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CES生產(chǎn)函數(shù)下的解釋[J]. 中國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18,39(9):87-93.
[13]王嫚嫚,劉 穎,陳 實. 規(guī)模報酬、產(chǎn)出利潤與生產(chǎn)成本視角下的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基于江漢平原354個水稻種植戶的研究[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7(4):83-94.
[14]金生霞,陳 英,楊倩倩,等. 河西走廊農(nóng)地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計量研究——基于578農(nóng)戶調(diào)查的研究[J]. 干旱區(qū)資源與環(huán)境,2012,26(11):6-11.
[15]盧 華,胡 浩. 土地細(xì)碎化增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成本了嗎?——來自江蘇省的微觀調(diào)查[J]. 經(jīng)濟(jì)評論,2015(5):129-140.
[16]許 慶,尹榮梁,章 輝. 規(guī)模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報酬與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基于我國糧食生產(chǎn)的實證研究[J]. 經(jīng)濟(jì)研究,2011,46(3):59-71,94.
[17]蔣和平,蔣 輝. 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實現(xiàn)路徑研究[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與管理,2014(1):5-11.
[18]黃河清. 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問題綜述[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1986(7):27-29.
[19]徐海南. 蘇南地區(qū)農(nóng)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研究[D]. 武漢: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2005:5-54.
[20]張海亮,吳楚材. 江浙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經(jīng)營條件和適度規(guī)模確定[J]. 經(jīng)濟(jì)地理,1998,18(1):85-90.
[21]鄖宛琪. 家庭農(nóng)場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及其實現(xiàn)路徑研究[D]. 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2016:4-84.
[22]汪亞雄. 南方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分析[J]. 統(tǒng)計與決策,1997(5):21-23.
[23]劉秋香,鄭國清,趙 理. 農(nóng)業(yè)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定量研究[J]. 河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1993,27(3):244-247.
[24]林善浪. 農(nóng)村土地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效率評價[J].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00(2):37-43.
[25]于 洋. 對中國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經(jīng)營的理論反思[J]. 長春大學(xué)學(xué)報,2004,14(1):20-23.
[26]程秋萍. 哪一種適度規(guī)模?——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社會學(xué)解釋[J]. 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7,34(1):69-82.
[27]周 娟. 基于農(nóng)戶家庭決策的土地流轉(zhuǎn)與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微觀機(jī)制分析[J].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8,18(5):88-97.
[28]許治民. 種植專業(yè)戶經(jīng)營規(guī)模適度分析[J]. 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1994(1):85-88.
[29]韋敬楠,張立中,胡天石. 廣西蔗農(nóng)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測算及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 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17,22(11):199-207.
[30]Wang J Y,Xin L J. Is larger scale better ? Evidence from rice farming in Jianghan plain[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8,9(4):352-364.
[31]付曉亮.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及其效益實證研究--以四川省為例[J]. 中國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17,38(5):72-75.
[32]陳 杰,蘇 群. 土地流轉(zhuǎn)、土地生產(chǎn)率與規(guī)模經(jīng)營[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7(1):28-36.
[33]張成玉. 土地經(jīng)營適度規(guī)模的確定研究——以河南省為例[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5,36(11):57-63.
[34]Zhang S C,Wei C F,Shao J A,et al.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ous cropping systems in the purple-soiled,hilly region of southwestern China[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2016,13(12):2205-2223.
[35]辛良杰. 中國糧食生產(chǎn)類家庭農(nóng)場的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研究[J]. 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2020,36(10):297-306.
[36]韓 蘇,陳永富.浙江省家庭農(nóng)場經(jīng)營的適度規(guī)模研究 ——以果蔬類家庭農(nóng)場為例[J]. 中國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15,36(5):89-97.
[37]孔令成,余家鳳.家庭農(nóng)場適度規(guī)模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8,46(16):301-305.
[38]鄒運(yùn)梅,何清泉.家庭農(nóng)場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的實證研究[J]. 浙江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9,60(2):310-313.
[39]關(guān)付新.華北平原種糧家庭農(nóng)場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探究——以糧食大省河南為例[J].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8(10):22-38.
[40]鄭 適,陳茜苗,王志剛. 土地規(guī)模、合作社加入與植保無人機(jī)技術(shù)認(rèn)知及采納——以吉林省為例[J]. 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經(jīng)濟(jì),2018(6):92-105.
[41]申 云,申紅芳. 種糧合作社的適度經(jīng)營規(guī)模研究[J]. 中國土地科學(xué),2018,32(3):74-80.
[42]范喬希,邵景安,應(yīng)壽英. 山區(qū)合適耕地經(jīng)營規(guī)模確定的實證研究——以重慶市為例[J]. 地理研究,2018,37(9):1724-1735.
[43]于亢亢,朱信凱,王 浩. 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變化趨勢與動因——基于全國范圍縣級問卷調(diào)查的分析[J].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2(10):78-90.
[44]張連剛,支 玲,謝彥明,等. 農(nóng)民合作社發(fā)展頂層設(shè)計:政策演變與前瞻——基于中央“一號文件”的政策回顧[J]. 中國農(nóng)村觀察,2016(5):10-21,94.
[45]郭慶海. 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功能定位及成長的制度供給[J].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3(4):4-11.
[46]李冬艷,余曉洋. 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水平評價體系構(gòu)建及測度[J]. 經(jīng)濟(jì)縱橫,2020(2):113-120.
[47]周 振,張 琛,鐘 真.“統(tǒng)分結(jié)合”的創(chuàng)新與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基于新田地種植專業(yè)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9(8):49-58.
[48]汪發(fā)元. 中外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展現(xiàn)狀比較及政策建議[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4,35(10):26-32.
[49]王國剛,劉合光,錢靜斐,等. 中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主體變遷及其影響效應(yīng)[J]. 地理研究,2017,36(6):1081-1090.
[50]張 磊,羅光強(qiáng). 現(xiàn)實與重構(gòu):我國糧食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困境與擺脫——基于川、湘246個稻作大戶的調(diào)查[J]. 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2018(5):28-33.
[51]劉靈輝,劉 燕. 家庭農(nóng)場土地適度規(guī)模集中實現(xiàn)過程中的博弈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8,28(9):15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