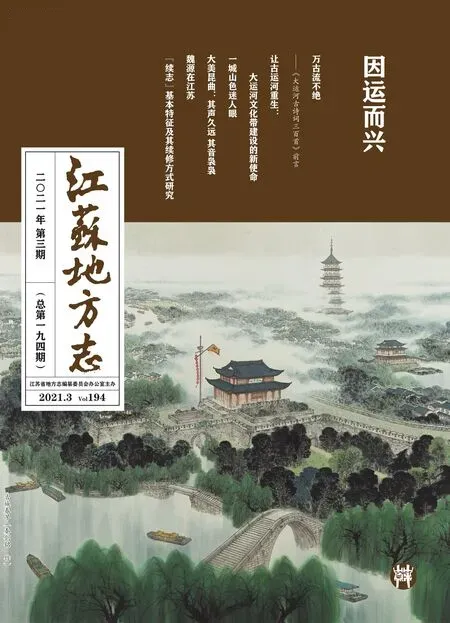萬古流不絕
——《大運河古詩詞三百首》前言
◎程章燦
(南京大學,江蘇南京 210023)
眾所周知,大運河是舉世矚目的東方奇跡,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運河實際上有兩種存在形態,甚至可以說,這個世界上同時存在著兩條大運河。
一條是在中國大地上流淌著的大運河,它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個部分,流經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河北、天津、北京8 個省市,貫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貫通南北。這條綿延近3200 公里的大運河,是古代中國人偉大的工程創造,溝通了中國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吳越等文化區域,是促進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的大動脈。這條大運河可以溯源至春秋時代,已有2500 多年的歷史,但直至今天,它仍與民生國運須臾不可分離,是中國大地的地理奇觀,也是“一部書寫在華夏大地上的宏偉詩篇”。
另一條是在中國古詩詞中流淌的大運河,歷經隋、唐、宋、元、明、清,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光里,在以宋之問、張若虛、王維、孟浩然、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杜牧、李商隱、韋莊、柳永、范仲淹、張先、晏殊、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賀鑄、周邦彥、楊萬里、姜夔、戴復古、文天祥、袁桷、張翥、王冕、張羽、高啟、李東陽、楊慎、朱曰藩、尤侗、陳維崧、朱彝尊、屈大均、王士禛、潘耒、鄭板橋、姚鼐、龔自珍、文廷式等人為代表的眾多著名詩家詞人的手中,這條河流出了平仄相間的音韻諧美,也流出了五彩繽紛和回味不盡的雋永。這條河沉淀了國家民族的盛衰分合,也浸透了個人的悲歡離合。這是一條古詩詞的大運河,盡管長度難以精確統計,深度也難以準確測量,但是,可以確定無疑的是,它是從最有才華、最為敏感的一批中國詩人的心上淌出來,又流進更多中國人的心靈里。這是中國人心中的一條大運河。
地上的大運河與心中的大運河,當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實體的、物質的,后者是虛擬的、文獻的;前者是在大地之上流淌的,后者是在文字之中流淌的;前者是土石水草混合的流動道路,后者是字詞章句構筑的文本之河;前者保留了歷史遺址和文化遺跡,后者存錄了古人的身影、聲音和情懷。另一方面,心中的大運河又是地上的大運河的映現,兩條大運河交叉纏繞、交相輝映,在日夜不停的流淌中,積淀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符號。
這條古詩詞的運河,雖然歷經一千多年,凝聚了無數名家巨匠之才智,卻鮮少以物質形態固定下來,也罕見系統的收集、爬梳和整理。編纂《大運河古詩詞三百首》,就是要以書籍的形式,呈現這條文本的大運河。我們從歷代詩詞總集和別集中,精選227 位詩人吟詠大運河的古詩詞三百首,加上簡要的注釋以及要言不煩的評析,再配上精美的插圖出版。全編共選錄各體古詩詞三百首,這是第一次以“三百首”這種經典選本的方式,將這條古詩詞的大運河引介給21 世紀的讀者。從此,這條大運河將從古人的心目之中,潺潺流入今人的心目。
這部大運河古詩詞選本,是地上的大運河和心中的大運河的融合,是古人的心目與今人心目的通接,是兩條大運河在經典化道路上的交匯。大運河早已成為中華文明史的經典符號,而“三百首”則是中國文學史的經典符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夫子一錘定音,奠定了《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的經典地位。后人繼起,編撰了以《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為代表的“三百首”系列選本。“三百首”作為文學經典的地位越來越牢固,不可動搖。《大運河古詩詞三百首》中所選詩家詞人,大多是古詩詞的經典作家,前文所開列的那一長串名單可以為證。這些名家出手不凡,藝術功力深湛,為這些作品奠定了經典化的基礎。例如,被稱為“詩仙”的唐代詩人李白所作《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這原本是一首尋常的離別詩,但李白開門見山,開口便道:“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有了這樣氣象恢宏、大氣磅礴的句子,這詩便顯得不同尋常。本篇篇名中的“萬古流不絕”,正是出自李白此篇。對于李白來說,“萬古流不絕”自然說的是他眼中那條盛唐開元二十五年(737)潤州刺史齊澣所開鑿的瓜洲新河,也就是瓜洲運河,但我們完全可以借用這一句詩,來描述這條古詩詞的大運河。
面對大運河這條歷史長河,詩人們是觀察者,也是感受者;是評說者,也是記錄者。他們的感興是豐富的,他們的視角是多樣的:
在詩人眼中,大運河是一條時間之河。從時間上看,大運河所涉及的時間,既有突出的漫長性,又有明顯的階段性。就漫長性來說,它長達2500 多年,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時代吳王夫差開鑿邗溝那個時代。就階段性來說,大運河的歷史主要分為三期:雛形草創的春秋時期,這可以稱為大運河的1.0 版本時代;規模初見的隋代時期,這可以稱為大運河的2.0 版本時代;體系成型的元朝時期,這可以稱為大運河的3.0 版本時代。越到后來,大運河的網絡聯接能力越強,影響輻射范圍越廣。其中,隋代無疑是最有歷史意味、最值得關注的時段。“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隋代只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但是,隋文帝尤其隋煬帝主持開鑿了山陽瀆、通濟渠、永濟渠,又重新疏通擴大了江南運河和浙東運河,使運河實現了全線貫通,成為全國性的運河體系,真正具有了“大”的規模和氣勢。從這一點來說,隋代承上啟下,貢獻最大。而大運河作為隋代給中國留下的最為重要的歷史遺產,其成敗利弊,自然成為后人評說隋朝及隋煬帝的最重要焦點,本書所選古詩詞中,以隋堤、隋宮、隋帝陵為吟詠主題的,可謂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與此同時,隋煬帝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箭垛式的人物”,幾乎受到千夫所指。實際上,隋煬帝之惡未必如史書所譴責的那樣不堪,這正如當年子貢評說商紂王的時候說過的:“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汴河懷古二首》之二中寫道:“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比起屢見不鮮、陳陳相因的懷古感慨,比起諸多人云亦云的史論,皮日休這篇懷古詩貌似翻案,實則持論公平,一分為二,還隋朝以及隋煬帝以公道,不僅體現了詩人獨特的視角,而且體現了他超卓的史識。

在詩人眼中,大運河是一條空間之河。從空間上看,大運河從南到北分為幾段,沿線串連了很多古都名城、名山大川,溝通了多個不同的文化區域。古詩詞中均有涉及,多少不均。把古詩詞中寫到的這些地點聯結起來,就串成一條大運河的詩歌之路。很多歷史文化名城的命運,與大運河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有些名城就是由大運河催生的,更有甚者,民間乃至于出現了“北京城是從大運河上漂來的”的說法。望文生義地說,大運河就是這些名城的“大運”之河。以大運河江蘇段為例,分布在大運河沿線的淮安、揚州、高郵、鎮江、蘇州等名城的興衰,與大運河都有密切的關系。揚州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揚州處于大運河與長江交匯點上,自隋煬帝南游,在此修筑宮殿迷樓,揚州逐漸脫穎而出,成為全國水陸交通中心和中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到了唐代,揚州與西南的益州(成都)并稱“揚一益二”,是唐代除東西兩京以外最引人矚目的繁華城市。唐代詩人張祜客游至此,曾作《縱游淮南》一詩,表達其由衷的歡喜贊嘆之情:“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一個人生于何地,是不由自主的,但葬于何地,卻可以選擇。張祜不是揚州人,沒有生長于揚州自是遺憾,只能希冀死后葬于揚州,可見他對這座運河之城的高度認同。另一方面,揚州又因其與隋代的特殊關系,而成為大運河文化帶最富有意味的時空交匯點之一。本書所選詩詞作品,有關揚州的特別多,并非偶然。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榮的城市景象,催生了很多優秀的運河詩篇,比如唐代揚州籍詩人張若虛的名篇《春江花月夜》。張若虛僅憑這一篇作品就名垂詩史,被人稱為“孤篇橫絕,竟為大家”。有人說這首詩創作于瓜洲鎮,有人說創作于廣陵古曲江之地,總而言之,它是揚州運河文化中心地帶的產物。被歷代朝鮮半島學人尊為朝鮮半島文學宗祖的新羅文人崔致遠,在唐朝居留17 年,曾任職于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他回國前作《酬楊贍秀才送別》,期望“好把壯心謀后會,廣陵風月待銜杯”,表達了對友人及唐朝的依依難舍之情。

繁忙的運河航運
詩人們觀察作為空間之河的大運河,還有另外一個特色視角,那就是眼光開闊,涉及整個大運河文化帶。根據《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大運河文化帶劃分為三個層次:“核心區” “拓展區” “輻射區”。核心區“主要指大運河主河道流經的縣(市、區),包含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是孕育形成大運河文化的主要空間,也是大運河文化帶的關鍵區域”;拓展區“主要是指大運河主河道流經的地市,是大運河文化向外逐步拓展與沿線地域文化融合的交匯地帶,也是大運河文化帶的重點區域”;輻射區“主要是指大運河主河道流經的省(市),是大運河文化進一步向外傳播輻射的聯動區域,也是支撐和保障大運河文化帶的省域空間”。本書所選三百首詩詞,涉及大運河文化輻射區的8個省(市),多數屬于大運河文化帶的核心區和拓展區。其中題詠大運河江蘇段的作品選錄較多,這主要是因為此類作品本身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編者有意突出這一重點。
在詩人眼中,大運河是一條意象之河,流淌著無數的意象。意象有的宏大,有的具體,但都充滿了自然或者人文歷史內涵。大者如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汴水、泗水、濟水、海河等水系意象,中者如溝池、渡口、橋梁、亭驛、寺廟、隋堤等空間意象,小者如瓊花、淮白、吳粳、鱸魚、官柳等風物意象。經過詩歌的開掘,這些意象日益豐富,由文學意象深化成文化意象,成為運河沿線風景和歷史文化的重要符號。這些意象與詩人們的行旅結合在一起,讓人聯想到大運河之上各種各樣的流動:水的流動、船的流動、物的流動、人的流動,以致情思的流動、生命的流動。大運河古詩詞,抒寫的就是流動的歷史、流動的情懷。細細品味這些詩作中的意象,可以在腦海中組合成一幅大運河的生活圖畫,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大運河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意義。唐代張繼的《楓橋夜泊》,是人人耳熟能詳的詩篇:“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烏啼和鐘聲訴諸聽覺,霜月、江楓和漁火訴諸視覺,這些富含情韻的美妙的意象,只有與大運河的背景結合起來,只有在充滿動感的夜行船中,才會顯得格外美妙。城漸遠,山寺漸近,寂靜中的聲音,時間與空間的切換,很多人的大運河夜航船的行旅經驗都被這首短詩代言了。
再舉一例意象之大者。姚鼐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并不以詩名,但他的《德州浮橋》詩在設喻取象上卻寫得很有特色:“運河繞齊魯,勢若張大弓。隈中抱泰岳,兩蕭垂向東。”“隈”指的是弓把兩邊的彎曲處,“蕭”指弓箭的末段。從地圖上來看,流經齊魯大地的大運河確實形如一張大弓,姚鼐詩句采用鳥瞰視角,連環設喻,不僅形象生動,而且新奇貼切,讀后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姚鼐的詩固然是一篇文學作品,但對于認識大運河的走向,尤其是對于了解大運河山東段的走向特點,卻具有地圖學所不可取代的生動性和形象性。
在詩人眼中,大運河還是一條歷史之河。那些發生在大運河上的史事,也透過詩人之眼,被記錄了下來,成為一種特殊視角、特殊價值的歷史文獻。南宋時代,大運河是宋金使節來往的必經之路。乾道五年(1169),樓鑰隨其舅汪大猷出使金朝,沿途作《北行日錄》,還作詩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他在《泗州道中》詩中寫道:“行役過周地,官儀泣漢民。中原陸沉久,任責豈無人。”目睹陸沉已久的中原故國,聽到遺民追思故國的悲泣之聲,樓鑰哀痛不已。此番運河之行,對樓鑰而言,就是親眼見證家國興亡之旅。差不多百年之后,民族英雄文天祥兵敗被擄北上,在運河道上親歷了亡國的慘痛。因為這些詩人的抒寫,運河成為興亡的見證。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途中往往考察運河漕運以及水利工程。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第四次南巡,途經高郵。當地士人賈國維獻《萬壽無疆詩》《黃淮永奠賦》,大合帝意,被召至沙船,試以《河堤新柳》七律一首,其首聯“官堤楊柳逢時發”,暗含頌圣之意,再次大得康熙歡心,從此被康熙拔擢重用,成為康熙身邊的紅人。乾隆也曾多次南巡,理政余暇,在運河沿線流連風景,留下了不止一首題詠大運河的詩作。清代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曾擔任高郵知州孫蕙的幕僚,協助孫蕙處理河務,并寫過《河堤遠眺》等詩作。對于小說家蒲松齡而言,高郵的這番經歷是他人生難得的一段體驗。按照傳統的詩歌題材分類,大運河古詩詞中最常見的是懷古詠史、羈旅行役、離別送行以及山水游覽等幾類詩。從廣義的角度來講,這些題材類型都與歷史場景相關。大運河所具有的恢宏的時空背景,對于敏感的詩人來說,就是最好的詩料,也為他們的詩作提供了深厚的歷史背景。而這些詩作傳之后世,也融入大運河的歷史之中,成為運河的文化風景。
在詩人眼中,大運河也是一條文化之河,詩人們行走其中,自然也能體會其所蘊藏的中國文化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中,經常以自然界中的事物來比擬人世倫理道德,仁山智水,就是一種以山水比德的說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感慨時光的流逝,強調時不我與、自強不息的努力,這是儒家對于水德的認識。大運河的開鑿、使用和治理的過程,就體現了這樣一種民族文化精神。練湖閘是宋代大運河沿岸重要的水利工程,運河水位較低時,即開閘引湖水濟漕。楊萬里《練湖放閘(其一)》生動地描寫了開閘放水時的壯觀景象,體現了這一工程的浩大及其設計的精巧:“滿耳雷聲動地來,窺窗銀浪打船開。練湖才放一寸水,跳作冰河萬雪堆。”運河的治理,歷來是一項艱巨的工程。清人潘耒在《汴河行為方中丞歐馀作》中,描述清代山東巡撫方大猷(歐馀)率領當地人民治河,廢寢忘食,辛勞投入,十分感人:“公也捧節來治河,赤手與塞滔天波。指揮人徒三十萬,北河柳盡南河柯。大帚如山小如堞,一浪不敵沖風過。晨餐掬泥土,夕眠枕盤渦。以身為石發為草,乃感帝力鞭黿鼉。荊隆口閉神馬塞,汴河南北重蠶麻。”另一方面,正如《荀子》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中國古代學者對于人與自然、君與民、治理與被治理關系的思考。清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十二日,詩人龔自珍行抵淮安清江浦,目睹運河纖夫艱難拉漕船的情形,深有感觸,作《己亥雜詩》第八十三首,其詩云:“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這雖然是一個普通官員的自省,也含有對于“覆舟”的戒惕。往深里說,這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和民胞物與情懷的表現。從這一視角來說,大運河古詩詞可以說展現了中國文化的情懷。
總之,大運河古詩詞是一條詩歌之河。這些詩詞體裁形式多樣,有五七言絕句、五七言律詩、五七言古詩,還有詞作,小令慢詞皆有。本書將詩詞混編,以詩人生卒年先后為序。詞體之中,也不乏柳永、張先、周邦彥等名家之作。例如,周邦彥的《繞佛閣·旅況》就是一首長調慢詞,其題材則是周邦彥最為擅長的羈旅行役之詞。其下片云:“倦客最蕭索,醉倚斜橋穿柳線。還似汴堤、虹梁橫水面。看浪飐春燈,舟下如箭。此行重見。嘆故友難逢,羈思空亂。兩眉愁、向誰舒展。”其表達的精致和婉約,令人遙想北宋時代的人文風貌,即使在大運河路上奔走的倦客,也不失其優雅氣度。
這三百篇歷代詩家詞人們優美的詩作,有如文學獻給大運河的三百顆珍珠。本書試圖將其串成一串項鏈,披掛到大運河身上,也呈獻于讀者的眼前。讓我們一起沿著古典斑斕的詩句,沿著時間這條“逝者如斯”的流水,走進“萬古流不絕”的大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