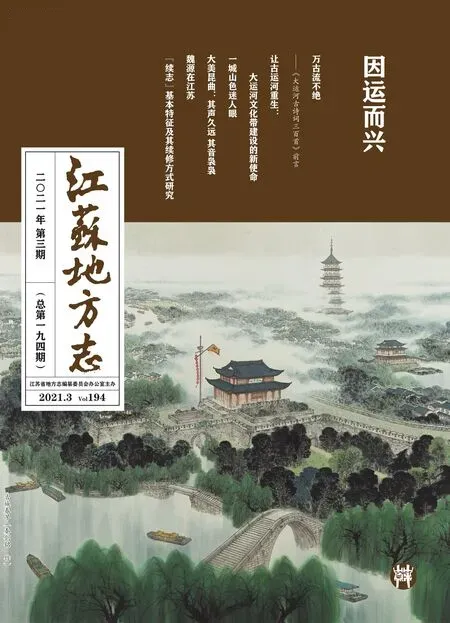近三十年來伍子胥研究綜述
◎陳 宇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南京 210002)
伍子胥是春秋晚期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其事跡傳說流傳至今,“伍子胥傳說”先后入選揚州、蘇州等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江蘇地區還保留著豐富的關于伍子胥的史料記載和歷史遺跡,比如淮安邗溝、宿遷伍家溝和斬龍墩、蘇州胥門等。伍子胥一生事跡悲壯,且富有爭議,從孔子、屈原、司馬遷開始,評價已有褒貶之別,這一爭論經過后世稗官野史、戲曲小說的編造渲染,引發了經久不息的關注和議論。筆者對近三十年伍子胥及其有關問題研究情況略作梳理,或有裨于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與利用。
一、伍子胥思想研究
伍子胥是司馬遷筆下一位個性鮮明、性格復雜的歷史人物,其思想觀念對后世的政治、軍事等多方面都有比較深遠的影響。王洪強《伍子胥思想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9 年學位論文)指出“伍子胥治國理政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具體表現在推行德政、遵循天道、保民無饑三方面,又以德政最為重要。伍子胥認為發動戰爭要選擇時機,首先是自己要做到安民利民,其次是只可攻擊無德之國,如他在勸諫夫差釋齊滅越時,對楚靈王、勾踐和夫差三人對待民眾的態度進行了評判,充分論證了德政對于國家安危存亡的重要性。
伍子胥的忠孝觀也是其政治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王洪強、王玉德在《伍子胥與屈原比較二題》(《求索》,2012 年第1 期)一文明確指出,“伍尚(伍子胥的哥哥)的‘孝’是約束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的‘孝’,而伍子胥的‘孝’是基于原始血親復仇觀念下的‘孝’”“伍子胥之忠,不是忠于君,而是忠于國;不是忠于鄉國,而是忠于君國”。伍子胥的復仇和忠諫,既表達了臣下對君主的忠心,也體現了家族對君主行為的道德約束。先秦諸子各取其一面,塑造了他們心目中的愛國者和成功者形象,因此歷來評論多有爭議。
伍子胥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軍事謀略家之一,對其軍事思想的研究出現很多成果。楊范中《從吳楚戰爭看伍員的軍事思想》(《江漢論壇》,1984 年第7 期)指出伍子胥“以破楚為首務”的謀略思想,并詳細介紹了伍子胥分師擾敵疲敵、遠道迂回奇襲等奇譎機變的作戰方法及謀劃全局、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徐勇、黃樸民《關于伍子胥軍事思想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3 期)從戰略目標的制定、攻楚戰略方針的實施等方面探討伍子胥的軍事思想。1983年,湖北省江陵漢墓出土了一批西漢竹簡,其中有一部記載伍子胥軍事思想的兵書《蓋廬》。它的出現,有利于學者加深對伍子胥軍事思想的認識,如田旭東《新公布的竹簡兵書——<蓋廬>》(《中華文化論壇》,2003 年第3 期)對《蓋廬》中“以方向定吉兇的擇日之術”和“五行相勝之術”的兵陰陽思想進行了初步探討。
除此之外,對于伍子胥事跡的考辨、評論甚至翻案文章也有部分研究者涉足。張君《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認為伍子胥未曾對死去的楚平王掘墓鞭尸,也未鞭墳泄憤,甚至連破郢之戰都未參加,這一記載是后人“鑿空捏造”。主要理由是:與伍子胥同時代的孔子在言論著作中都沒有提及;《左傳》也未提及鞭墳、鞭尸事;屈原稱贊并自擬于伍子胥;《公羊傳》明確記載了伍子胥忠君、不報私仇的言論。倉林忠《關于伍子胥有否對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辨析》
(《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10期)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春秋谷梁傳》《呂氏春秋》已明確記載伍子胥鞭墳或鞭尸的史事;伍子胥個性剛烈,強烈的復仇愿望使他有掘墓鞭尸的可能;我國歷史上長期存在掘墓、辱尸的惡俗。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完善。
二、伍子胥形象研究
伍子胥形象最早出現在《左傳》《國語》中。編年體史書《左傳》主要記其事,有6 處。國別體史書《國語》主要載其言,有第十九卷“吳語”和第二十卷“越語上”2處。這些記載,附屬其他史事,分散于各年,人物的言行事跡也多分散記錄在事件發生的各個年代。將這些不同年代的人物事跡聯系起來,約略可見伍子胥是個有堅韌性格(計不從而獻士退耕待時機)、過人謀略(拖疲戰術和預見越將滅吳)、忠貞精神(屢次進諫)的歷史人物。
關于戰國諸子散文中的伍子胥形象,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4 年學位論文)指出,伍子胥形象在《韓非子》《呂氏春秋》中逐漸明朗。如后者首增伍子胥射王宮,鞭墳復仇,提及人物外貌,“見之而惡其貌”。在此,人物善謀(激楚換子常),敏捷機智(應對邊侯,用計見公子光及吳王),善理政事(練兵強吳),知恩圖報(解劍酬漁人),性格逐漸豐富。
司馬遷在描寫伍子胥父兄被害以及伍子胥引吳兵入郢的事件中,增加了兩個情節。其一,增加了伍子胥逃往吳國時,一路歷經磨難、備嘗艱辛的情節,如昭關遇漁父、未及吳國患病等;其二,鞭尸的描寫。這些都是《左傳》中所沒有記載的。許多學者都撰文分析這種再創作現象,認為《史記·伍子胥列傳》中增加的細節描寫,體現了伍子胥為復仇忍受的苦難和艱辛,為塑造伍子胥忍辱負重、不屈抗爭的烈夫形象增添了重要一筆。
東漢《吳越春秋》中的伍子胥是蒙垢忍恥、堅忍不拔的烈丈夫,也是上稽天時、下測物變的神知之士。曹林娣《論<吳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中國文學研究》,2003 年第3 期)認為《吳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形象塑造,具有空前性和原創性:作者將歷史上一員練兵戰將,通過對史料的踵事增華和民間傳說的融化,運用旁見側出、對比烘染等多側面的描寫手法,塑造成一位文武雙全、忠孝節烈集于一身的神化英雄,成為后世伍子胥藝術形象的范本。
唐代的《伍子胥變文》譜敘了伍子胥大半世的榮辱浮沉和生死離別,題材上沒有脫離歷史的重大背景。單芳《<伍子胥變文>與<伍員吹簫>雜劇比較》(《敦煌研究》,2008 年第5 期)認為變文中塑造的伍子胥形象心情凄苦、態度謙卑、陰柔內斂、悲觀消極,但又有神秘感和傳奇色彩,如伍子胥兩外甥想捉舅父去領賞,伍子胥用法術掩護自身。
元明時期的伍子胥形象主要出現在戲曲舞臺上,高云萍的學位論文將現有可考的元明史劇按內容分為四個系列:臨潼斗寶系列、棄楚亡吳系列、鞭尸復仇系列、報吳身亡系列。臨潼斗寶系列展示了伍子胥少年豪俠的英雄形象,棄楚亡吳、鞭尸復仇系列展示了伍子胥復仇志業的悲劇形象,報吳身亡系列則塑造了一位耿直剛勇的老臣形象。元雜劇《伍員吹簫》歷時較短,只寫到伍子胥報仇,吳王闔閭即位,劇本的主題主要是復仇,其次是報恩。單芳認為雜劇中的伍子胥堅貞剛烈、不屈不撓,給觀眾以信心和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著名作家馮至曾創作過一篇詩化小說《伍子胥》,以伍子胥選擇“棄楚、奔吳、復仇”即“奧德賽”式的心路歷程為寫作內容,糅雜了東西方文化、現代性文化及作者自己的獨特感悟,因此,伍子胥形象研究中亦有一部分是圍繞馮至筆下伍子胥形象的現代文化內涵展開討論的。

蘇州伍子胥紀念園所立伍子胥像(陳宇 供圖)
三、伍子胥故事流變研究
關于伍子胥故事的來源,早在1927年鄭振鐸《伍子胥與伍云召》就已進行了區分:一種是《史記》《吳越春秋》《新列國志》,皆有實有據;另一種是元曲及《列國志傳》《伍子胥變文》等多采錄無根據的民間傳說,如“鞭伏盜跖”“臨潼斗寶”等。黃亞平《伍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003 年第2 期)將伍子胥故事分成兩大系統:史傳系統和民間系統。史傳系統由早期傳說到《左傳》《公羊傳》《呂氏春秋》,再到《史記》,再至《吳越春秋》《越絕書》,再至《太平御覽》《高士傳》《琴操》;民間系統是從《吳越春秋》《越絕書》到變文再到元雜劇、明雜劇、《說唐傳》以至現代京劇《文昭關》。
對司馬遷《史記·伍子胥列傳》在伍子胥故事的發展演變中起到的作用,李曉一《〈史記·伍子胥列傳〉復仇觀的價值特點》(《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認為司馬遷對伍子胥故事進行了清晰獨立的文學加工,集中在單篇傳記《伍子胥列傳》中,在《吳太伯世家》《楚世家》《范雎蔡澤列傳》中又有補充,使得伍子胥故事初步完整。又通過吸收《韓非子》《呂氏春秋》對伍子胥事跡的加工手法,在內容上有所增刪,有強烈的文學加工痕跡,使《伍子胥列傳》更具有可讀性。
伍子胥故事的定型完成在東漢時期,實現了伍子胥故事由歷史文獻向文學文本的過渡。劉青《先秦兩漢史籍中伍子胥復仇故事研究》(吉林大學,2018年學位論文)指出《左傳》《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史籍中伍子胥復仇故事結構上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動,細節卻隨著時間不斷被增添,而一些遠離伍子胥這一核心人物之外的內容被剝蝕掉。孫瑩瑩《從歷史到傳說——先秦兩漢伍子胥故事的流變》(北京大學,2008年學位論文)指出《越絕書》載伍子胥死后成神,發展了《左傳》吳王“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這一事跡,用離奇、虛幻的浪漫主義手法為伍子胥故事增添了新的結尾。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4年學位論文)進一步分析,《越絕書》中伍子胥故事的復仇力度明顯降低,儒家中庸、理性、忠君說教增強,因這一渲染,人物性格更加豐富,形象更加豐滿,故事本身也含更多主題。
高云萍的學位論文認為伍子胥故事在《吳越春秋》中完全故事化,獲得了基本定型。伍子胥故事中“起因—逃亡—積蓄—復仇—報恩—賜死”等每個環節在《吳越春秋》中敘述均詳細分明,故事生動且獨立清晰,情節完整。后世的文學文本,無論是唐代的《伍子胥變文》,宋代詩詞對伍故事的用典,還是元曲《伍員吹簫》等,都沒有逃離這些基本情節,只是不同程度不同環節的故事想象放大,依體裁需要而有所增添。《吳越春秋》的傳奇色彩使伍子胥故事更深入民間,伍子胥成了民間特別是吳越地區人們的重要祭祀對象和吳越文化的組成部分。
六朝以后伍子胥的故事仍然深入人心,在隋唐詩文中也對伍子胥故事做了歌詠或用典。龔敏《唐詩中的伍子胥信仰與傳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1 期)以唐代文學中的詩歌為主,就伍子胥及其相關之信仰與傳說(伍子胥廟、錢塘江濤、羅剎石),做了更深層次的探討。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陸龜蒙等人詩文中都有對伍事的用典。伍子胥故事的流傳和接受越來越廣,民間大眾對此青睞有加,因而引起了載體的變化,即出現文本敦煌變文《伍子胥變文》。經過王重民、潘重規、張涌泉等學者校勘注釋,該篇變文中的疑誤之處已漸趨消除殆盡。彭慧《〈伍子胥變文〉校注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0 年第5 期)在參照寫卷的基礎上,就“不免此處生留難”等21處文字的形義問題進行探討。
20 世紀初敦煌發現《伍子胥變文》文獻資料,所以關于伍子胥變文的學術研究相當多,無論是文本分析、文獻考證還是思想分析、佛教影響都很豐富。變文最初是僧徒演說佛經的文本,有僧講、俗講之分。前者限于法門的聽眾而枯燥干澀,后者面向法門外的善男信女,內容通俗化、故事化,題材多樣,影響較大。《伍子胥變文》僅是通過選取其中的子胥奔吳、助吳伐楚、忠諫被殺這三個事件來展開情節。李騫在《敦煌變文話本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 年)一書中認為《伍子胥變文》處處宣揚儒家的“天人感應”“孝道”“勸善懲惡”思想,又深刻地受到儒、佛兩種思想交融的影響。黎聰《論〈伍子胥變文〉中的儒佛交融》(《語文學刊》,2009 年第8 期)提出變文中的楚平王、楚昭王、魏陵、子安、子永、鄭王正是由于心存邪念,作惡多端而受到殘酷的報應。相反的,漁夫、浣紗女等不惜一切代價來幫助伍子胥復仇的人都得到了應有之善報。佛教的報應論摧毀了人們的僥幸心理,收到的是與儒家的“勸善懲惡”同樣的效果,也使它能夠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兩者相資互補,不可或缺。
黃亞平《伍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003 年第2期)認為變文汲取了佛教故事變文盛行時關于真實和幻想的觀念改寫歷史,其對重大史實的改寫程度遠遠超過了同類題材的漢代雜史小說《越絕書》《吳越春秋》。李明《<伍子胥變文>的文化內涵》(《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5 年第2 期)提出《伍子胥變文》通過在史事的框架內加了一些新奇、怪誕的情節片段,以有血有肉的人間性反過來改寫變文的宗教色彩,把變文帶入更為豐富的世俗層面,體現著恩恩怨怨的復雜情感,散發著生死榮枯的悲涼情調。
明崇禎中馮夢龍重輯本《新列國志》,其中在對之前的伍子胥故事整理、總結的基礎上,加進編者的思維成果,因為情節更加完整、清晰,故事曲折、跌宕生姿,更富有傳奇色彩。黃智詠《“伍子胥故事”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接受》(北京大學,2014 年學位論文)指出《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這些文獻將伍子胥故事傳播到了朝鮮半島,經過李朝文人的翻譯和改寫的《伍子胥實紀》(玄公廉著,大昌書院,活字本,上下兩卷,1918 年10 月),成了李朝末期和開成期的通俗小說。
龔敏《唐詩中的伍子胥信仰與傳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認為伍子胥故事的發展,約略可以分為雅、俗文學兩條脈絡,一條是文人記錄,吟詠的史傳文學、詩歌、古文等雅文學;另一條則是流傳在民間的信仰、地名、風物等俗文學。域外漢學家宇文所安《敘事的內驅力》(《他山的石頭記 宇文所安自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6月),以伍子胥傳奇故事為例,論述中國上古時期敘事的“內驅力”,重點在于史傳傳說敘事故事體中內在結構的演變。域外漢學家姜士彬《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一)(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3年第7期、第9期),提出伍子胥故事的變異發展取決于接受者,民間群眾和文士精英始終各自掌握著不同的知識,這一思路對分析不同文類里的伍子胥意象之演變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伍子胥信仰研究
伍子胥對吳國的霸業和吳地的開發作出了莫大的貢獻,最終忠諫屈死。千百年來,伍子胥受到人們無限的敬仰,死后還被奉為神明來祭祀。
蔣康《試論伍子胥的崇祀習俗》(《蘇州大學學報》,1995 年第4 期)指出伍子胥從人到神,受到人們特別是吳越地區人民崇敬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伍子胥生前對吳地開發的杰出貢獻,如造闔閭大城,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對吳國的迅速崛起以及爭霸事業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開鑿的我國歷史上第一條人工運河胥溪,成為蘇州經太湖西通長江的重要航道。伍子胥對吳地的杰出貢獻和個人的悲慘遭遇,贏得了人們極大的同情和深深的敬仰。梅迪《論端午節及其文化》(華中科技大學,2012 年學位論文)指出蘇州當地許多地名均與伍子胥有關,如胥門、伍相公弄、胥山、胥口、胥江、胥溪。在統治階級的提倡下,伍子胥的祭祀地域已大大地超過了原先的吳越一帶,信仰轉盛,不僅擴大到揚州,而且在荊楚以西,甚至安徽、福建、廣州等地也遍立子胥廟,東漢王充《論衡》記載:“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
伍子胥個人的品質和情操也是他受到民間廣泛崇祀的原因之一。孝和忠是古代倫理規范中最重要的兩個范疇,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升華,伍子胥可謂忠孝兩全。戈春源《端午節起源于伍子胥考》(《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4 期)分析伍子胥首先是個孝子,避禍復仇,棄小義,雪大恥,在攻下郢都后,將楚王掘墓鞭尸。在后人看來,雖然頗為過分,但在當時中國這個極度重視血緣宗法關系的國家里,孝仍以它最富人情味的特征贏得社會最普遍的認同。其次,伍子胥忠言直諫,而直諫本身就是忠,而且是一種更真誠的忠。最終以諫勸夫差停止伐齊而被賜死,對吳國及國君表達極大的忠誠。
關于端午節由紀念伍子胥轉為紀念屈原的原因,戈春源《從屈原與伍子胥的關系看端午節的起源》(《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2 期)認為伍子胥的故事,代代相傳,而且日益豐富;屈原則以其作品中的情感影響著后代。伍子胥和屈原的書寫,有著不同的著眼點,一則在故事,一則在情感。前者更多地打動普通百姓,后者更多地打動文人騷客。百姓關注的是情節,要求快意恩仇;文人騷客關注的是精神與情感,注重的是高潔與不群。這就奠定了伍子胥和屈原在后代傳承中不同的走向和趨勢。富世平《伍子胥、屈原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的不同書寫及其對端午習俗的影響》(《中國俗文化研究》第八輯,2013 年)指出原本都以“忠貞”著稱的伍子胥和屈原,在后代有了不同的身份標識——伍子胥是痛快淋漓的復仇,屈原則是“九死其猶未悔”的忠貞。創作文學作品時的文人,無論實際的處境怎樣,大都具有懷才不遇之感,這使得他們在情感上對屈原有著深深的認同。而當屈原和端午在一定的地域聯系在一起之后,便迅速被他們接受,在大多數的文學作品中,確立了端午和屈原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不同的標識,不僅影響了兩人在正統社會的地位,而且在端午民俗活動中,也有了大不相同的遭遇——作為端午祭祀的對象,時間上更早的伍子胥始終局限在吳越一帶;而后來者屈原,卻從荊楚出發,走向了大江南北,成了端午節的代言人。宋亦簫、劉琴《端午節俗起源新探》(《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2 期)也認為早期文獻中不同的書寫方式以及不同書寫方式所體現的兩人在當時的不同境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