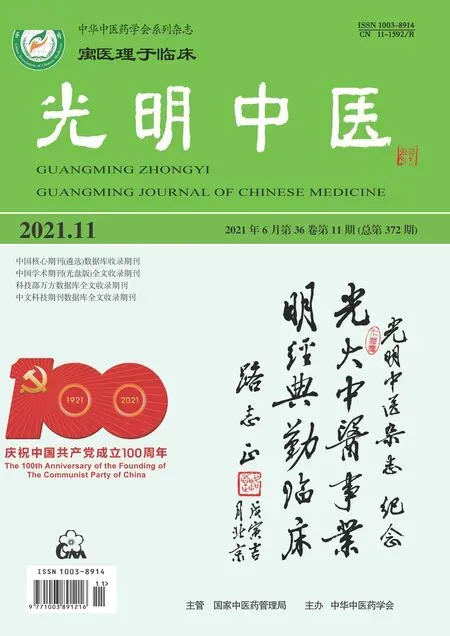基于藥物功效的小青龍湯組方分析*
孟 菲 張 丹
小青龍湯為千古名方,記載于多部古方典籍中,現代也被廣泛地應用于呼吸系統疾病中,如支氣管哮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肺心病等。但小青龍湯在多部古方典籍中組方卻不完全相同,各藥味的炮制品種選擇尚有爭議,不利于后世繼承和發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為古代經典名方的復方制劑提供了便利條件和法律依據,故從經典名方的傳承和制劑開發來說,小青龍湯組方研究也應是研究的基礎。故作者基于以上考慮,從小青龍湯的病機、組方原理、藥物功效等方面對其組方進行分析,以期明確其組方,為后期研究奠定基礎。
1 小青龍湯介紹
小青龍湯始載于《傷寒論》,由“麻黃(去節) 芍藥 細辛、干姜、甘草(炙)、桂枝(去皮)各三兩,五味子半升,半夏(洗)半升”組成。其總的病機特點為內有水飲宿疾,又外感寒邪,外邪引動內疾出現外寒內飲、內外皆實的病癥;其辨證要點為惡寒發熱、無汗、喘咳、咳白色稀痰、苔白滑、脈浮;主治外寒里飲證。方中麻黃、桂枝相須為君,發汗散寒以解表,麻黃又宣發肺氣以平喘,桂枝助陽化氣以解里飲;干姜、細辛為臣,溫肺化飲,亦助麻、桂祛表邪;五味子斂肺止咳,芍藥和營養血,二藥可增強止咳平喘之功,又可制約辛散溫燥之藥傷陰,還可避免耗傷肺氣太過;半夏化痰、降逆為佐藥;甘草為佐使藥,益氣調中,調和諸藥。全方體現其“宣收相濟,升降兼施,陰陽平調”的獨特功效和適應病證廣泛的主治特點[1]。
2 不同典籍中小青龍湯的比較
各古籍中小青龍湯組方比較可見各古籍所載方劑組分及炮制品均有所差異。見表1。

表1 各古籍中小青龍湯組方比較
3 小青龍湯藥物組成分析
3.1 麻黃《傷寒論》中記載麻黃炮制方法為去節,而其他幾部古籍記載麻黃的炮制方法為去節、去根,現代研究表明麻黃根有斂汗的作用,與本方功能主治不符,因此其炮制方法應為去根節,與現代麻黃(2020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的炮制方法相同。其現代的炮制品有麻黃、麻黃絨、蜜麻黃、蜜麻黃絨。麻黃發汗解表和利水消腫力強;蜜麻黃性溫偏潤,辛散發汗緩和,以宣肺平喘力勝;麻黃絨作用緩和,適用于老人、幼兒及虛人的風寒感冒,其用法與麻黃相似;蜜麻黃絨作用更加緩和,適用于表證已解而咳喘未愈的老人、幼兒及體虛患者。因此;若外寒重,建議使用生品,即麻黃以發散外邪,若表證輕者,建議選用蜜制之品。
3.2 桂枝、桂心、肉桂《太平圣惠方》載桂心,其他幾部載肉桂、桂枝。《太平圣惠方》為收集唐代《千金方》《外臺秘要方》之后,而流傳下來,而《外臺秘要》中的“桂心”, 即現在常用的肉桂[2]。桂枝味辛、甘, 性溫, 歸心、肺、膀胱經, 功效發汗解肌、溫通經脈、助陽化氣。肉桂味辛、甘, 性大熱, 歸腎、脾、心、肝經, 功效補火助陽、引火歸原、散寒止痛、溫經通脈。李東垣在《珍珠囊補遺藥性賦》中寫道:“桂,味辛性熱有毒。浮也, 陽中之陽也。氣之薄者, 桂枝也, 氣之厚者肉桂也。氣薄則發泄, 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 肉桂下行而補腎。此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3]。桂枝與肉桂對比, 桂枝氣薄其性質趨向于外、向上, 溫通陽氣之力勝, 常用于陽氣不得外達之證;肉桂氣濃而趨向于內、向下, 溫補陽氣之力勝, 常用于下元虛寒之證[4]。《景岳全書·傳忠錄》云:“氣味之動靜:靜者守而動者走。走者可行, 守者可安”[5]。桂枝與肉桂相較, 桂枝走而不守, 偏于動藥, 肉桂守而不走, 偏于靜藥[4]。 肉桂味甘,性大熱,氣厚味純,守而不走,溫補之效強;桂枝辛甘溫, 氣薄升浮, 走而不守,溫通之力勝。《傷寒論》中第40條載:“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載小青龍湯治形寒飲冷,內傷肺經,咳嗽喘急,嘔吐涎沫。綜合以上二本古籍小青龍湯條文,其主治外寒內飲,病機為心下胃脘部素有水飲內停,又外感表邪,外寒引動內飲,若不疏表而徒治其飲,則表邪難解;不化飲而專散表邪,則水飲不除[6]。故宜治法為解表與化飲配合而表里雙解。因此從病機的角度考慮更應該選擇解表、溫通助陽化氣的桂枝, 而不是偏于溫補的肉桂。桂枝現代的炮制品主要有桂枝、蜜桂枝。本品以生用為主,生品桂枝辛散溫通作用較強,蜜桂枝辛通作用減弱,長于溫中補虛。因此建議本方選用生品更為恰當。
3.3 干姜干姜,《傷寒論》及《方劑學》選用干姜,而其他三部選用干姜(炮),從功效看干姜味辛性熱,能守能走,故對于寒飲伏肺的咳喘頗為適宜,而炮姜則長于溫中止痛、止瀉、止血,因此本方干姜更為適宜。
3.4 細辛細辛,《奇效良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要求細辛去葉入藥,其他三部則并未明晰該藥味的炮制要求,細辛是馬兜鈴科植物,很長時間都以全草入藥,一般以地上部分占比較多。鑒于馬兜鈴酸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于2000年把細辛的入藥部位由全草改為根和根莖,現如今細辛以根及根莖入藥。
3.5 五味子五味子,各部古籍并未對五味子炮制品選擇做特別的標注,宋代有去梗(《總病論》)、酒浸(《局方》)、蜜蒸(《證類》)等法,現在的主要有五味子、醋五味子、酒五味子、蜜五味子。五味子生品以斂肺止咳止汗為主;而醋制之后酸澀之性增強,澀精止瀉作用增強;酒制后益腎固精作用增強;蜜制后補益肺腎作用增強。根據本方的組方原則,故應選生品以取其收斂肺氣之性更為適宜。
3.6 白芍、赤芍漢末之前尚未有赤芍、白芍之分,梁朝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最早出現將芍藥分為赤芍與白芍[7]。《本草經疏》亦曰:“芍藥,《圖經本草》載有兩種,金芍藥色白,木芍藥色赤。赤者利小便散血,白色止痛下氣,赤行血,白補血,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酸以收之,甘以緩之,甘酸相合用,補陰血通氣而除肺燥”[7]。宋代時期,用白芍重在緩急止痛,活血養血,健脾和中之功;用赤芍則重在清熱涼血,“利小便,下氣”,大大豐富了芍藥的功效主治,補前人之未及[8]。金代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中寫到:“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此后,歷代醫家開始正式將赤白芍分開記述[9]。2015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認為,白芍:苦、酸,微寒,歸肝、脾經。養血調經,斂陰止汗,柔肝止痛,平抑肝陽。用于血虛萎黃,月經不調,自汗,盜汗,脅痛,腹痛,四肢攣痛,頭痛眩暈;赤芍:苦,微寒。歸肝經,清熱涼血,散瘀止痛。用于熱入營血,溫毒發斑,吐血衄血,目赤腫痛,肝郁脅痛,經閉痛經,癥瘕腹痛,跌撲損傷,癰腫瘡瘍。熊曼琪教授主編的《傷寒論》一書中對小青龍湯芍藥方義解釋,認為“桂枝與芍藥相配,調和營衛”[10]。鄧中甲主編的《方劑學》對其的釋義為芍藥和營養血,與辛散之品相配,既可增強止咳平喘之功,又可制約諸藥辛散溫燥太過之弊[11]。《古今名醫方論》云:“溢飲之證,《金匱》云當發其汗,小青龍湯治之。蓋水飲溢出于表,營衛盡為之不利,必仿傷寒營衛兩傷之法,發汗以散其水,而后營衛行,經脈通,則四肢之水亦消,必以小青龍為第一義也”[12],所以釋義亦為取芍藥和營之意。綜合方解芍藥的釋義結合赤芍、白芍的功用,當選調和營血、酸甘化陰的白芍,而非性散、重在清熱涼血的赤芍。白芍現代炮制品種類較多,如白芍、酒白芍、炒白芍、醋白芍、土炒白芍。白芍性微寒,瀉肝火、養陰除煩,多用于肝陽上亢、陰虛發熱等酒炙后其酸寒伐肝之性降低,入血分,善調經血、柔肝止痛;醋炙后引藥入肝,斂血養血、疏肝解郁作用增強;土炒后入脾,增強養血和脾、止瀉作用;炒白芍寒性緩和,以養血和營、斂陰止汗為主。因此建議本方選用炒白芍,取其斂陰和營之功,更為合適。
3.7 半夏半夏因其生品有毒,古籍記載亦是湯洗后入藥,半夏的炮制方法最早可見于《金匱玉函經》,其中寫到“不咀,以湯洗十數度,令水清滑盡,洗不熟有毒也”[13]。現今半夏多以加輔料炮制入藥,如法半夏、清半夏、姜半夏、半夏曲。法半夏偏祛寒痰,亦具有調和脾胃的作用;姜半夏增強了降逆止嘔作用;清半夏長于化痰,以燥濕化痰為主。因此,若痰多又兼脾胃不和,法半夏更為適宜,痰飲嘔吐姜半夏更為適宜,濕痰咳嗽則清半夏更符合。依據原方注釋及半夏炮制品功效,應選擇姜半夏為宜。
3.8 甘草研究表明,張仲景時期原書中所用炙甘草為今天的炒甘草[14]。現代甘草炮制品有蜜甘草、炒甘草。甘草,味甘,偏涼,長于瀉火解毒,化痰止咳;蜜甘草甘溫,蜜炙甘草后有甘緩、甘壅、膩滯斂邪及滑腸等弊端[15],而長于補益、緩急止痛;甘草經炒制后其涼性去而溫性存,既能補中焦脾土而不傷,又有甘緩而不滯之性,實為健脾補虛溫中佳品[16]。因此炒甘草更契合方中病機特點。
4 小結
本文通過對比幾部典籍中組方藥味差異,中藥性味歸經及主治功效,結合病因病機和中藥飲片處方用名確定其藥味組成,應為麻黃、炒白芍、細辛、干姜、炒甘草、桂枝、五味子、姜半夏,更為貼合本方主治病癥。
本文對本方8味中藥飲片的常用炮制品及其功效進行總結,由于炮制方法的不同,其炮制品的化學成分發生變化,其功效亦有偏頗,因此炮制品選擇應以辨證論治為前提,針對一定的病因、病機,根據不同人群不同兼證,選用不同的炮制品種,體現“飲片入藥, 生熟異治”的中醫用藥特色優勢[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