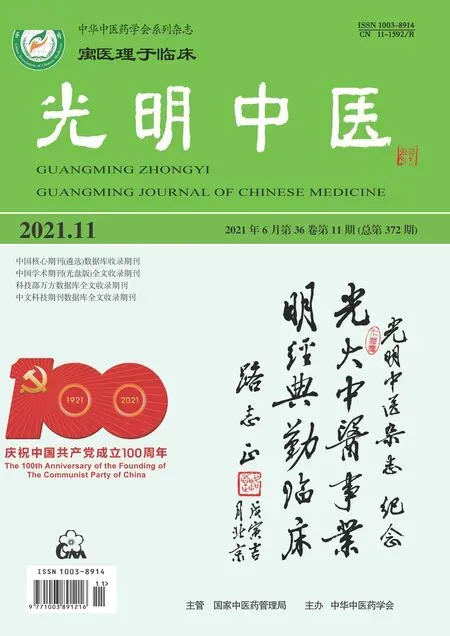補腎活血調周聯合艾灸治療原發性痛經40例
陸嬋麗 梁玉蓮 劉桂英 何麗亞
痛經在中醫學屬于“經行腹痛”范疇,是指女性在月經期或月經期前后出現周期性的下腹部疼痛、墜脹,或伴有腰骶部酸脹疼痛等不適,嚴重者可出現惡心嘔吐、大汗淋漓、面色蒼白,甚至暈厥等,以致影響工作、學習和生活[1]。在西醫學痛經有原發性痛經和繼發性痛經之分,其中原發性痛經又被稱為功能性痛經,指的是痛經的發生原因非因生殖器官和盆腔等器質性病變所致。目前西醫對于原發性痛經的病因病機尚未完全明確,也無能徹底治療該病的治療方法,主要采取解痙止痛等對癥治療為主,雖在當時能取得一定療效,但不能根治,停藥后會反復,且存在胃腸道不良反應以及易成癮等不良作用。相比較而言,中醫治療原發性痛經雖然見效慢,但療效可靠,不易反復,且安全無不良作用。本研究將中藥補腎調周法聯合艾灸治療原發性痛經患者,取得滿意的療效。現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收集2016年12月—2019年10月前來肇慶市中醫院婦產科門診求治的80例原發性痛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將所有患者按照不同隨機分為2組。其中觀察組40例,對照組40例。觀察組年齡14~28歲,平均年齡(17.5±3.4)歲;病程1~11年,平均病程為(4.62±0.73)年;有性生活史者12例,無性生活史者28例。對照組年齡15~29歲,平均年齡(16.81±2.21)歲;病程2~10年,平均病程為(3.95±0.62)年;有性生活史者10例,無性生活史者30例。全部遵循醫學倫理學原則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經統計學分析比較,2組患者的年齡、病程、性生活狀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1)經B超和婦科檢查排除盆腔和生殖器官的器質性病變;(2)于月經前后或者月經期周期性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腹部疼痛,可同時伴有下腹墜脹、腰骶酸痛、頭暈乏力、四肢不溫、大汗淋漓、惡心嘔吐、腹瀉等癥狀[1]。
1.2.2 中醫診斷標準婦女在經行前后1周以內或者經期出現以周期性下腹疼痛為主癥,并且伴有其他不適,以致影響工作及生活者[2]。
1.2.3 腎虛血瘀證的中醫辨證標準(1)主癥:經期或經期前后出現周期性小腹疼痛,溫熱后可緩解;(2)次癥:①月經量中或量少、質稀,經色黯淡、或伴有血塊;②腰膝酸軟;③頭暈耳鳴;④夜尿頻數或者小便清長;⑤面色晦暗。(3)舌脈:舌質黯淡、有瘀點或瘀斑,苔薄白,脈沉、細或澀。上述主癥為必備,次癥具備2項或以上,結合舌象、脈象,即可確定證型[3]。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1)年齡介于12~30歲;(2)同時符合以上中、西醫診斷標準;(3)自愿參加本次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需同時符合以上3項的患者,方可以納入本研究。排除標準:(1)B超或者婦科檢查發現同時合并有其他引起痛經的器質性病變;(2)對本研究所用治療藥物過敏者;(3)同時合并有心、肺、腦、肝、腎等嚴重內科疾病或者精神性疾病;(4)因治療的依從性差而影響療效判斷者。
1.4 治療方法試驗組:予以艾灸聯合中藥補腎調周治療。艾灸治療:取穴足三里、三陰交、關元,患者取仰臥位,點燃艾條后對準穴位距離以皮膚能耐受為度施以溫和灸,每次施灸30 min,每日1次,于經期前7 d開始,灸至月經來潮止,連續治療3個月經周期。中藥補腎活血調周治療:基礎方:菟絲子30 g,山萸肉15 g,熟地黃20 g,當歸10 g,川芎10 g,赤芍10 g,白芍20 g,香附10,炙甘草6 g。月經期加用枳殼10 g,延胡索15 g,五靈脂10 g,烏藥10 g,肉桂5 g,牛膝10 g桃仁10 g;經后期加杜仲10 g,黃精10 g,女貞子10 g,枸杞子15 g,續斷20 g,鹿角膠10 g;經間期加皂角刺10 g,澤蘭20 g,杜仲10 g,續斷10 g,巴戟天15 g,紫石英15 g,丹參15 g;經前期加仙茅10 g,牛膝15 g,杜仲10 g,桑寄生15 g,淫羊藿15 g,玫瑰花10 g。每日1劑,連續治療3個月經周期。對照組:予以口服布洛芬緩釋膠囊治療(0.3 g/粒,中美天津史克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00089)。于痛經發作時立即開始服用,每次口服1粒(0.3 g),每天服用2次,至痛經癥狀完全緩解停藥。
1.5 觀察指標觀察治療前后的經期腹痛情況并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和《中藥治療痛經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相關痛經癥狀評分標準進行評分[3,4]。觀察治療前后的中醫臨床癥狀,并計算中醫癥狀評分。
1.6 療效判定標準將綜合療效分為痊愈、顯效、有效、好轉4種情況[3]。具體如下:痊愈:治療后痛經癥狀評分降為0分,腹痛和其他癥狀消失,且停藥后3個月經周期未復發者;顯效:治療后痛經癥狀評分較前減少50%以上,腹痛和其他癥狀明顯緩解,停藥后正常工作和生活不受影響者;有效:治療后痛經癥狀評分較前減少25%~50%,腹痛和其他癥狀略有緩解,經期需服用藥物治療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者;無效:痛經和其他癥狀均無改善。

2 結果
2.1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治療結束后,觀察組患者總有效率95.0%,對照組患者總有效率77.5%,2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165,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2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2組治療后的中醫證候積分均較治療前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2組均能不同程度改善相關臨床癥狀;研究組治療后的中醫證候積分低于對照組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同對照組相比較,研究組在改善相關臨床癥狀方面具有更好的療效。見表2。

表2 2組患者治療前后的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例,
2.3 2組患者治療前后的痛經癥狀積分比較與本組治療前比較,2組患者治療后痛經癥狀評分均明顯降低(P<0.05);治療后,觀察組患者痛經癥狀評分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治療前后的痛經癥狀積分比較 (例,
2.4 2組患者復發情況比較3個月后隨訪,觀察組有效患者中4例復發,復發率為10.5%;對照組有效患者中復發29例,復發率為93.5%。經統計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159,P<0.01)。
3 討論
原發性痛經在婦科臨床極為常見,該病多見于15~25 歲的年輕女性[5]。有關數據統計顯示,女性中約74%有過不同程度的痛經經歷,近些年來該病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而治療的緩解率卻呈下降趨勢[6]。由于痛經的高發病率和對女性生活的干擾,現代醫學對于原發痛經的發病機理和臨床治療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目前對于原發性痛經的具體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且無確切有效的根本性治療方法。目前的研究大多認為原發性痛經的發生與月經來潮時子宮內膜內前列腺素的含量增多密切相關[7],也有研究認為其發生與血管加壓素、催產素、環氧化酶、雌孕激素、內皮素等內分泌因素相關[8-11]。此外,子宮發育不良或者過度屈曲、子宮內膜管型脫落也可能導致痛經的發生,而神經、精神因素、飲食因素和遺傳因素等都可能是導致痛經的誘因[12,13]。現代醫學目前尚無理想的方法能夠根治原發性痛經,目前痛經發作時采取對癥治療為主。常用的藥物主要包括非甾體抗炎藥、解痙劑、鈣離子拮抗劑、鎮靜劑、抑制排卵藥物、維生素類等,其中以非甾體抗炎藥最為常用[7],該藥屬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劑,通過阻斷環氧化酶來減少前列腺素的合成,抑制子宮的收縮,使子宮的張力減少,從而緩解疼痛,據研究報道該藥止痛的有效率為75%~80%[14]。該藥價格便宜、且能快速止痛,但只能緩解一時的癥狀,且停藥后痛經會復發,長期服用易導致惡心嘔吐、胃脘不適等,嚴重者可發生胃出血[15]。
中醫學關于原發性痛經的治療和研究歷史悠久,關于痛經的記載最早可見于《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并治》,而《景岳全書·婦人規》首次提出經行腹痛的病名。根據中醫學理論,疼痛的發病機理可歸為虛實兩大類,實者為不通則痛,虛者為不榮則痛。原發性痛經的患者可由于憂思、抑郁、暴怒等情志因素導致肝郁氣滯,經期血行不暢,發為痛經,或因為寒邪入侵經脈導致氣血失和,寒凝血瘀,不通則痛。因虛所致的疼痛可因先天腎虛或者久病體虛,或后天失養,氣血虧虛,發為不榮則痛。經水出諸腎,月經病與腎的關系最為密切。臨床觀察發現,痛經大多見虛實夾雜者,且多以腎虛為本,血瘀為標。腎藏精,而精與血同源,腎所藏之精是血液生成的物質基礎,若腎精不足,血海虧虛,胞宮經絡失于濡養,經期經血耗損,血液更虧,不榮則痛,發為痛經。或因腎陽不足,溫煦失職,虛寒內生,寒客于胞宮沖任導致氣血運行不暢,發為不通則痛。腎氣不足則推動無力,經血運行不暢,阻滯胞宮胞脈,發為痛經。腎陰虧虛,失于濡養,可導致筋脈攣急,氣血運行不暢,不通則痛。因此,腎虛血瘀是痛經的主要發病機理,治療該病當以補腎為主,活血為輔。本研究采用補腎活血調周法,通過補腎來扶助正氣,通過活血來祛除瘀血,通過調周調節腎氣-天癸-沖任-胞宮軸的功能,促使恢復正常的月經周期,最終達到標本同治的目的,從根源上治療原發性痛經,故而具有療效顯著,且復發率低的特點。
灸法是中醫學的外治法之一。《名醫別錄》載有:“主灸百病,可作煎……辟風寒,使人有子”。《本草綱目》云:“艾葉服之則走三陰而逐一切寒濕,轉肅殺之氣為融合;灸之則透諸經而治百種病邪”。艾灸具有溫經散寒、通經活絡的作用。艾灸療法主要通過溫熱效應和輻射效應[16]發揮作用,其治療原發性痛經患者可能通過促進子宮血液循環、改善新陳代謝、調節內分泌和免疫功能、緩解子宮平滑肌的收縮等達到緩解疼痛的作用。臨床觀察證實艾灸治療不僅對于原發性痛經具有滿意療效,還可有助于緩解多種臟腑病痛[17]。本研究將中藥補腎調周法與艾灸聯合用于治療原發性痛經患者,可提高綜合療效,達到標本同治的目的。且該療法安全無不良作用,治療成本低,易于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