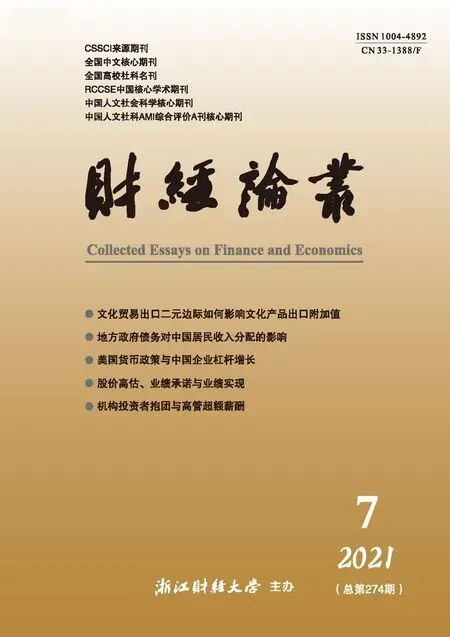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與服務化
宋 燦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近年來,我國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均呈現較快增長的趨勢,促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高效率融合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經濟轉型的關鍵所在。在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企業逐步由原來的單一生產方式調整為兼顧生產和提供服務的綜合經營策略,這一調整過程稱為“服務化”[1][2]。制造業企業服務化不僅為我國建設先進制造業提供有力的支撐力量,同時也是我國現代經濟體系中“先進制造業與高端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必然階段[3][4][5]。
制造業企業是否選擇服務化取決于投入成本與獲得收益的權衡,服務化經營策略調整意味著企業將面臨巨額的成本投入及較高的收益不確定性。所以,盡管在全球服務化趨勢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傳統制造業企業都選擇服務化。在企業資源約束普遍趨緊的情況下,一方面,服務化所需較高的資金投入對原有的產品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6];另一方面,服務化投入和產出的不確定性增加企業的沉沒成本[7],提高了企業的盈利風險,由此造成制造業企業對服務化策略持觀望態度。在“深化外資開放政策及有效利用外資”的原則下,我國外資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外資開放程度不斷加深。首先,外資開放程度的提高通過外資引入為服務要素投入奠定資金基礎,服務要素投入強度的提高促進了企業服務化。其次,多元化的外資投入在提高企業生產率、拓展企業利潤空間的同時增強了企業服務化風險承受能力[8][9],降低服務化產生的擠出效應和沉沒成本效應,促進企業服務化水平的提高。
與單一的產品生產相比,服務的提供不僅注重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和精準定位,而且關注企業與消費者良好的溝通和互動(如售前的資訊服務、售后的維修服務等)。因此,服務化不僅要求企業對消費市場具有較強的數據分析及處理能力,還要求企業具備對消費者較好的溝通互動能力和市場反饋能力[10]。數字工具和信息平臺的使用在提高制造業企業大數據搜集及分析能力的同時[11][12][13],也為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提供良好的互動平臺,拉近消費者與企業間的距離,降低企業服務化進程中產生的搜尋成本和摩擦成本,促進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14][15]。外資作為資本和技術的重要載體,其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能有效促進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為服務化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
與本文相關的文獻分為三類,主要是與外資開放、數字經濟及服務化相關的文獻。在外資開放的相關文獻中,包群等(2015)和Arnold等(2016)認為外資進入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16][17]。Fernandes和Paunov(2012)及孫浦陽等(2018)認為外資的進入加劇了本地市場產品競爭的激烈程度[18][19],對本地企業產生擠出效應,因此降低了企業生產率。韓超和朱鵬洲(2018)從中間品投入的視角驗證外資開放對企業出口及產品質量提升具有促進作用,且外資的作用效果隨著制度環境、企業所有制的不同而產生較大差異[20]。現有文獻從多個視角對數字經濟的內涵及外延進行了定義,其中與本文的數字信息化定義較為相似的文獻中,Zoroja(2015)和Lechman(2017)驗證數字信息化建設可通過促進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等渠道對區域經濟增長或競爭力提升產生影響[21][22]。Bayo等(2013)及詹曉寧和歐陽永福(2018)從微觀視角驗證企業數字信息化建設不僅提高資本的吸引力、促進資本的利用效率,還可通過搜尋成本和摩擦成本的降低來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升及改善出口績效[23][15]。Melville等(2004)認為數字信息化對企業行為的作用效果隨企業所在的產業鏈位置、企業外資利用水平高低等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24]。現有文獻對企業服務化策略的驅動因素分析可概括為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從外在因素看,Ariu等(2016)認為市場環境的變化導致企業被動地以“服務化”作為調整策略,以此增加企業產品附加值、提高產品核心競爭力[25];Coreynen等(2018)研究發現市場競爭有效促進制造業企業服務化[26]。從企業內在因素看,Mathieu(2001)指出企業是否選擇服務經營策略取決于在既定資源的基礎上及最大化利潤目標的驅動下,企業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獲得收益的權衡[27];Arnold等(2016)驗證企業生產率、企業利潤率及企業風險承受能力均是影響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的重要因素[17]。除此之外,Kohtamki等(2013)及Greenstein(2020)研究發現數字信息技術的應用通過降低與客戶溝通過程中的摩擦成本提高企業的服務效率,促進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28][29]。
由上可知,在我國外資開放程度逐漸提高的政策背景下,鮮有文獻從服務轉型策略的角度探討外資開放政策對企業行為的影響,且已有文獻對服務化的衡量大多從行業層面,通過構建制造業服務要素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作為服務化的代理變量,難以體現不同企業服務化的異質性。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主要創新點在于:首先,將外資開放和數字信息化納入企業服務化策略選擇模型中,從理論層面分析外資開放和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影響;其次,利用文本識別技術構建企業級別的服務化指標,以充分體現不同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的異質性,并從服務轉型策略和服務化深度兩個層面全方位刻畫服務化;最后,在理論分析和指標構建的基礎上,通過經驗分析不僅驗證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正向促進作用,厘清外資開放和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交互作用機制,還從服務化類型、市場開放程度及信息基礎設施密度等角度拓展分析外資開放對服務化影響的異質性。
二、理論分析
本文在Blanchard等(2017)及Breinlich等(2018)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外資開放指標[1][6],從理論層面分析制造業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與企業服務化三者之間的關系。
(一)消費者需求假設

(1)
(2)
其中,消費和服務的價格指數及用于產品及服務的總支出均為外生給定的,wG為產品生產的勞動力工資,wS為提供服務的勞動力工資(wG=wS=wi)。
(二)生產者假設
假設企業i產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YiG=ΛiGNGTiGLiG,服務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YiS=ΛiSNSτTisLis。ΛiGNG和ΛiSNS表示企業受外在因素影響而變化的生產率。根據Barro和SalaiMartin(2004)的做法[30],假設企業受外在因素影響的生產率與生產所需的中間品種類(NS、NG)成正比,企業可選擇的中間品投入種類為NG=NS=N(index)。其中,index表示外資開放指數,某個行業的外資開放程度越高(即外商投資越多),企業的數量就越多,則企業可選擇的中間品種類也越多(?N/?index>0)。與產品生產相比,服務的提供對企業的大數據搜集和分析能力及與客戶的溝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數字信息技術的應用不僅提高企業數據搜集和分析能力,使企業通過精準定位降低客戶的搜尋成本,還通過降低與客戶溝通過程中的摩擦成本來提高企業的服務效率(1)為簡化起見,本文未在模型中提及數字信息化對產品生產的影響。若同時將數字信息化變量加入產品生產效率中,最后的推導結果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因此服務產出的生產率與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τ成正比。Ti表示企業內在決定的生產率,企業根據市場情況在生產產品與提供服務之間進行抉擇,其分布函數為Ti=(TiGt+TiSt)1/t且t∈(0,∞)。
(三)企業服務化策略選擇
企業的利潤函數πi為收益減去成本,對企業利潤最大化求解:
maxπi=piGQiG+piSQiS-wi(LiG+LiS)
(3)
s.tTi=(TiGt+TiSt)1/tt∈(0,∞)
(4)
此時,消費者對企業i的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量等于企業產品或服務的產出量(QiG=YiG,QiS=YiS)。其中,QiG和QiS分別表示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量,YiG和YiS分別表示產品和服務的產出量。通過利潤最大化求解,可得企業服務收入與產品收入之比G為:
(5)
公式(5)對index求導,可得:
(6)
其中,γ-σ>0,?N/?index>0,?G/?index>0。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程度隨著外資開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一方面,外資開放增加制造業企業服務要素投入的數量,降低由于服務化產生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外資開放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升,拓展企業利潤空間,提高企業服務化的風險承受能力。由此,本文推出理論假設1:制造業外資開放提高了企業服務化水平。
公式(5)對τ求導,可得:
(7)
其中,γ-1>0,?G/?τ>0。由公式(7)可知,數字信息化對企業服務化的影響為正,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服務化程度隨著數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與單一的產品生產相比,服務的提供對企業在市場上數據搜集能力及溝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數字工具和信息平臺的運用降低了企業在服務化進程中的搜尋成本和摩擦成本,促進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本文推出理論假設2:數字信息化建設促進了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
三、變量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變量與數據說明
1.外資開放指標。本文將《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限制或禁止的行業賦值為-1,鼓勵的行業賦值為1,其他的行業賦值為0,并構建行業層面的外資開放指標(Index)(2)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分別于2007、2011和2015年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修改。。外資開放指標越大,表明該行業在政策層面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在指標構建完成后,將2007~2016年上市公司數據庫中的行業代碼與行業名稱進行精準匹配,并在匹配后予以人工校驗,以最大程度地保證匹配的準確性。
2.企業數字信息化指標。Hsu(2007)將數字信息化定義為系統、平臺、軟件等信息化數字技術和數字工具的應用[31]。根據Saunders和Brynjolfsson(2016)的做法[32],本文運用文本識別技術,依據企業無形資產明細中信息化的數字技術及數字工具相關的資產(如軟件、平臺、系統、信息技術等)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企業數字信息化程度,即AI=AIassets/Assets。其中,AIassets表示企業數字信息化無形資產,Assets表示企業總的無形資產,AI表示企業數字信息化程度。該指標越大,表明企業數字信息化的程度越高(3)企業數字信息化、服務化及控制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2007~2016年的上市公司數據庫(www.wind.com.cn)。。
3.服務化指標。本文借鑒Breinlich等(2018)的做法[6],從兩個層面構造服務化指標:一是從企業參與服務活動的策略上,企業參與服務經營活動則取1,否則取0,以此來衡量企業服務化策略(Service);二是從企業參與服務活動程度的層面上,采用制造業企業提供服務獲得的收入與總收入之比來衡量企業服務化程度(SerReve),即SerRevei=Ris/Ri。其中,Ris表示企業i提供服務獲得的收入,Ri表示企業獲得的總收入。該指標越大,表明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程度越高。
4.其他控制變量。鑒于企業服務化驅動因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為減少因模型設定帶來的計量偏誤及得到更加準確的計量結果,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加入可能影響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的其他控制變量。(1)企業年齡(Age),根據企業從設立年份到樣本期間,計算企業的存續時間并加一后再取對數。(2)企業規模(Size),根據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來衡量企業規模的大小并取對數。(3)企業杠桿率(Lev),以資產負債率表示企業杠桿率的大小(即企業負債與企業資產之比)。(4)資產回報率(Roa),采用企業利潤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值表示企業的資產回報率,資產回報率越大,企業的盈利能力則越強。(5)固定資產水平(Tan),以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值表示企業固定資產水平。
(二)計量方法的選擇與模型設定
鑒于企業服務化指標存在大量為0的特征,為避免因計量模型錯誤設定而導致的回歸偏差,本文借鑒Silva和Tenreyro(2006)的處理方法[33],采用泊松偽極大似然估計(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PPML)模型對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與企業服務化三者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經驗分析,具體的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Servpijt=exp(α+βIndexijt+θAijt+ξIndexijt*AIijt+λXijt+μijpt)
(8)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處于制造業行業j的企業i在時期t的服務化指標(Servpijt),核心解釋變量為外資開放指標(Indexijt)、數字信息化指標(Aijt)及二者的交互項。Xijt為可能影響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的其他控制變量,主要包括企業年齡(Age)、企業規模(Size)、企業杠桿率(Lev)、資產回報率(Roa)和固定資產水平(Tan)(4)此外,我們在計量模型中加入年份層面的固定效應,以控制特定時間事件沖擊對回歸結果的干擾;加入行業層面的固定效應,以控制不同行業特征的差異性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加入城市層面的固定效應,以控制不同區域差異因素對回歸結果的影響。。表1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N=7125)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分析
1.基準回歸。基于前文對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與服務化三者之間關系的理論分析,本文以服務化為被解釋變量、外資開放為解釋變量進行經驗分析。表2的第(1)~(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年份、行業和城市固定效應及企業固定效應的條件下,外資開放至少在5%的水平上對服務化策略的影響顯著為正。具體而言,外資開放程度每提高0.1個單位,制造業企業參與服務活動的概率提高15%。表2的第(4)~(6)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程度的影響顯著為正。外資開放程度每提高0.1個單位,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程度提高0.19個單位。以上分析表明,外資開放有效提高了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程度,促使企業由原來的單一產品生產轉向同時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一方面,外資開放吸引了制造業企業的外商投資,外資引入為服務要素投入奠定資金基礎,而服務要素投入強度的提高促進了制造業企業服務化。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外資投入為企業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不僅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升、拓展企業利潤空間,還提高企業服務化的風險承受能力,降低服務化產生的擠出效應和沉沒成本效應,由此促進企業服務化水平的提高,從而驗證了理論假說1。

表2 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回歸結果(N=7125)
2.數字信息化對企業服務化的影響。延續前文理論分析的思路,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數字信息化及其與外資開放的交互項,以分析外資開放與數字信息化的協同作用機制對服務化的影響。表3的第(1)~(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信息化對企業服務化策略的影響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具體而言,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每提高0.1個單位,制造業企業選擇服務化的概率提高1.6%。表3的第(4)~(6)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信息化對企業服務化程度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每提高0.1個單位,制造業企業服務化程度提高0.23個單位。以上分析表明,數字信息化提高企業服務化水平,數字工具和信息平臺的使用不僅增強制造業企業大數據搜集及分析能力,而且為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提供良好的互動平臺,拉近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距離,降低企業服務化進程中產生的搜尋成本和摩擦成本,促進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由此驗證了理論假說2。同時,數字信息化與外資開放的交互項對服務化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隨著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強。外資開放不僅為企業數字信息平臺的建設注入重要的資金力量,外資引入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提高了企業數字信息化水平,增強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邊際作用效果。

表3 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影響回歸結果(N=7125)
(二)異質性分析
1.區分服務化類型。為探討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作用機制及區分外資開放對不同類型服務作用效果的差異性,本文在Kowalkowski等(2015)及Mathieu(2001)對服務化定義的基礎上[34][27],根據企業參與服務活動是否直接與產品相關而將服務化分為產品支持類服務化和非產品支持類服務化。其中,產品支持類服務化指企業主要提供與核心產品相關的售后服務,以確保產品的正常運行及保證用戶的最佳體驗;而非產品支持類服務化指企業主要提供與產品服務不相關的咨詢服務、融資服務等。表4的第(1)、(2)列為以產品支持類服務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4)列為以非產品支持類服務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見,外資開放對產品支持類服務化的作用效果顯著大于非產品支持類服務化。制造業外資開放政策吸引大量外資企業的進入,與非產品支持類服務化相比,產品支持類服務化與產品生產直接相關,服務化的沉沒成本相對較小且服務化風險相對較低。因此,外資開放主要通過增加與產品相關的售后服務來促進企業服務化程度的提高。

表4 區分服務化的類型(N=7125)
2.區分不同的市場準入門檻。為分析市場開放程度對服務化的影響,本文借鑒Donaldson(2018)的做法[35],運用ArcGIS軟件及交通基礎設施電子地圖測算各個城市的最短運輸時間,并借助MATLAB軟件通過遞歸方程的推導來計算各個城市的區域市場準入指標。市場準入程度越高,表明該區域具有較低的區域貿易成本及較大的市場準入空間。本文依據企業所在區域的市場準入程度是否高于平均值來劃分樣本企業,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表5的第(1)、(2)列為以服務化策略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4)列為以服務化程度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總體的回歸結果表明,對處在市場準入程度較高區域的企業而言,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作用系數顯著大于市場準入程度較低區域的企業,主要原因是外商更傾向于在貿易成本較低及市場空間較大的區域投資設廠,市場準入程度較高區域的企業對外資的吸引力更大。相比于市場準入程度較低區域的企業,市場準入程度較高區域的企業對外資的吸收和利用效率也較高,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作用效果也更顯著。

表5 區分不同的市場開放程度
3.信息基礎設施密度對服務化的影響。由前文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可知,數字信息化是加快制造業企業服務化進程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區域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是企業數字信息化的重要依托,更是提高企業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邊際作用效果的關鍵所在。因此,本文將城市人均固定電話用戶、人均移動電話用戶及人均互聯網用戶三個指標加總(取對數)(5)信息化基礎設施密度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衡量該區域信息化基礎設施密度及信息化市場規模。表6的第(1)、(2)列為以服務化策略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4)列為以服務化程度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見,對處于信息基礎設施密度較高區域的企業而言,其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影響系數大于信息基礎設施密度較低區域的企業。在企業服務化的進程中,信息基礎設施通過提高數字信息化的成本降低效應來促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有效融合,最終提升企業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邊際作用效果,這與前文的實證分析結果相一致。

表6 區分不同的信息基礎設施密度
(三)內生性討論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討論。與傳統的以外商直接投資衡量我國外資開放程度相比,本文以外資政策為基礎構建外資開放指標,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由于潛在的因果關系產生的內生性問題。為進一步證明核心解釋變量的有效性,本文借鑒侯欣裕等(2018)的做法[36],通過構造制造業面臨的上游外資開放指數(6)一方面,上游外資政策變化與制造業企業并不直接相關;另一方面,由近年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調整可知,各個行業整體的外資開放調整方向和調整力度呈現同步平穩變化的趨勢。因此,以產業關聯為基礎計算的制造業上游開放指標作為制造業外資開放的工具變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以此作為本行業制造業外資開放內生性檢驗的代理變量。具體而言,假設每個上游行業投入占下游行業總投入的比重為θij,以該比重為權重,對外資開放賦值的虛擬變量(Index)進行加權,從而得到該行業面臨的整體上游外資開放指數(Ivindex),其計算公式為Ivindexi=∑Indexi*θij。表7的第(1)、(2)列為以服務化策略為被解釋變量的內生性檢驗結果,第(3)、(4)列為以服務化程度為被解釋變量的內生性檢驗結果。回歸結果顯示,在考慮內生性后,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及二者的交互項對服務化的影響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前文的分析結論依然成立。

表7 內生性檢驗的回歸結果(N=7121)
2.穩健性檢驗。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企業服務化程度的加深不僅體現在服務收入的持續增加,還體現在服務相關業務利潤空間的持續擴大。因此,本文以服務利潤與總利潤之比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資開放與服務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表8的第(1)、(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以服務利潤占總利潤的比值對企業服務化重新度量后,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依然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本文預期的結論相一致。此外,前文的基礎回歸采用的是全樣本,在制造業企業服務化轉變的過程中,部分企業提供房地產及相關服務的方式大多是以資本積累的形式開展的,與傳統的制造業企業由生產產品轉向提供服務的服務化轉變方式差別較大。為減少樣本選擇不當對估計結果產生的偏誤,本文剔除提供房地產服務企業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表8的第(3)、(4)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剔除提供房地產服務的制造業企業樣本后,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依然顯著為正,再次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如前文所述,鑒于被解釋變量中存在大量為0的特征,為避免因模型錯誤設定導致的計量偏差,本文分別以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為基礎,對外資開放與服務化之間的關系再次進行經驗分析,表8的第(5)、(6)列為Logit模型回歸結果,第(7)、(8)列為Probit模型回歸結果。可見,在替換計量模型后,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影響依然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也與前文的分析相一致。

表8 替換被解釋變量、剔除房地產服務企業及替換計量模型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外資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及數字經濟由服務業向制造業不斷滲透的雙重背景下,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上市公司年報構建微觀層面的服務化指標,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分析外資開放、數字信息化與服務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得出的主要結論為:外資開放有效促進了企業服務化的提高;數字信息化提高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邊際作用效果;外資開放對產品支持類服務化的作用效果更顯著;外資開放對服務化的作用效果在市場開放程度較高的區域更顯著,數字信息化對服務化的作用效果在信息基礎設施密度較高的區域更顯著。
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的幾點政策建議。首先,政府應不斷優化外資開放政策。外資開放不僅體現在開放行業和開放領域的拓寬,還體現在各個行業外資開放程度的加深,以此充分利用外資及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而帶動我國先進制造業的發展,促進高端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有效融合。其次,政府應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體系及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的資金支持,形成互聯互通的信息網絡體系,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硬件基礎。最后,政府應大力支持數字經濟的發展,形成數字經濟由先進服務業向高端制造業的高度滲透,為制造業企業服務化提供必要支持。對企業而言,在準確把握外資開放和數字經濟的雙重機遇下,積極調整經營策略,通過提供附加服務促進產品質量的提升,以達到增加產品附加值及維持行業競爭優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