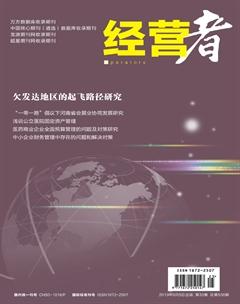煙草企業會計內部控制風險及其防范措施
羅皓
摘 要 煙草企業在新經濟發展壓力下需要對資金加強管理,提升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本文圍繞煙草企業會計內部控制風險與防范進行探討,為提升煙草企業的發展能力獻計獻策。
關鍵詞 煙草企業 會計 內部控制 風險防范
一、引言
煙草企業會計內部控制工作主要是通過對企業所有員工的約束與激勵,促進企業實現更高的經濟效益。企業的內部控制是一個系統的工作內容,控制的部分與部分之間存在相互的聯系,所以必須全方位地做好內部控制工作。煙草企業會計內部控制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企業未來的建設與發展,影響企業的資金風險,做好會計內控管理可以幫助企業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推動企業穩定前行。
二、煙草企業相關概述
煙草企業是具有采購、生產加工、銷售等一體化功能的生產加工企業,其產成品在所有產品類型中較為特殊,對人體有一定危害。所以,國家在其生產上進行調控。煙草企業關乎民生,其發展也受到社會的關注。加強對煙草企業的內部控制,對其自身的經濟競爭力和實力都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重要性從以下兩方面展開闡述:一是內部控制是建立在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基礎上,針對企業發展需要進行的內部控制制度,明確企業員工的職能責任;尤其是對企業財務的內部控制規范,對于企業的成本核算與控制十分關鍵。通過財務內部控制制度,可以對采購生產加工銷售中的所有環節進行監控,促進企業資金的良性循環。二是內部控制是企業對風險的防范機制,內部控制可以通過控制績效考核,提升企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對企業運作各環節進行風險要素的識別,對資金使用情況實時了解,及時發現不良的資金問題并做出調整,以防范企業中的資金風險等問題。
三、煙草企業內部控制的風險分析
煙草企業的財務風險分析在全方位預算、財務風險意識以及會計核算信息來源的不準確等方面,存在較多的問題,需要對此加以分析。
(一)全方位預算問題
一些煙草企業都是在年末進行次年的預算編制,但是年末財務人員還需進行眾多企業核算的任務,所以在預算的編制內容上難免會缺乏準確性。正是由于這種不準確性,造成預算對企業運作的控制力度不夠,很容易發生預算超支的問題;加上煙草企業人員認為預算工作只是財務部門的工作,也會引發一些問題。實則不然,預算是需要全部門相互協調配合的工作,但是實際工作中,企業對于預算控制也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導致員工在預算范圍內沒有盡責地進行成本控制,所以無法發揮預算的較大價值,也容易給企業財務帶來風險。
(二)財務風險意識不足
在煙草企業中,財務人員的專業素養層次不高,對于企業的風險分析意識不到位,缺乏利用財務數據為企業的決策與發展進行風險分析的能力。通常,有意識的財務活動多為基礎性的財務數據錄入與核算,對于數據的處理分析能力不足,無法為企業進行風險防控。
(三)會計核算信息不準確問題
煙草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落實不到位,很容易帶來會計核算信息不準確的問題。例如,月末前該提交的成本數據信息不全,管理人員有漏交的情況,或者因為對采購、生產各個環節的監督不足,導致成本核算時出現虛假賬目等現象,都不利于會計核算反映企業的真實情況,不利于企業制定正確決策,財務風險隱患加重。
四、煙草企業內部控制風險的有效防范措施
(一)利用大數據增強全方位預算控制
企業的預算管理對于企業應對風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今企業管理都已經將大數據引入大企業當中。煙草企業為了加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對市場作出準確的決策與規劃,需要科學的預算數據作為支持。大數據能夠為財務工作提供數據分析報告,提升財務工作水平和質量,使得企業的決策有數據可依;大數據使財務工作更加專業化,提高會計內部控制風險應對能力,推動煙草企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二)培養高素質財務工作人員
煙草企業為加強財務風險防范工作,需要從財務人員素質上加強培養。高專業素養能夠帶動煙草企業上下財務工作的有序化、專業化。尤其是在財務工作上,要由基礎工作向管理會計這種高級工作職能發展,多引進優秀企業的管理經驗,供煙草企業的財務工作進行借鑒學習。鼓勵員工考取注冊會計師等高級職業資格證書,多為員工提供專業知識能力培養的學術交流以及經驗交流活動,通過員工能力的提高,從財務工作中增強應對風險的能力。
(三)利用系統控制的思想設置全方位的內部控制制度
企業的內部控制監督主要是對企業人員的職責發揮進行監督,所以內部控制制度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對于員工的職責要特別明確,要讓員工自身清楚其具體的職能范圍,才能有標準去實現對其具體職責的考核,考核即監管工作內容,做好了監管才會利于財務控制工作的順利開展。同時,做好全方位的具體考核,就可以發揮有效的激勵機制,實現激勵的真實價值,用制度從根源一步步實現對煙草企業的財務風險防范。
五、結語
煙草企業內部控制存在全方位預算、財務風險意識不足、會計核算信息不準確的問題,優化煙草企業財務風險防范需要從利用大數據增強全方位預算控制、培養高素質財務工作人員、利用系統控制的思想設置全方位的內部控制制度三方面進行改進,提高煙草企業的財務風險防范水平。
(作者單位為四川省煙草公司雅安市公司)
參考文獻
[1] 鄧婭瓊.煙草企業內部控制的風險及其防范舉措[J].科技、經濟、市場,2015(9):165-166.
[2] 馮雪橋.關于煙草企業內部會計控制策略的思考[J].財會學習,2018(10):239.
[3] 王紅梅.煙草商業企業加強管理會計建設研究[J].全國流通經濟,2017(21):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