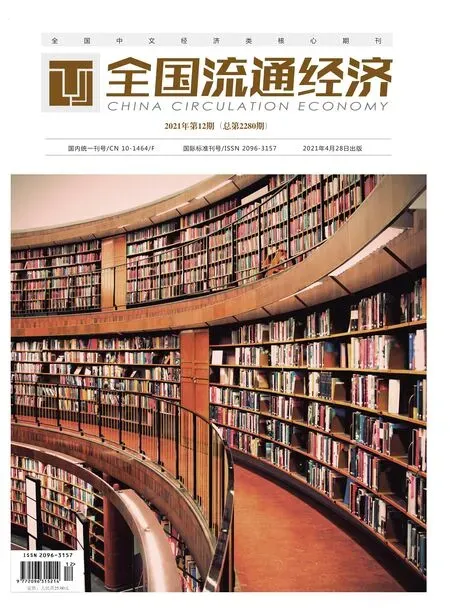普惠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基于西部地區的面板數據分析
章德花
(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0)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一直面臨著發展不平衡、發展質量和效率低等問題,普惠金融具有服務對象廣泛、成本可負擔、服務范圍廣泛的特點,能在更大范圍為經濟發展助力。如何讓普惠金融更好服務于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讓西部地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重要議題。
金融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金融發展是否對地區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有學者認為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和地區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倒U”形關系[1];如果不考慮傳導機制,經濟增長的回歸會削弱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2]。金融規模的地區差距對經濟差距發揮正向作用,而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的地區差距對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負向作用[3]。
普惠金融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傳統金融的供給與中小微型企業和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不匹配,使得我國金融體系出現了結構性的矛盾。一些學者發現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4],從區域發展角度看,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水平存在區域不均衡;從整體看,普惠金融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呈“倒U 型”的關系,有利于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5]。然而在目前的金融體系中,普惠金融在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困難[6],普惠金融對減小貧富差距效果不顯著,并且存在一些問題,如缺乏可持續性和地區差異[7]。
綜上,現有相關文獻大多數是從全國角度對普惠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沒有詳細研究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也沒有將城鎮化水平等因素考慮進去。本文對西部12個省份2009 年~2018 年普惠金融發展指數IFI 進行了測算,對普惠金融的研究進行補充。
二、構建普惠金融指數
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可用普惠金融指數衡量,為了評價普惠金融在各國的應用和發展情況,國外學者構建了一系列評價指標體系[8][12][13];國內學者對普惠金融的評價也構建了相應的指標體系[10][11]。有學者將普惠金融指標分為三個維度:普惠金融的滲透性、服務可得性和使用情況[9][11][13];而另外有學者則是從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給方面對普惠金融進行評價和比較[8][10]。
在指標選取上,本文從普惠金融供給和需求角度選取了六個指標來衡量普惠金融的發展。供給角度包括地理維度和人口維度,需求角度包括金融產品服務,具體的指標選取如表1 所示。

表1 普惠金融的維度及指標
本文參考了Chakravarty(2010)提出的指數計算方法,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i 是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六個指標,j 是各省市,xij是i維度在j 省的實際值,mi、Mi分別是i 維度在各省市的最小值和最大值;k=6,代表6 個維度;r 為常數,取值范圍為0 ~1,表示各指標對普惠金融的敏感度,本文取r=0.5 進行計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見表2。
IFI 指數的值取值范圍為0 ~1,其中0 表示完全金融排斥,1 表示完全金融包容。在國際上,當0 ≤IFI <0.2 是低普惠金融發展水平、0.2 ≤IFI <0.5 為中等普惠金融發展水平、0.5 ≤IFI <1 為高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通過對表2 分析發現,重慶市普惠金融發展較好,而內蒙古和寧夏在2011 年才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余9 個省份在2010 年有進一步的發展。總體而言,我國西部地區各省份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都有提高,但各省份之間還存在差距。

表2 我國西部地區2009年~2018年普惠金融指數
將2018 年西部各地區的IFI 指數和人均GDP 進行對比,發現IFI 指數與各省份人均GDP 趨勢相似,說明我國西部地區普惠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似關系。
三、實證研究
本文選取我國西部地區2009 年~2018 年12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建立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時期國家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可用人均GDP 衡量,因此將西部地區各省份人均GDP 作為因變量。為消除異方差性,取人均GDP 的對數值,IFI 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本文借鑒杜強等(2016)的方法,為了提高實證分析的準確性和全面性,將CPI、TFD、GOV、FDI、City 作為控制變量。并采用stata15 計量軟件,對我國西部地區普惠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本文以我國西部12 個省份2009 年~2018 年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共120 個觀測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wind 數據庫及各省份的統計年鑒。
為了使數據維度保持一致,對數據進行處理,各變量的具體解釋及取值方法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取值的具體解釋及取值方法
2.構建模型
根據選取的數據和樣本特征,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通過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本文的面板數據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構建的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α,β1,β2,β3,β4,β5,β6是各變量的系數,因變量PGDPit是i 省t 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自變量IFIit是i省t 年的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在回歸模型中,若系數β1大于0,表明普惠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顯著正相關;CPIit,TFDit,GOVit,FDIit,Cityit是控制變量; εit是隨機擾動項。
3.實證模型檢驗
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從核心解釋變量來看,IFI 的系數為0.47196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普惠金融對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具體表現為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每增加1%,西部地區人均GDP 提升47.20%,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顯著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
從控制變量來看,CPI 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能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政府規模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有積極的影響,地方政府在普惠金融發展時給予普惠金融財政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城鎮化水平從側面反映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程度,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的系數為4.2532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城鎮化要素聚集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有推動作用。

表4 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四、穩健性檢驗
上述實證結果充分驗證了普惠金融可以促進我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接下來將通過嘗試改變不同的信息集,對西部地區普惠金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穩健性進行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經濟體系的公平和收入分配對應,因此城鄉收入差距也可以表示經濟發展情況,其結果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衡量。
將城鄉收入差距Gap 作為因變量,根據相關結果,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隨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城鄉收入之間的差距減小,普惠金融能顯著地改善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通過計算,普惠金融發展每提高1%,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將縮小56.26%。
從控制變量的角度看,消費價格指數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CPI 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促進作用;TFD 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傳統金融機構對資金需求者的差別對待導致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鎮化水平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鄉差距越小,從側面反映了經濟的增長。替換因變量所得到的結果與基準模型的回歸結果一致,穩健性檢驗通過。
2.增加控制變量
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 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對外開放程度是貨物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
回歸結果表明,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普惠金融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計算,普惠金融發展每提高1%,西部地區經濟將增加47.23%,這表明普惠金融正向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從控制變量看,CPI、GOV 和City 都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政府影響比較大。從結果看,普惠金融能促進經濟增長,穩健性檢驗通過。
五、結論與建議
當前階段,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東中部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西部地區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本文利用我國西部地區12 個省份2009 年~2018 年的面板數據,對普惠金融指數進行測算,對普惠金融的發展進行評估,進而探討普惠金融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根據測算的IFI 可知,當前我國西部地區普惠金融發展呈現出利好趨勢,但是各省份之間仍存在差異,重慶市普惠金融發展相比其他省份一直處于中高水平,但增速較低。
第二,通過實證,發現普惠金融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自變量IFI 系數小于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說明普惠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果有待加強。雖然普惠金融在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積極的效果沒有得到很好發揮。
第三,政府規模和城鎮化水平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溢出作用,表明政府對普惠金融的發展給予支持,城鎮化水平越高,經濟增長越高。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積極調動金融機構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同時積極向居民宣傳金融知識,提高民眾的金融意識,進而提高金融服務的質量;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東中部相比存在一些差距,更應加強對金融服務模式和產品的創新,帶動西部地區金融業的發展。
其次,當前西部地區還存在一些金融服務空白的地帶,我們應加強對普惠金融的滲透性,擴大普惠金融服務范圍;另外應加大對新型金融機構的建設和發展,讓政府在普惠金融對經濟發展中起作用,促進經濟發展。
最后,要優化農村的金融環境,提高農村經濟的活力,使普惠金融對經濟的發展落到實處;同時注重對外貿易,抓住共建“一帶一路”的機遇,鼓勵小微創新型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同時,優化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化的普惠金融體系,并對普惠金融的制度條件進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