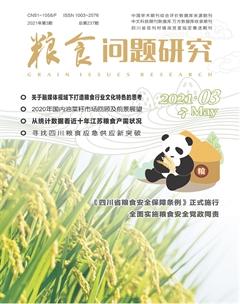尋找四川糧食應急供應新突破
任翔
摘要:四川經歷了多次地質等自然災害的考驗,糧食應急供應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和教訓。隨著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傳統糧食應急供應工作,有必要結合新的基礎條件、新的經濟業態、新的技術手段,以及人民群眾新的需求進行更多的改革探索和創新試驗。
關鍵詞:四川 糧食 應急 創新
四川盆地四面環山,北有秦巴大山阻隔,自古稱蜀道艱險。西部甘孜、阿壩、涼山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橫斷山脈貫穿其中,山地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被喻為“大地的階梯”,從成都出發到最遠的石渠縣城有1000余公里,山路曲折,要走三天時間。總體來看,全省地質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糧食自給能力較低,糧食流通跨度大、運距遠、費用高,保障轄區糧油供應、維護市場價格穩定,任務十分艱巨。
繼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四川又相繼發生“7·10”汶川特大山洪泥石流、“4·20”蘆山地震、“11·22”康定地震、“6·24”茂縣特大山體滑坡、“8·8”九寨溝地震、“6·17”長寧地震等重特大地質災害;使當地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受到極大威脅,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產生活面臨嚴峻挑戰,國際社會和國內各界高度關注。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四川糧食部門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冒著余震飛石,爬山涉水,連夜奮戰,圓滿完成糧食應急保供任務,保證了受災群眾有飯吃,保障了救援部隊需求供應,為奪取抗震救災勝利貢獻了糧食人的力量。
然而當前,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巨大提升,糧油加工行業集中優化,物聯網、無人機、人工智能、5G信息技術等一大批新事物不斷崛起,社會經濟的多個方面正發生著重大和深遠的改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深刻的影響,對于糧食應急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糧食應急工作只有適應這種新變化,才能在未來之路上承擔起時代賦予的新的責任和使命。
一、糧食應急工作面臨新形勢
(一)交通運輸方式的跨越式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川從蜀道難到蜀道通,再到蜀道暢,實現了歷史性跨越。目前,全省公路總里程達到33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位居西部第一、全國第二。到2020年底,四川(除三州外)所有貧困縣將縣縣通高速公路,至少形成兩條二級以上公路的互聯互通。隨著到康定高速的通車,最遠的石渠縣也能實現陸路當天抵達。阿壩、甘孜等機場的建成,為人員出行、貨物運輸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選擇方式。以前山石阻道、洪水斷路,一個地區成為孤島的情況將很難出現。
同時,在應急救災和物資運輸中,直升機、無人機等空中運輸也開始在民用、商用推廣普及。早在2016年,四川省衛生計生委就啟動空中救援體系建設,醫院與保險、直升機救援公司合作,建立空中救援體系。2019年8月,順豐公司利用無人機在甘孜運載著剛采摘的新鮮松茸,過去需要村民徒步幾個小時才能完成的運輸任務,如今僅需幾分鐘。交通運輸方式的跨越發展,由此而帶來的,將是糧食等應急救災物資運輸方式的重大改變。
(二)電商物流行業的迅速崛起
當前的四川糧油應急物流運輸大多是由儲備加工企業聯系長期合作車輛,根據調撥指令裝車發運到受災地區,通過災區的專門供應點和商場超市供應給受災群眾。又或是災區當地糧食企業或軍糧供應站點將本地儲備糧油直接分發到村鎮、街道和救災部隊,再由當地基層政府分發給百姓。可以說目前的糧食應急供應鏈還局限在糧食和行政系統內,對新經濟中迅速發展壯大的專業物流運輸少有觸及。而電商和由此而帶來的物流快遞行業可以說是近年來中國發展最為迅猛的產業之一。2020年6月1日,董明珠攜3萬經銷商直播帶貨,一天就成交50億元。順豐、京東、“四通一達”等一批覆蓋全國各地、直達村鎮的快遞物流企業創造著新經濟快速發展的神化。2019年,雙十一的訂單量達到創紀錄的12.92億單,發出一億個包裹僅用時8小時。設想一下,如果把這一億個包裹換成一億袋10公斤的大米,那么只要8個小時,就可以向全國各地發出100萬噸大米。這樣的物流速度和覆蓋面真是嘆為觀止,可以說我們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專業渠道能與之媲美。對于應急供應來說這是現有的優勢資源。
新零售的出現和物流快遞行業的快速發展改變的是商品的供給渠道。目前局部性的糧油應急也主要發生在如何把糧油及時配送到老百姓手中,滿足急需或者加大市場中的糧油供給,穩定市場糧源和價格。這個過程實際是一個供應渠道的問題。在商品供給渠道方式發生變革的趨勢下,糧油應急供應要融合進新零售的變革之中,利用好零售、物流行業的倉儲、配送、供應等載體,實現對市場糧油及時、全面、便捷供應。
(三)糧油加工行業集中度提升
糧油行業的行業集中度比較高,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大多是航母式企業,而且隨著市場的發展,集中度還有可能進一步提高。例如,在2010年后,中糧、益海、北大荒開始在四川建廠,魯花、道道全、克明面粉也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鋪貨分銷,四川的糧油生產格局由此而發生重大變化。到2019年,中糧在川的面粉產值占到全省面粉產值的44%,益海在川的食用植物油產值占到全省的24%。在大型企業開疆拓土,提高市場占有率的同時,另一邊是省內中小糧油加工企業的停(破)產。2018—2019兩年間全省停(破)產的入統大米加工企業有66家、小麥粉加工企業22家、食用植物油加工業24家。全省除大米加工還較分散外,可以說面粉和食用植物油生產已高度集中。而大米生產加工也必定走向大型化、集團化。“花中花”“金龍魚”“吉林大米”等一批大米加工龍頭企業和品牌,或在本地崛起,或從省外分銷占領四川市場。同時,由于集團化、大型化企業成為主導,這些企業也由此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銷售供應渠道,通過眾多的分銷、代理機構能夠將糧油產品及時、高效的供應到大部分鄉鎮、街道。
(四)零售服務點多面廣
與北方地區相比,四川的商品零售業可謂是異常發達。每個縣城、鄉鎮的街道兩旁通常都是商鋪,其中各種零售和餐館店占據絕大部分,像在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幾百米范圍內便有一家紅旗超市。同時,糧油供應已不局限于專賣店、商場、超市,以淘寶、京東為代表電商更是在中國掀起了一場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零售風暴。2019年中國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6.10億,市場交易規模突破11萬億元。
而眾多的商超等主體,不僅是糧食流通的重要力量,也是糧食儲備以及應急供應的重要力量。例如,成都的紅旗連鎖超市,在2020年疫情期間,每日糧油庫存保持在3000余噸,可保證3000余家店面10—15天的糧油銷量。而就是因為企業較多糧食商品周轉庫存,有效滿足了群眾在4月初受輿論影響的集中購糧需求。我們在擔心每個家庭存糧減少的同時,商超、餐飲企業的糧食存量卻在不斷豐富。現在四川的各個縣城、鄉鎮都有數家超市、商場、專賣店經營著品種豐富的糧油產品。在應急供應中,這些商超都有豐富的糧源可以供應,又有多種的糧源組織渠道,是應急工作寶貴的現有資源。
(五)應急工作由量到質的提升
從目前四川的自然災害等應急響應情況看,雖然一場地震、洪水會造成多個縣區、鄉鎮受災,但核心災區,斷水、斷電、房屋不能居住,需集中安置的受災群眾通常是在幾個重點鄉鎮或街道,人數從幾百到數萬。在最初的救援和集中安置中,群眾需要最基本的食、住、醫療等生活保障。作為住來說,或搭建帳篷或安置在學校、體育館等應急避難場所,有應急供電車、應急通訊車等配套保障。醫療衛生方面有帳篷醫院、移動醫療車,又或者通過轉運等為群眾及時提供醫療服務。而在食的方面,由糧食部門供應成品糧油,或由民政等部門供應方便食品。在受災前期,受災嚴重的群眾和廣大救援部隊,大多無法制作熟食,多靠民政部門發放的方便面、餅干、礦泉水解決吃飯問題。所以時常出現一些當地餐館和志愿者義務為受災群眾和救援部隊提供熱菜熱飯的感人場景。
由此看出,受災群眾和救援隊伍對應急供應的食物有著更加人性化的需求。作為保障受災群眾和救災部隊口糧供應的糧食部門,雖然及時供應了應急成品糧,對穩定災區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救災初期,大米、面粉等救災物資不能及時成為受災嚴重地區群眾和救災部隊的米飯、面條、饅頭,功效上打了折扣。如何在受災群眾最困難、救災部隊最艱辛的時候,為他們供應上熱飯熱湯,不僅是群眾生活的必需,也是災區樹立信心的有力手段,更是糧食應急供應部門承擔的責任。而到了災區群眾返家或分流安置階段,各地商業服務基本恢復,在后續的生活保障中,也多采用貨幣化救助措施,不再向受災群眾供應成品糧油。
二、創新應急供應方式,適應新形勢
(一)全面鋪點向相對集中轉變
全省建成糧食應急供應網點4103個,落實了糧食應急加工企業312個,配送中心248個,儲運企業288個。但在眾多的供應點中也存在良莠不齊、監管難度大的情況,一部分應急網點長期未開展過應急工作,名存實亡。即使有應急供應的地區,也往往是調動少數幾家糧食或商貿企業通過動用儲備或者異地購買調動商品糧油來保證供應。而隨著交通物流、信息化等基礎設施巨大發展和行業集中度提升,機構的組織方式開始更多的采用“總部+區域分中心”的方式建立。從中儲糧系統收縮戰線、區域集中戰略可以看出,各地應急載體也開始更多采用一種便捷有效的扁平化組織架構,集中由一個區域應急中心來保障一個地區的糧油應急需要。從而集中優勢資源和力量,加強各個區域中心的管理與建設,也讓應急工作更加專業、快捷、有效,也更利于監管。
舉個例子,像在阿壩、甘孜的一些縣,人口只有4—5萬,但地方儲備有2、3千噸,地處偏遠,消費量小,每年上千噸的輪換不能在當地購買和銷售,都需到內地往返,這樣的輪換的是入不敷出,企業虧損嚴重,而且監管極為不便。一些地方變通成在內地異地儲備,往往也是失去了儲備的應急作用。像這樣的地區可以探索以建立區域應急中心來覆蓋保障,縣上儲備以滿足10—15天成品糧油儲備為主,加上群眾存糧和商超庫存,基本能滿足當地群眾一個月的口糧消費。縣(區)一級將應急能力放在10—15天的成品糧油儲備和供應上,而區域中心由省、市(州)共建,著力加強原糧儲備管理和應急配送能力建設,保證在各種極端情況下能在較短時間將更多糧食供應到受災地區。
探索通過建立省級應急中心,各市(州)整合資源建立若干應急分中心方式,來進行糧油應急資源整合改革。省級中心負責全省糧油應急供應調度,各區域中心負責各區域的糧油應急供應。區域中心除了自身應急能力建設外,更多通過引進種植、加工、物流、供應企業方面的戰略合作伙伴,開展全產業鏈應急保障。例如,在加工方面,與中糧、益海、新興等一些全省性區域龍頭企業達成應急加工協議,各區域與區域重點企業開展合作,淘汰小而散的應急加工企業,一個區域盯住這幾家重點企業,讓大型企業成為應急中的核心骨干。建立起政府糧油應急與糧油加工企業的聯系機制,運用好大型企業現有的生產和分銷能力,實現糧油應急的及時加工、及時供應。
(二)縱向建設向縱橫聯合轉變
一是增強應急中心內力。在有條件應急中心,探索智慧倉儲建設,推進淺圓倉等自動機械化建設和AI技術應用,實現糧食從進到出的信息化、無人化、智能化管理。試驗無人機、特種越野車輛等糧食應急供應方式,實現對一些交通阻斷地區的及時供應。通過建立衛星定位系統和車載可視化系統,實現對應急車輛和資源的遠程調度。二是開展廣泛橫向合作。探索與京東、天貓、蘇寧易購等互聯網企業的線上合作和與益海、中糧、北大荒、紅旗、沃爾瑪等大型企業、連鎖企業的線下合作,調動這些企業的全國和全球糧油資源,聯合順豐等物流企業,動用社會商品糧油,實現對局部地區糧油應急供應,筑牢應急供應的第一道防線和緩沖帶。在縣(區)一級可聯合當地的重要商貿企業,通過利用大型商貿企業采購、庫存等資源,實現對地區糧油的應急供應。聯合商業直升機企業和專業運輸企業,構建立體多層次運輸通道。豐富糧食應急供應手段,實現從空中到陸地、從糧食系統到全社會力量的立體應急供應體系。
(三)原糧應急向生熟兼顧轉變
管理大師德魯克說:“在組織的內部,不會有成果出現,一切成果都存在于組織之外。組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外部環境提供良好的服務。”既然在災后應急救援期間,在水、電、氣不通、住房無法居住的情況下,成品糧油無法及時為災民和救援隊伍提供熟食,那么作為糧油應急供應的糧食部門,有必要想一些辦法,實現受災群眾和救災部隊的即時口糧需求,給災區群眾和救援部隊帶去最直接的溫暖和信心。例如,在2020年疫情期間,益海嘉里武漢營銷分公司聯合當地經銷商,將集團捐贈的糧油物資免費配送至為醫療機構提供愛心盒飯的餐飲終端,保障包括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在內 16 家武漢市醫院的餐飲后勤服務。目前在各地應急救災中已經有應急醫療車、應急通訊車、應急發電車等各種應急設備,而糧食還局限在原糧及成品糧供應中。提供熟食的方式有添置野戰餐車,在省或重要的市(州)配置野戰餐車,當有應急需要時,機動供應到災區最需要的地方,在救災第一時間實現熟食供應,這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應急熟食供應還可建立帳篷食堂,在安置點等集中區為災區群眾定點供應;還可租用當地有條件的餐館,成為救災口糧供應點。熟食供應成為糧食應急救災供應的重要補充。
汶川地震過去十余年,十余年來,從汶川到蘆山,從康定到九寨,這些經歷山河破碎的多難之地,書寫著縫合傷口、重建新生的“中國奇跡”。作為在災難中經受考驗和成長的四川糧食應急保障,更加明確該擔起的重任,不論在災時、戰時,還是平時、裕時,都要時刻守住糧食安全底線,為經濟發展、為民生安定筑牢堅強保障。作為經歷多次應急考驗,從悲壯走向豪邁的四川,更要在應急救災、保障糧食供應方面,為全國探索更多可推廣的寶貴經驗。
(作者單位:四川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