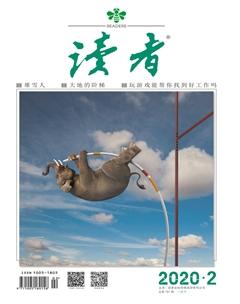肥瘦之間

減肥,為了健康,更為了美。楊貴妃不需要減肥,相反,當時的婦女們都仿效她增肥。不知李隆基的審美品位是高是低,只從周昉筆下的《簪花仕女圖》來看,當時崇尚的女性之肥胖的確傾向于雍容華貴之美。趙飛燕以瘦之美征服了帝皇,楚宮里為崇尚苗條細腰而餓死不少人。
繪畫中有疏密對照之美,疏可走馬,密不透風,各走極端。藝術美往往體現在特性之夸張中,走極端,猶如疏密之為兩極,肥與瘦也是造型美中的兩極。吳道子畫寬松衣著的人物,人稱“吳帶當風”;而曹仲達追求緊窄美,衣紋如濕了水般緊貼在身軀上,人稱“曹衣出水”。西方現代藝術的主要特征就是表達感情之任性,形式走極端。馬約雕刻的肥婆比楊貴妃胖得多,其實已超越“胖”的概念,而在追求造型中的飽滿與張力,即所謂量感美。而當代美國畫家奧得羅則更由此道發展進入漫畫世界,他的作品形象肥得臃腫到極限,眉眼口鼻都縮成小星點兒,丑中求美,美丑之間難分難解。中國人大都不接受這種調侃之美,但我們欣賞無錫泥阿福。我前幾年在印尼海邊見到一位肥碩驚人的英國年輕婦女,覺得她是造型藝術中追求量感美的最佳模特兒,返京后我為此作了幅油畫。不了解西洋藝術的客人來家看到后都覺得刺激、好奇,我于是解說“這是洋阿福”,他們會心地點頭,因而我為此畫命名為“洋阿福”。“衣帶日已緩”“思君令人瘦”“人比黃花瘦”,中國詩人多愁善感,時時流露出對瘦的憐愛。林黛玉之美似乎潛藏在瘦弱中,弱不禁風也成了一種東方的審美形象。西方現代造型藝術中也追求瘦骨嶙峋之美,盡量揚棄一切累贅的脂肪、肌肉,突出堅實的人之最本質的架構。瑞士的杰克梅蒂于此走到了極端,“人”幾乎存在于幾根鐵絲中,人們評說那屬于存在主義了。
生活中人們追求肥瘦合度,有人說合度就是美。有位史學家開玩笑,說如果埃及艷后的鼻子增高毫厘,羅馬的歷史就要被改寫了。確乎,美丑之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形容美,總說增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但“情人眼里出西施”,審美往往帶有偏見。藝術創作中,審美的“偏見”是獨特風格之別,偏見緣于偏愛,而偏愛則緣于發現了別人尚未發現的特色。美術基礎教學中要求作業完整,面面俱到。面面俱到了,完整了,是一件可評高分的習作,但絕不可能是藝術杰作。五官端正并不等于美。肥人中有美丑之別,瘦人中也有美丑之別,不肥不瘦而合度呢,也未必就美。美,真是有點邪氣!
(長天遠水摘,吳冠中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