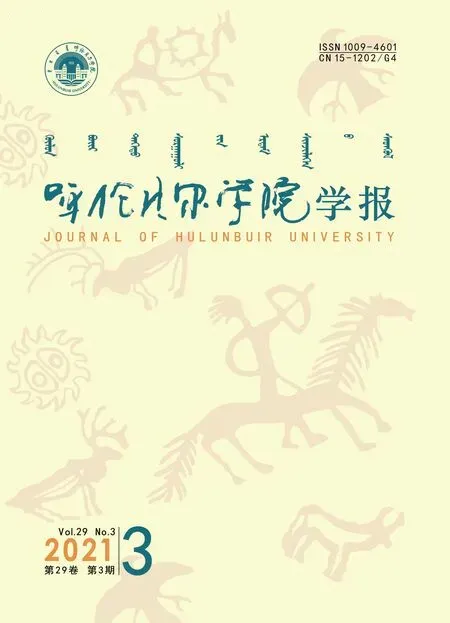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
——基于杠桿率的中介效應(yīng)研究
李利婷
(安徽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安徽 蚌埠 233000)
金融危機(jī)以來我國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日益金融化,與此同時(shí),微觀層面實(shí)體企業(yè)從金融渠道獲利占比逐年升高[1]。伴隨著我國經(jīng)濟(jì)“脫實(shí)向虛”的趨勢下,我國實(shí)體企業(yè)的金融化趨勢也愈發(fā)彰顯,根據(jù)雷新途等[2]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滬深兩市非金融上市企業(yè)的金融投資率和與之相匹配的金融渠道獲利比率整體呈上升趨勢,從2008年的2.58%和12.99%上升到2017年的11.24%和51.98%。經(jīng)濟(jì)的“脫實(shí)向虛”趨勢引起了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密切關(guān)注。正如李克強(qiáng)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bào)告中明確指出的“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從來都是我國發(fā)展的根基”,實(shí)體企業(yè)的金融化問題關(guān)系到振興與發(fā)展我國實(shí)體經(jīng)濟(jì),了解實(shí)體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xiàn)綜述
目前,已有文獻(xiàn)主要研究企業(yè)金融化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經(jīng)濟(jì)影響。其中,宏觀層面研究主要考察了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宏觀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金融市場穩(wěn)定等方面的影響。朱映惠[3]研究指出:企業(yè)獲利更依賴對(duì)金融投資的收益會(huì)放大宏觀經(jīng)濟(jì)波動(dòng),且這種波動(dòng)的放大在次貸危機(jī)后的經(jīng)濟(jì)下行區(qū)間更加顯著。李思龍[4]研究指出:上市公司“脫實(shí)向虛”的金融業(yè)股權(quán)投資行為,造成了虛擬經(jīng)濟(jì)的過度膨脹,雖不會(huì)提升銀行體系的風(fēng)險(xiǎn),但是會(huì)增加股票市場風(fēng)險(xiǎn)以及金融體系的系統(tǒng)性風(fēng)險(xiǎn)。而微觀層面關(guān)于企業(yè)金融化經(jīng)濟(jì)影響的文獻(xiàn)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自身的影響,如對(duì)企業(yè)價(jià)值、研發(fā)創(chuàng)新和經(jīng)營管理狀況等的影響,但研究結(jié)論存在較大爭論。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企業(yè)金融化會(huì)造成負(fù)面影響。例如,Orhangazi[5]利用美國非金融企業(yè)的樣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非金融企業(yè)金融投資的增加會(huì)擠占實(shí)體投資。吳非和向海凌[6]的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金融化顯著地抑制了自身的研發(fā)創(chuàng)新活動(dòng),而倪志良等[7]也指出會(huì)通過擠出實(shí)物資本投資,進(jìn)而損害實(shí)體企業(yè)的主業(yè)業(yè)績。但也有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實(shí)體企業(yè)金融化發(fā)揮的并非全是負(fù)面作用。例如,胡奕明等[8]研究指出:企業(yè)主要是基于“蓄水池”動(dòng)機(jī),持有金融資產(chǎn)形成預(yù)防性儲(chǔ)備,可以發(fā)揮“蓄水池”效應(yīng)。蔡艷萍和陳浩琦[9]的研究表明實(shí)體企業(yè)金融化與企業(yè)價(jià)值之間呈現(xiàn)“倒U型”關(guān)系,而鄧超等[10]在研究指出:企業(yè)金融化能夠提升經(jīng)營業(yè)績、改善融資約束,進(jìn)而顯著降低股價(jià)崩盤風(fēng)險(xiǎn)。也有學(xué)者進(jìn)一步對(duì)企業(yè)持有的金融資產(chǎn)進(jìn)行分類,研究不同金融資產(chǎn)的經(jīng)濟(jì)影響,如宋軍和陸旸[11]的研究指出:企業(yè)持有的非貨幣性金融資產(chǎn)與企業(yè)的經(jīng)營收益率呈U形關(guān)系;徐珊[12]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持有投資性金融資產(chǎn)會(hu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起到拉動(dòng)作用,而貨幣型金融資產(chǎn)則會(huì)抑制企業(yè)資本回報(bào)率和長期績效的提升。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shè)
(一)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
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分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和擠出效應(yīng)兩個(gè)方面,兩個(gè)效應(yīng)的具體分析需要從企業(yè)配置金融資產(chǎn)的動(dòng)機(jī)講起。企業(yè)配置金融資產(chǎn)的動(dòng)機(jī)分為“蓄水池”動(dòng)機(jī)和利潤最大化動(dòng)機(jī)。其中,“蓄水池”動(dòng)機(jī)是指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是預(yù)防性儲(chǔ)蓄,是指企業(yè)為了面對(duì)市場環(huán)境變化、融資困難而持有金融資產(chǎn);利潤最大化動(dòng)機(jī)指的是企業(yè)為了獲取最大化的利潤而配置金融資產(chǎn)。但其實(shí)無論企業(yè)基于何種動(dòng)機(jī)配置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均存在拉動(dòng)效應(yīng)和擠出效應(yīng)。
所謂拉動(dòng)效應(yīng),就是指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能夠提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一方面,企業(yè)出于“蓄水池”動(dòng)機(jī)持有的金融資產(chǎn)能夠提升應(yīng)對(duì)風(fēng)險(xiǎn)能力、營運(yùn)能力以及盈利能力。首先,企業(yè)利用金融資產(chǎn)主動(dòng)進(jìn)行資產(chǎn)管理能夠提高資產(chǎn)的流動(dòng)性,保持資產(chǎn)增值的同時(shí)能夠及時(shí)為企業(yè)提供資金補(bǔ)償、緩解企業(yè)融資約束、加快企業(yè)資本的周轉(zhuǎn)速度,從而防止資金短缺或者突發(fā)事件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造成不利影響,同時(shí)也避免錯(cuò)失未來投資機(jī)會(huì)。其次,企業(yè)可以通過利用衍生金融產(chǎn)品進(jìn)行套期保值,從而對(duì)沖外部風(fēng)險(xiǎn);企業(yè)還可以通過金融資產(chǎn)協(xié)調(diào)各部門的現(xiàn)金流,可以穩(wěn)定企業(yè)的現(xiàn)金流,從而緩解企業(yè)在外部市場的借債壓力;另一方面,出于利潤最大化動(dòng)機(jī)而配置的金融資產(chǎn)在獲取了資本增值、豐富了企業(yè)利潤結(jié)構(gòu)的同時(shí),也能夠?yàn)槠髽I(yè)帶來了更高的流動(dòng)性,使企業(yè)在財(cái)務(wù)管理、資本運(yùn)作等方面擁有更多選擇,提升企業(yè)的盈利能力。
所謂擠出效應(yīng),是指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對(duì)實(shí)體產(chǎn)業(yè)存在擠出效應(yīng),進(jìn)而會(hu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造成負(fù)面影響。無論出于何種動(dòng)機(jī)配置金融資產(chǎn),對(duì)實(shí)體業(yè)務(wù)都會(huì)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即占用了企業(yè)用于實(shí)體業(yè)務(wù)的資金,使實(shí)體業(yè)務(wù)得不到充分的發(fā)展。現(xiàn)代公司治理制度下,常常通過短期業(yè)績指標(biāo)來評(píng)價(jià)管理者價(jià)值,而持有金融資產(chǎn)為企業(yè)帶來了大量流動(dòng)性資產(chǎn),為管理者擴(kuò)大投資提供了便利,這就加劇了企業(yè)的金融化程度,甚至造成企業(yè)盲目投資和過度投資金融資產(chǎn)的現(xiàn)象。從長期來看,企業(yè)金融化將會(huì)導(dǎo)致企業(yè)主營業(yè)務(wù)的收縮,同時(shí)迫于業(yè)績的壓力,企業(yè)不得不繼續(xù)壓縮主營業(yè)務(wù)投資并轉(zhuǎn)向金融投資。然而,上述企業(yè)金融化過程會(huì)導(dǎo)致企業(yè)重心轉(zhuǎn)向金融部門,會(huì)導(dǎo)致企業(yè)經(jīng)營性投資過分縮減,使企業(yè)投入技術(shù)研發(fā)、生產(chǎn)改進(jìn)等方面的經(jīng)費(fèi)降低,又削弱了企業(yè)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性業(yè)務(wù)能力,最終陷入企業(yè)過度金融化的惡性循環(huán)中。
基于以上拉動(dòng)效應(yīng)和擠出效應(yīng)的論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a:企業(yè)金融化程度較低,持有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
假設(shè)1b:企業(yè)出現(xiàn)過度金融化,持有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營運(yùn)主要為擠出效應(yīng)。
(二)杠桿率的中介效應(yīng)
首先,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杠桿率既有降低效果也有提升效果。一方面,金融資產(chǎn)的強(qiáng)流動(dòng)性使得配置金融資產(chǎn)成為企業(yè)的一種重要的融資方式,必然會(huì)替代企業(yè)的一部分債務(wù)融資,直接導(dǎo)致企業(yè)杠桿率下降;另一方面,管理者對(duì)于金融資產(chǎn)的偏好促使企業(yè)有更大動(dòng)力進(jìn)行銀行信貸,同時(shí)金融投資帶來的高收益也使得企業(yè)更容易獲得信貸支持,均會(huì)造成杠桿率的提升。
其次,杠桿率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也有促進(jìn)和抑制兩個(gè)方向的影響。一方面,杠桿率越高表明企業(yè)負(fù)債越多,而通過債務(wù)利息支出的抵稅,能夠降低綜合資本成本,因此,杠桿率提高會(huì)給企業(yè)帶來稅盾等收益從而促進(jìn)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提高;另一方面,高杠桿率意味著高負(fù)債,負(fù)債會(huì)引起的財(cái)務(wù)拮據(jù)成本和代理成本問題,而當(dāng)負(fù)債過多時(shí),企業(yè)因債務(wù)違約風(fēng)險(xiǎn)會(huì)產(chǎn)生過多的財(cái)務(wù)費(fèi)用、因破產(chǎn)風(fēng)險(xiǎn)的上升也需要更高的人力成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狀況不利;高杠桿也會(huì)造成未來融資約束,而企業(yè)為了緩解融資約束會(huì)將資金過多地投放在固定資產(chǎn)和土地投資上,會(huì)導(dǎo)致創(chuàng)新研發(fā)等方面投入減少,從長遠(yuǎn)來看并不利于企業(yè)績效的提高。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a:企業(yè)金融化程度較低,持有金融資產(chǎn)會(huì)導(dǎo)致杠桿率降低,從而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以拉動(dòng)效應(yīng)為主;
假設(shè)2b:企業(yè)出現(xiàn)過度金融化,金融資產(chǎn)的持有會(huì)導(dǎo)致杠桿率的提升,進(jìn)而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為擠出效應(yīng)。
(三)金融資產(chǎn)期限結(jié)構(gòu)
不同期限的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不同。流動(dòng)性是短期金融資產(chǎn)的主要特征,正如上文分析,流動(dòng)性能夠提升企業(yè)應(yīng)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營運(yùn)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因此,短期金融資產(chǎn)會(huì)使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得到提升。而長期金融資產(chǎn)缺乏流動(dòng)性,與上文同理,長期金融資產(chǎn)會(huì)對(duì)實(shí)體產(chǎn)業(yè)產(chǎn)生擠出效應(yīng),進(jìn)而會(hu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造成負(fù)面影響。
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shè):
假設(shè)3:短期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而長期金融資產(chǎn)會(huì)產(chǎn)生擠出效應(yīng)。
三、研究設(shè)計(jì)
(一)樣本選擇
本文樣本為我國A股滬深兩市非金融類企業(yè),選取其于2007-2019年之間的財(cái)務(wù)數(shù)據(jù)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檢驗(yàn),數(shù)據(jù)來源于CSMAR數(shù)據(jù)庫,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ST、*ST公司、以及信息不全、數(shù)據(jù)缺失的公司樣本。同時(shí),對(duì)所有連續(xù)型變量在1% 和99% 水平上進(jìn)行Winsorize處理,以避免異常值的影響,最終獲得了1040家上市公司共計(jì)13520個(gè)公司年度樣本。
(二)模型設(shè)定
本文基于溫忠麟和葉寶娟[13]的中介效應(yīng)模型,來進(jìn)行本文中介效應(yīng)的檢驗(yàn),建立如下模型:

(1)

(2)

(3)
其中,ROA(i,t)是指代碼為t的企業(yè)在t年份的資產(chǎn)收益率,為被解釋變量,用來表示企業(yè)的經(jīng)營績效,取凈利潤與總資產(chǎn)之比;FAR(i,t)是指對(duì)應(yīng)的企業(yè)金融資產(chǎn)比,為解釋變量,用來表示企業(yè)金融化程度,其取值為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占總資產(chǎn)的比重,本文借鑒Demir[14]、宋軍和陸旸[11]、杜勇等[15]的做法,根據(jù)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表,將貨幣資金、交易性金融資產(chǎn)、衍生金融資產(chǎn)、短期投資凈額、發(fā)放貸款及墊款凈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chǎn)凈額、持有至到期投資凈額、長期債權(quán)投資和投資性房地產(chǎn)凈額都納入金融資產(chǎn)的范疇;在后續(xù)的進(jìn)一步檢驗(yàn)中,本文根據(jù)金融資產(chǎn)的流動(dòng)性,將上述前四項(xiàng)列為短期金融資產(chǎn),其余為長期金融資產(chǎn)。短期金融資產(chǎn)變量SFA和長期金融資產(chǎn)變量LFA,取值分別為短期金融資產(chǎn)額與總資產(chǎn)之比、長期金融資產(chǎn)與總資產(chǎn)之比,分別替代企業(yè)金融化指標(biāo)FAR代入方程中進(jìn)行檢驗(yàn);LEVi,t表示企業(yè)杠桿率,用企業(yè)的資產(chǎn)負(fù)債率即總負(fù)債比上總資產(chǎn)來衡量,是模型中的中介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有資產(chǎn)規(guī)模SIZEi,t、公司成長性GROi,t、公司年齡AGEi,t、股權(quán)集中度SHRLi,t、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STATEi,t,取值分別對(duì)應(yīng)企業(yè)總資產(chǎn)取自然對(duì)數(shù)、(當(dāng)期營業(yè)收入-上期營業(yè)收入)/上期營業(yè)收入、數(shù)據(jù)所在年份減去公司成立年份然后加上1、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建立的虛擬變量(國有企業(yè)為1,其他性質(zhì)企業(yè)為0)。
四、實(shí)證結(jié)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jì)
資產(chǎn)收益率的平均值為0.0381,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0.2119和0.2539,表示企業(yè)的資產(chǎn)收益率之間差異較大。企業(yè)金融化程度的均值為0.1994,標(biāo)準(zhǔn)差為0.1404,表示不同企業(yè)不同年份的金融化程度相差較大。短期金融資產(chǎn)和長期金融資產(chǎn)占總資產(chǎn)的比重均值分別為0.1644和0.0333,且短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的標(biāo)準(zhǔn)差0.1165大于長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的標(biāo)準(zhǔn)差0.0700,表明企業(yè)持有短期金融資產(chǎn)比重大于持有長期金融資產(chǎn)的比重,且不同企業(yè)持有的短期金融資產(chǎn)總量差異也大于持有長期金融資產(chǎn)的總量差異。企業(yè)杠桿率均值為0.5009,最大值達(dá)到1.2083,最小值為0.0710,且標(biāo)準(zhǔn)差為0.2090,表示企業(yè)杠桿率處于較高水平,并且不同年份不同企業(yè)之間差異較大。同時(shí),表1也表明各企業(yè)間各控制變量的差異也較為明顯,其中企業(yè)資產(chǎn)規(guī)模的標(biāo)準(zhǔn)差最大,達(dá)到了1.3639,而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雖然標(biāo)準(zhǔn)差最小,但是標(biāo)準(zhǔn)差為0.1497,也表明股權(quán)集中度在不同企業(yè)間差異并不小。(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
(二)回歸結(jié)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的是平衡面板數(shù)據(jù),通過以混合回歸(OLS)作為參照系,同時(shí)考慮個(gè)體隨機(jī)效應(yīng),通過F檢驗(yàn)和Hausman檢驗(yàn),最終確定應(yīng)使用無時(shí)間效應(yīng)的個(gè)體固定效應(yīng)模型。(見表2)

表2 模型回歸結(jié)果
由表2,列(1)金融化程度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回歸系數(shù)為0.095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t值為19.20,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也說明企業(yè)金融化程度較低,即假設(shè)1a成立。列(2)中企業(yè)金融化程度對(duì)杠桿率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企業(yè)提高金融資產(chǎn)配置水平能夠顯著降低杠桿率水平。在列(3)中,企業(yè)金融資產(chǎn)比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回歸系數(shù)為0.0557,相對(duì)于列(1)中0.0957有所降低,且杠桿率仍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有顯著的負(fù)向抑制作用,說明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通過降低企業(yè)杠桿率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有正向促進(jìn)作用,即杠桿率在企業(yè)金融化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上述過程中杠桿率的中介效應(yīng)占總效應(yīng)的41.67%,表明本文假設(shè)2a成立。
(三)進(jìn)一步分析:不同期限金融資產(chǎn)的檢驗(yàn)
本文在上述檢驗(yàn)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檢驗(yàn)持有不同期限的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異質(zhì)性。(見表3)

表3金融資產(chǎn)期限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影響的檢驗(yàn)結(jié)果
從表3的回歸結(jié)果來看,列(1)短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回歸系數(shù)為正,t值為0.124,值為22.07,表明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列(2)中企業(yè)短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對(duì)杠桿率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企業(yè)提高金融資產(chǎn)配置水平能夠顯著降低杠桿率水平。在列(3)中,企業(yè)短期金融資產(chǎn)比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回歸系數(shù)為0.0851,相對(duì)于列(1)中0.124有所降低,且杠桿率仍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有顯著的負(fù)向抑制作用,說明企業(yè)持有短期金融資產(chǎn)通過降低企業(yè)杠桿率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有正向促進(jìn)作用,即杠桿率在企業(yè)持有短期金融資產(chǎn)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上述過程中杠桿率的中介效應(yīng)占總效應(yīng)的31.37%。列(4)中長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總效應(yīng)并不顯著,列(5)表明企業(yè)持有長期金融資產(chǎn)也能夠顯著地降低企業(yè)的杠桿率,而列(6)中,在把長期金融資產(chǎn)占比和企業(yè)杠桿率同時(shí)納入模型的檢驗(yàn)表明,持有長期金融資產(chǎn)會(hu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且杠桿率的提高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也會(huì)產(chǎn)生負(fù)面作用,基于此判斷企業(yè)持有長期金融資產(chǎn)會(huì)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產(chǎn)生擠出效應(yīng),但中介效應(yīng)并不成立。至此,上述檢驗(yàn)表明,假設(shè)3成立。
(四)穩(wěn)健性檢驗(yàn)
本文從兩個(gè)方面開展穩(wěn)健性檢驗(yàn)來驗(yàn)證研究結(jié)論的穩(wěn)健性。一方面,選擇凈資產(chǎn)收益率作為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代理變量進(jìn)行上述檢驗(yàn),結(jié)果與上述結(jié)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本文考慮使用不同估計(jì)方法(OLS和RE)來進(jìn)行回歸,進(jìn)一步增加本文研究結(jié)論的可靠性。實(shí)證結(jié)果表明:本文結(jié)論具有穩(wěn)健性,因篇幅所限,回歸結(jié)果未予列示。
五、結(jié)語與啟示
本文選取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財(cái)務(wù)數(shù)據(jù),來對(duì)企業(yè)金融化的微觀經(jīng)濟(jì)后果進(jìn)行研究,即研究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并檢驗(yàn)了杠桿率在其中發(fā)揮的中介作用。研究結(jié)果表明:一是企業(yè)金融化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說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是拉動(dòng)效應(yīng);二是杠桿率是企業(yè)金融化影響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中介變量,企業(yè)持有金融資產(chǎn)除了直接影響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外,還存在通過降低杠桿率從而提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中介效應(yīng),且中介效應(yīng)占總效應(yīng)的41.67%;三是不同期限的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不同,短期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拉動(dòng)效應(yīng),且杠桿率的中介效應(yīng)顯著,占總效應(yīng)的比重為31.37%,即杠桿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而長期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的影響主要為擠出效應(yīng),且擠出效應(yīng)只在控制了企業(yè)杠桿率的基礎(chǔ)上顯著。
基于上述研究結(jié)論,本文提出了兩點(diǎn)政策啟示:第一,合理控制企業(yè)配置金融資產(chǎn)的額度。目前總的來說,企業(yè)配置金融資產(chǎn)程度還未出現(xiàn)過度現(xiàn)象,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來講,金融資產(chǎn)仍更多地發(fā)揮著拉動(dòng)效應(yīng),因此在抑制企業(yè)金融化時(shí)不能一概而論,應(yīng)以各企業(yè)實(shí)際情況為依據(jù)進(jìn)行把控,以免影響企業(yè)正常的投融資行為;第二,改善金融資產(chǎn)配置的期限結(jié)構(gòu)。配置短期金融資產(chǎn)對(duì)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更多具有的是拉動(dòng)效應(yīng),可以適度持有,而配置長期金融資產(chǎn)發(fā)揮的更多是擠出效應(yīng),應(yīng)謹(jǐn)慎持有。同時(shí),監(jiān)管方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非金融企業(yè)的金融投機(jī)行為的監(jiān)管,避免出現(xiàn)企業(yè)過度進(jìn)行金融資產(chǎn)投資的行為,有效監(jiān)管“脫實(shí)向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