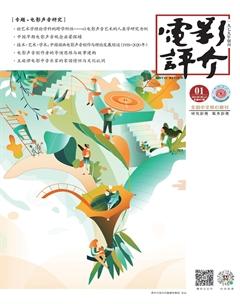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中音樂家的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
邱健
《為國而歌》(青山,2019)和《音樂家》(西爾扎提·亞合甫,2019)是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上映的兩部主旋律電影。《為國而歌》由王雷、古力娜扎主演。該片講述了人民音樂家聶耳(王雷飾)青年時代的成長經歷,從昆明到上海的音樂自覺之路,以及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故事。《音樂家》由胡軍、別里克·艾特占諾夫主演。該片講述了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胡軍飾)到蘇聯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但因蘇德戰爭爆發被迫停工,從莫斯科輾轉到阿拉木圖與哈薩克斯坦音樂家巴赫德讓·拜卡達莫夫結下深厚友誼并修訂完善《黃河大合唱》的故事。
從題材來講,聶耳、冼星海的電影并不好拍,在此之前已有過多部類似影片,如《聶耳》(鄭君里,1959)、《冼星海》(王亨里,1994)、《少年星海》(李前寬、肖桂云,2011)。讓人耳目一新的是《為國而歌》的導演青山是聶耳的侄孫,也是聶耳文化的研究者、傳承者,這是他的電影處女作,他懷著對祖輩的深切緬懷,從家鄉的視角來呈現聶耳“為大眾而歌”的形象;《音樂家》的導演西爾扎提·亞合甫是維吾爾族,被稱為“西部暖流”派代表人,他憑借自己對異域文化的熟悉,用異鄉的視角來呈現冼星海“為民族而樂”的形象。
一、家國情懷:人生追求與共同體命運的熔融合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是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禮記》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1]《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家國情懷”中的“情懷”指的是情感、寄托和希望。在古代社會,家國情懷源于士大夫階層所倡導的人文價值觀,以儒家的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為代表。在近現代社會,家國情懷與個體意識/集體意識、家庭命運/國家命運密不可分,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外敵入侵、戰爭踐踏、骨肉分離、妻離子散之后痛定思痛的文化心理沉淀。在當代社會,家國情懷又有了新的內涵,尤其注重主體對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即“在中國人的心中,家是最小的國,國是千萬家,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與家庭、家族、國家緊密相連。從家出發,個人、家庭、群體、國家乃至天下,一脈相承,共同支撐著我們的理想。”[3]作為新主旋律電影,《為國而歌》《音樂家》在對聶耳、冼星海的塑造中盡可能地還原了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和革命者所展現出來的家國情懷,又融入了當代人從個體經驗出發對家庭、社會的新認知。
(一)家鄉與異鄉的雙重意義
在《為國而歌》中聶耳的家鄉是云南,異鄉是上海、日本。在《音樂家》中冼星海的家鄉是中國,異鄉是蘇聯、哈薩克斯坦。兩部電影都很注重家鄉與異鄉的意義,試圖通過鏡頭的切換、轉場來敘述音樂家的家國情懷。在家鄉的敘述中,影片強調了音樂家之于家人、家庭的意義。聶耳是入孝出悌的兒子,敦厚善良的未婚夫,母親彭寂寬、女友袁春暉(影片最后已叫聶母為媽)一直期盼著他從上海、日本歸來。冼星海是無微不至的丈夫、慈愛謙和的父親,妻子錢韻玲、女兒冼妮娜也日夜盼望著他從莫斯科、阿拉木圖歸來。家人的團聚、家庭的團圓對于中國人來說有著重要意義,但戲劇性的是這兩位音樂家始終都沒有歸來。更為悲劇性的是,23歲的聶耳在日本避難時溺水身亡,40歲的冼星海因無法回國在莫斯科染上肺病去世。聶耳、冼星海的英年早逝是家之不幸,也是國之不幸,這讓人們看到了個人、家庭、國家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異鄉的敘述中,影片強調了音樂家之于社會、國家的意義。聶耳和冼星海都是有著遠大理想并背負使命的音樂家。聶耳到上海后,尤其是在聯華影業公司和百代唱片公司的那段日子,積極投身于左翼音樂運動,倡導新音樂,批判靡靡之音。冼星海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到《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中,輾轉到阿拉木圖結識拜卡達莫夫后又主動參與到當地反法西斯的音樂活動中。聶耳在上海創作了《賣報歌》《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冼星海在阿拉木圖改編了哈薩克斯坦民歌,創作了《民族解放》《阿曼蓋爾達》等樂曲,并修訂了《黃河大合唱》。導演有意突出音樂家在異鄉的音樂生活、音樂創作,其目的就是要展現他們在社會命運共同體中的責任與擔當。
為了豐實這種家國情懷,兩部影片都努力把家鄉與異鄉放置到更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場景中進行拓展。《為國而歌》拓展的是“家鄉”。導演青山對云南歷史十分熟悉,影片中展現出了兩個明顯的意圖。一是彰顯云南的抗戰文化,其手法是通過虛構聶耳參軍時的鐵血戰友張潤武,來點出云南陸軍講武堂并串聯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二是彰顯云南的教育文化,其手法是把袁春暉設計為大學才女,以此來引出云南教育史上第一所高等學府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并作為實景拍攝地。此外,影片對白色恐怖場景的設計也有所考慮,“七一一”北門街火藥爆炸案,地下黨員趙瓊仙被害,李國柱、吳澄(有孕在身)夫婦就義,都是聶耳家鄉昆明抹不去的歷史事件。
《音樂家》拓展的是“異鄉”。哈薩克斯坦作為蘇德戰場的大后方,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一是安置了數十萬戰爭難民。影片中的音樂廳、歌劇院收容了大量難民,拜卡達莫夫的老母親家中也接納了滿屋子的難民。電影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拜卡達莫夫及家人對冼星海提供的無私幫助,讓冼星海在異鄉也有了一個溫暖的家。二是號召動員上百萬人加入蘇聯紅軍奔赴前線。雖然影片沒有花太多鏡頭去表現前線的戰斗,但大后方不斷收到的陣亡通知單就已經說明問題了。年輕的小提琴手的陣亡、小女孩卡麗婭的父親被槍殺,都令人欲哭無淚、悲痛萬分。三是不遺余力地生產物資支持前線。影片中婦女們都在工廠里干著重體力活,卡麗婭的母親達娜什·拜卡達莫娃受傷后,冼星海去幫忙干活,拉小提琴的雙手被磨得傷痕累累。這些鏡頭敘述都體現出了哈薩克斯坦人民堅強不屈、英勇無畏的家國情懷。
(二)家書與文稿的內心獨白
在家鄉與異鄉的敘述中,家庭與社會的意義同時疊置在了音樂家身上,影片以家書為載體來勾連二者并體現主人翁的家國情懷。無論是聶耳還是冼星海,他們的家書都有著共同的寫作結構,即前半段表達對家人的思念,后半段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理想。這種結構并不老套,也不是導演或編劇虛構的,而是基于聶耳和冼星海書信的史料所做的藝術加工。
《為國而歌》中聶耳到上海后寫了多封信回家,母親也不斷地給他回信。考入黎錦暉的明月歌舞劇社后,聶耳和母親有過一次深入的交流。這篇信件的原稿來自聶耳于1932年6月28日寫給母親的信。“親愛的媽媽,您的信我已接到了!我看了流了不少的眼淚,我也不知到底為了什么?雖是一封很簡單的信,但是里面卻包含了許多問題:1.我的婚姻問題。2.我的回滇問題。3.人生問題……我一向總是抱著一個正當宗旨:‘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礙物阻止或妨害我對社會的改造,我要在這人類社會里做出偉大的事業。”[4]這是19歲的聶耳親筆寫出來的內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社會的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并發出要改造社會的宏愿。質言之,聶耳想做他那個時代的弄潮兒。
《音樂家》中,冼星海到莫斯科、阿拉木圖后,也堅持給妻子寫信,但除一封信寄出外,其余的信都被退了回來。這些信是在1990年冼星海女兒冼妮娜造訪阿拉木圖見到卡麗婭時才讀到的。雖然影片中沒有展開信件的內容,但鏡頭在冼星海、錢韻玲之間的切換已經給出了答案,即以淚洗面、相互思念卻又肩負重擔、身不由己。這種藝術加工的合理性來自1940年之前冼星海給錢韻玲寫的信。如冼星海于1940年11月8日寫給錢韻玲的信。“你的近況怎樣?你可以時常寫信給我,我也不斷地給你寫信,希望我們在這別離的日子,都要大家把身體保重,不特為現在工作起見,也是為將來,也為國家、民族、人類做工作的……我的精力大部分都是為著工作,把私人的事情放在第二位。”[5]有了這些史料支撐,影片的藝術創作就顯得堅實和真實,音樂家的家國情懷就不再是毫無根基的口號式宣教。
除了信件外,兩部影片也盡可能地對各種文稿進行挖掘。如《為國而歌》中,聶耳與友人在昆明西山暢談理想的臺詞,就來自他的兩篇文章。《我之人生觀》談到,“來到滇的西山,買點極清幽的地方……約得幾個同志,蓋點茅屋,一天研究點學問,弄點音樂。”[6]這種想法在《我的人生觀》中發生了轉變,“從我個性去發展、所以我也要研究藝術。還有我也希望做一個游歷家(并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游歷世界一周,由實地觀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7]又如《音樂家》中,拜卡達莫夫和冼星海的一次別有深意的對話。拜說:“你創作的每個音符都是你對家鄉的思念”,冼說:“沒有祖國的人就是沒有根的大樹”。實際上,冼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就有過這樣的思考。他寫道,“我把我對于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我漸漸把不顧內容的技巧(這是‘學院派藝術至上的特點)用來描寫訴說痛苦的人生、被壓迫的祖國。”[8]兩部影片中還有很多場景的設計能在聶耳、冼星海的文稿中找到相應的表述,這都真實地彰顯了他們的家國情懷。
二、文化認同:身份確認與新音樂精神的協同共建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基本含義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9]認同(Identity),除了確認、體認的含義外還有身份、識別的意思。聶耳和冼星海都是雙重身份者,一重是職業身份,即音樂家;一重是政治身份,即共產黨員,兩位音樂家對文化認同的理解正是從身份的確認中開啟的并集中地體現在了新音樂中,他們用這樣的音樂來凝聚人心、喚醒國人。
(一)聶耳對大眾音樂的認同
“認同”的對立面是“不認同”,“認同”是肯定性的,“不認同”是否定性的。聶耳對音樂的思考是從自我反思開始的,一天深夜,他像往常那樣寫起了日記。“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所謂古典音樂,不是有閑階級的玩意兒嗎?一天花幾個鐘頭苦練基本練習,幾年,幾十年后,成為一個小提琴家又怎么樣。你演奏一曲貝多芬的索納塔,可以鼓動起勞動群眾的情緒嗎?不對,此路不通。”由此看來,聶耳認同的是革命音樂,用音樂來鼓舞大眾,不認同的是陷入古典音樂的迷宮,沉湎于音樂的消遣。要說明的是,聶耳很清楚這種認同與否不是純粹出于音樂審美的考慮,他知道古典音樂也很有價值,并花了大量時間來學習。但從聶耳對職業身份和政治身份的雙重體認來說,走上革命音樂的道路是自己所做出的選擇,他要賦予音樂更多的社會屬性。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理解聶耳的音樂創作。
導演青山對聶耳歌曲的設計可謂用心良苦,他從聶耳一生寫的37首歌中挑選了5首,并以“用歌曲看上海”的視角來進行鏡頭的敘述。第一首是聶耳在街頭買報紙,為報童小毛頭寫的《賣報歌》;第二首是田漢帶聶耳看真實的、勞動人民的大上海,為碼頭工人寫的《碼頭工人》;第三首是飛機轟炸上海灘,餓殍滿地,聶耳為勞苦大眾寫的《饑寒交迫之歌》;第四首是女明星阮玲玉自殺后,聶耳為賣藝的歌女寫的《鐵蹄下的歌女》;第五首是聶耳在沮喪時,聽到劉良模帶領民眾歌詠會在演唱自己為筑路工人寫的《開路先鋒》。這五首歌有獨唱、合唱,有男聲、女聲、童聲,在視聽語言上符合現代人的審美,但更重要的是,這五首歌所體現的文化認同。之所以把聶耳的音樂稱為“新音樂”,就是因為他在音樂的道路上開掘出了一條大眾性的道路,以區別于那些“舊音樂”。對此,呂驥給出了中肯的評價。“他(聶耳)是中國音樂史上第一個新現實主義的作家,他雖然沒有許多作品,可是他的作品建立了中國音樂史上最初的新現實主義。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感染到一種完全新的情感,鮮明有力的節奏,樸素明朗的曲調,使他的作品區別于同時代的某些作家。”[10]
影片中聶耳音樂的真正高潮是《義勇軍進行曲》。和其他聶耳題材電影不同的是,《為國而歌》沒有花大量精力去講述聶耳如何為《風云兒女》配樂,而是從他個人的夙愿出發,把寫一首中國的《馬賽曲》作為文化認同的起始點,繼而在劇情的推進中不斷強化,讓《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水到渠成。導演把聶耳這個夙愿的種子埋在了昆明,把花開在了上海。場景一,聶耳與李國柱、吳澄、艾思奇等在昆明相聚時,唱的就是《馬賽曲》,此時聶耳已秘密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場景二,聶耳與田漢在上海探討《馬賽曲》,田漢說“中國也應該有這樣的歌曲”,此時聶耳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場景三,聶耳和小提琴老師討教如何寫出像《馬賽曲》這樣的音樂,但老師卻告訴他,“沒有上帝的指引,你是寫不出來的”,每一次的暗示、強調都在刺激聶耳,激發他的潛能,終于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他寫出了《義勇軍進行曲》。
事實上,《為國而歌》中的《義勇軍進行曲》還蘊含著中國人更為深厚的文化認同。影片中三個場景頗有深意。一是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頭腦中浮現出寧死不跪的地下黨員趙瓊仙老師;二是宋慶齡為《起來》(《義勇軍進行曲》在美國叫《起來》,由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演唱)唱片做序;三是中國遠征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赴緬作戰以及血戰到底的松山之役。這三個場景可以概括為三個動詞:不跪、起來、前進,并可以反復說、反復唱。因為與之對應的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大義凜然、百折不撓、英勇無畏。因此,《義勇軍進行曲》象征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戰歌,也成為了新中國的《國歌》。
(二)冼星海對民族音樂的認同
五四運動時期,北大“歌謠運動”的發起者曾提出過一個設想,即在“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11]這里的“民族”是nation的含義,是在政治學、文化學中理解的概念,指的是國家、國民、國族。廣義地來說,所謂“民族的詩”,就是指能夠代表民族共同體,并被民族所認同的藝術作品。要想創作出“民族的詩”絕非易事。從作品來說,它必須能夠體現出民族精神的普遍性,在情感、風格、水準等方面也經得起考驗。從創作者來說,他也必須持之以恒、堅定信念,甚至是浴火重生,在極大的精神強度中去思索個人與民族的命運,才有可能產生好作品。很多音樂家都試圖向著這個方向努力,但真正走出來的并以作品說話的音樂家卻不多。聶耳的新音樂精神鼓舞了冼星海,讓他在職業音樂家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身份確認中繼續沿著這條音樂之路前行。冼星海走出來了,他極大地提升了大眾音樂的藝術品質,為中華民族譜寫出了“民族的詩”。
冼星海始終把音樂作為精神的寄托,在哈薩克斯坦期間,他改編了多首當地的民族歌曲并成功地創作了交響音詩《阿曼蓋爾達》。阿曼蓋爾達是哈薩克斯坦的民族英雄,他曾帶領人民擊退了強大的侵略者,處在家國存亡之際的哈薩克斯坦人正在呼喚他。“冼星海對這部史詩的工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在開始工作之前,他細心地研究過阿曼蓋爾達的傳記,到哥薩克所住的山莊里去熟悉哥薩克的生活,學習哥薩克民族的文化和音樂。”[12]影片中,樂曲寫完后冼星海把手稿拿給樂隊成員試奏。拜卡達莫夫激動地說,“黃訓(冼星海的化名)的《阿曼蓋爾達》,哈薩克斯坦的《阿曼蓋爾達》。”在這之后,《阿曼蓋爾達》傳遍了哈薩克斯坦,在慶祝反法西斯的勝利日里上演,也在多個重要的音樂場合上演,被哈薩克斯坦人民認同為“民族的詩”。
冼星海作為一個顛沛流離的異鄉人,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一方面是音樂對他來說猶如一股暖流,是生命得以延續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是他對民族性的音樂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1937年創刊的《文化新聞》中有篇文章叫《一位從艱難困苦里斗爭出來的民族音樂家——冼星海先生》。“民族音樂家”這個稱號是準確的,冼星海始終在思考民族精神、民族命運,并要以音樂的民族形式表現出來。在他的聲樂和器樂作品中,民族性的音樂占到了很大比例。冼星海對民族性的文化認同實現了他個人的價值,也傳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價值。文章寫道,“冼氏是我國在國際上爭得光榮的音樂家,而他在音樂上有所成就,他的毅力和環境困難掙扎奮斗的精神,是值得人們來欽佩的。”[13]影片中,胡軍的演繹也非常到位,既有剛毅堅卓的一面,又有多情善感的一面,以“硬漢”的形象展現出了苦難中的冼星海用音樂進行戰斗的革命意志。
《音樂家》中,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修訂完善《黃河大合唱》的樂譜也是一項重要工作。雖然1939年《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獲得了巨大成功,但冼星海明白,要想讓作品成為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藝術佳作,還要繼續提升品質,精益求精。他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留學的那段日子,看到了西方音樂的偉大,因此他是把《黃河大合唱》與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西貝柳斯的交響音詩《芬蘭頌》、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等偉大音樂作品進行對標的,力圖把中國的民族音樂引到世界音樂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導演在電影接近尾聲時,也就是1945年冼星海輾轉到庫斯塔納后,特地安排了一場音樂會,冼星海帶病向祖國獻上了修改版的《黃河》。他說道:“我的身體不太好,但我相信音樂是不朽的。”這次音樂會震撼了所有人,但令人心痛的是,這竟然成為了冼星海生命終章的挽歌。
結語
作為弘揚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的主旋律電影,兩部影片都顯示出了一個字——真。《為國而歌》從構思到拍攝前后經歷了5年的時間,導演青山是以多年對聶耳的研究為積淀,在閱讀大量史料、文獻的基礎上來創作電影的。《音樂家》的拍攝,前后也是5年時間,導演西爾扎提·亞合甫帶領主創人員和拍攝團隊在中、哈、俄三國實地走訪,盡可能地搜集、整理了冼星海的一手資料。從整體上講,這兩部電影所呈現的歷史事件都是真實的,即便是虛構、杜撰出來的人物或情節也能在相應的史實中得到合理的解釋。此外,從視覺畫面來說,如場景、服裝、道具等的設計,也多半是從老照片中取材的,這就讓影片充滿了真實感、歷史感。
對于如何表現音樂家的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來說,除了“真”還要“純”。青山導演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道,“聶耳是個純粹的人,孝的純粹、愛的純粹、音樂的純粹、信仰的純粹,只有這樣一個純粹的人才不會被大上海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所迷惑,始終向著自己的使命‘前進、前進、前進進。”有意思的是,劇中青山借用了阮玲玉的臺詞“你很純粹”講出了聶耳的純。在《音樂家》中,冼星海也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人。小女孩卡麗婭是影片中的重要角色,導演、編劇有意從孩子的眼睛里來看冼星海,就是要表明這位來自中國的音樂家有一顆赤子之心。而身體每況愈下的冼星海仍堅守著他的音樂事業就更加純粹,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人類聽覺文化中最純粹的積淀。胡軍把這種純粹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他就要繼續指揮著生命的交響曲演奏下去,直到終止式的來臨。總的說來,主旋律電影中的家國情懷與文化認同必須是至真至純的,“挖得深”才能“拍得真”,“拍得真”也才能“保住溫”。聶耳、冼星海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兩位偉大的人民音樂家有情有義、絕假純真,《為國而歌》《音樂家》的成功為同類影片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參考文獻:
[1]陳戌國.禮記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485.
[2][戰國]孟軻.孟子譯注[M].金良年,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50.
[3]劉躍進.家國情懷,一個古老民族的精神脊梁[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12-04(12).
[4][6][7]《聶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聶耳全集(中)[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145,9,26.
[5][8][12][13]黃祥鵬,齊毓怡,編.冼星海專輯2[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1962:217,5,312,248.
[9]李國良.增進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EB/OL].(2016-10-28)[2021-02-19]http://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498597/1498597.htm.
[10]《聶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聶耳全集(下)[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17.
[11]劉勇,李怡總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1895-1949[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196.
【作者簡介】? 邱 健,男,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雅博士后,主要從事文學批評、音樂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