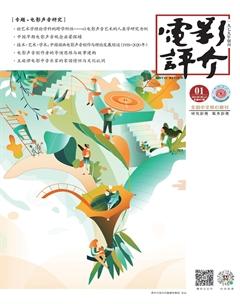《隱秘的角落》:“差異與重復”背后的啟蒙邏輯
曹芳
在代表作《差異與重復》中,德勒茲將重復劃分為兩種類型——“空洞的重復”指完全由本能決定的行為,它的循環不會帶來任何差異;創造性的重復則將差異置于同一之上,重復中差異的程度越高,人的行為就越是自由。[1]其中,“空洞的重復”又以是否對主體產生裨益為依據分為有益的重復和有害的重復。《隱秘的角落》中以單個個體或人物關系網為基礎建構了以上所述的多種重復類型,然不論是無差異的空洞性重復抑或是有差異的創造性重復都并未簡單停留在形式層面,導演真正想觸及的是重復形式背后的人類共同情感。
一、空洞性重復
(一)積極的空洞性重復
德勒茲所提出的空洞性重復是蜜蜂采蜜、蟻后繁殖,抑或人類的膝跳反應等本能行為,[2]清晨的一杯白開水、夜間的早眠本是脫離本能、走向自律的個體單一行為,但在一遍遍重復后最終成為習慣,便也在潛意識中獲得了本能特征,這些重復性的動作能夠在日積月累中對個體生理機能和心理素質產生一定有益影響,因此被視作積極的空洞性重復。
這種重復模式在《隱秘的角落》中以主題形式呈現出來,嚴良對“不要做壞孩子”的執念與陳冠聲發自內心的正義感相契合,兩個人物相繼將“正直”這一主題推至觀眾眼前,他們的生命并非兩個孤獨的個體,而是一種隱匿的輪回。陳冠聲在劇中的身份是一名人民警察,但他與葉警官又有不同之處,因為他是一名即將退休的警察,年齡的蒼老賦予了這個人物復雜而值得回味的閱歷,而在這過往的人生中,嚴良便是他的遺憾,在老陳退休前夜,他與年輕同事們聚餐的這個場景中,導演特意安排這個角色發出感慨,以臺詞直白地進行自我悔悟,他認為自己一生公正執法、盡心盡力,卻仍有一事無法釋懷,那便是沒有看好嚴良之父,導致其犯下重罪。為什么這一場內心剖析的戲碼會被安排在退休前夕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更甚者或許可以探討老陳這個角色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筆者以為老陳的蒼老其實是與嚴良的茁壯成長相對應的,在劇情設置中,朱朝陽與嚴良本是同齡人,但嚴良卻因身材高大健碩而成為朱朝陽的保護傘,顯然身體強壯的嚴良不止于與朱朝陽形成了對比,在另一條暗線中,嚴良的成長與老陳的衰老是同步進行的,而與這一時間進程同時推進的還有嚴良心智的成熟,即他的內心世界也逐漸走向老陳所期待的方向。在作品結尾處,鏡頭漸漸從遙遠的天際拉回到兩個人物的近景中,他們難得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嚴良微笑著告訴老陳:“我以后想當警察。”這句短小而溫馨的臺詞使老陳生命中的正直品質在嚴良處得到了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個人物在故事敘述的過程中均完成了堅守正直品質這一任務,且在這一過程中二者都未對人生理想有過動搖之心(即便嚴良參與了敲詐張東升的事件,但他內心一直堅持要在拿到錢之后自首贖罪),因此其中并無差異產生。嚴良的成長與老陳的衰老演示出自然萬物生理層面的空洞性重復,而嚴良成為警察的夢想與老陳的警察身份相呼應,形成了心理層面的空洞性重復,于是雙重重復共同展示出不具有差異但又向前發展的重復。老陳的退休意味著嚴良人生的開始,具有正面教導意義的空洞性重復展開了新的輪回。
如果說嚴良與老陳的關系網是通過主題形式展現積極的空洞性重復,那么影片中的另一些人物則通過自己對某一行為的不斷實施展現此重復模式,這種形式更加機械化,亦更符合空洞性重復的本質性要求。例如被網友戲稱為“萬年老二”的葉馳敏,當她出現在鏡頭中時,無一不是認真學習的模樣:提前做初三題型、抱怨老爸工作交談聲音打擾自己看書、獲得第二時的不甘、在張東升家里偶遇朱朝陽詢問補習卷事宜……超情節人物是中國學者提出的一個概念,許旺認為這一類人物不對主要情節發展起作用,但卻適時出現,成為小說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承擔了隱喻性功能。[3]葉馳敏這一角色的反復出現看似不合情理,但她作為一個“錨”銜接在故事結構中,她是聯結葉警官、張東升、朱朝陽的一個關鍵點,因此她是一個具有情節作用的人物,但同時她的出現又過于頻繁,并且這個人物的勤奮特質與劇情聯系并不明顯,這便是她所具有的超情節性。對于學習的熱愛和好強的天性導致葉馳敏在鏡頭中不斷重復自己的學習生活,在此意義上來說,學習不再是一種任務,而變成了不可或缺的習慣,葉馳敏的幾次學習情節之間雖未生成差異,但她自己卻作為一個榜樣對電視機前的青少年產生了引導作用,因此這個人物本身便足以作為積極的空洞性重復的重要符號,同時她作為超情節人物出現時又是同一個符號的多次復現,不斷推動情節發展并使人物網絡趨于完善,又對劇作結構的豐滿度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消極的空洞性重復
空洞性重復不僅有積極類型,還有消極類型,例如神經官能癥便是典型的消極空洞性重復,患者不受控制地做無差異的同一動作,在心理上產生厭倦感。相比于積極類型,消極類型的重復在《隱秘的角落》出現得更為頻繁,人物在生活的困境中不斷循環,面對命運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復既有操作,缺乏改變的行動將人物推至瓶頸、陷入窒息。
這部電視劇從孩子的視角出發,對親子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可以看到劇中出現的孩子幾乎都成長于非正常的家庭環境中,孩子面對父母時的反應與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似乎都存在一定問題,而許多角色一直到結尾都在重復著這些有問題的相處模式,毫無疑問這是不利于少年健康成長的。
電視劇前半部分主要呈現朱朝陽與其父的相處困境——朱父第一次出現的場景被設置于賭博環境中,牌友夸獎朱朝陽成績優秀又考了第一名,他露出驚訝的神情,顯然對這個好消息并不知情,于是被牌友調侃不了解自己兒子,接著朱朝陽出現在場景中,他周身的裝束之舊與其父大把贏錢的舉動極不相稱,緊接著朱父帶著朱朝陽前往商場買新鞋。在這個短暫的動態場景中,觀眾很容易獲得一個信息點:朱父對兒子的忽略,因為一個在意兒子的父親不會允許兒子進入一個賭博環境中,亦不會忽視其成長過程中的重要階段。在此后的劇情發展中,朱父無意識地、不斷地重復這一態度,例如在兒女面前,只顧及女兒朱晶晶的任性,毫不在意朱朝陽被落在身后的尷尬處境;和朱朝陽約好慶生,臨到頭卻又爽約;在包中藏錄音筆試探兒子是否殺死朱晶晶;要求朱朝陽說謊應付警察只為保護妻弟王立……對兒子的忽視在這些生活事件中一步步加深,到最后,朱朝陽為王瑤和朱晶晶的利益讓步幾乎成了朱父的習慣性想法,顯然,這種重復對于兩個孩子的成長都極為不利:朱朝陽會逐漸與之疏遠,朱晶晶的刁蠻任性也會日益加劇。
相比于朱父無意識的重復動作,朱晶晶和王瑤的任性則是一種有意識的習慣。朱晶晶會在商場拉走為朱朝陽買鞋的父親,也會為了威脅他人自己踏上頂樓窗戶,在這個小孩子的意識里,占有和爭搶好像是理所當然的,最后她的任性將自己引向了一條不歸路。如果說朱晶晶的任性還可以用小孩子不懂事來解釋,那么王瑤對朱朝陽的刻意排斥便只能被闡釋為惡毒。從在商場門口的冷嘲熱諷到后來對朱朝陽的追趕打罵,再到樓道里張貼的殺人犯照片,甚至于后來放任弟弟王立恐嚇朱朝陽,這些事件盡管程度一點點加深,但其本質并無差異,那便是對一個少年的迫害,從這個意義上講,王瑤的重復性動作不僅對朱朝陽產生了傷害,而且最終也使她自己和弟弟深陷其中。
二、創造性重復與差異生成
在德勒茲看來,擬像是一種不具有相似性的“像”,如果說柏拉圖的摹本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礎之上的“像”,那么德勒茲則將擬像看作一種“非相似性”的“像”。從擬像的本質來看,擬像是在歧異性、差異之上被建構的,將非類似性內在化。[4]兩個本來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在重復過程中產生了差異,這種差異使得重復本身獲得了意義,并且讓人們關注到事物永恒輪回過程中差異生成的重要價值。
開播不久,很多觀眾便從兩位主角的名字中獲得了一些關鍵信息:朝陽與東升都象征著冉冉希望,并且這兩個人物在經歷、性格、智商等方面也具有極大相似性,因此他們也具有能夠組成重復模型的資質。但不同于嚴良和老陳這一組重復模型對正直品質的一致追求,朱朝陽與張東升的“像”又只停留于表面,從本質上看他們仍舊是不同的,因此是“擬像”,是具有差異性的創造性的重復。
導演對張東升的原生家庭和親人沒有直接的鏡頭描寫,而是通過他人敘述來展現——農村家庭出身的高智商青年,因與家境優越的妻子相愛而放棄直博機會,組建家庭,之后因出身一直不被妻子父母接納。因此張東升對待妻子和岳父母的態度總是謙卑的,他帶兩位老人爬山、隨時注意其情緒和需求、夸獎岳父攝影技術好、一回家便張羅著做飯……他對妻子的討好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哀求地問“我還有沒有機會”到假裝沒看到妻子和其他男人幽會再到最后哭訴“我就只剩下你了”,張東升與妻子的地位始終處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他希望獲得妻子的愛與目光,因此一遍遍重復著謙卑與哀求,但另一方面,他又在這個重復過程中壓抑了自我。人對欲望的適當壓抑有利于其進入社會秩序、正常成長,但壓抑一旦過度,便會產生反作用,從這個層面分析,最后張東升對妻子一家痛下殺手是完全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邏輯和人生軌跡的。
相比于對張東升的隱匿描寫,導演對朱朝陽的刻畫更加全面且直接。奧數比賽的好成績和平時考試的第一名都直接凸顯了這個少年不同于常人的智商,這與張東升的高智商人設相吻合,另外,朱朝陽對笛卡爾的喜歡和關注更是與張東升如出一轍。朱朝陽對父愛的追求同樣通過許多細節不斷重復:收到父親所買鞋子時瞬間的欣喜、聽父親說自己幼時量身高事件時的微笑、對兒時與父親一同逛游樂園的回憶、與父親一同游泳時的孩子心性……嚴良若有所思的一句“朝陽你真是變了好多,我記得你以前很愛說話,現在卻不怎么喜歡說話了”讓觀眾思考是什么樣的變故讓這個少年發生如此轉變,父母的離婚與父親對自己的忽視是朱朝陽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朱朝陽對于父愛一直是極度渴望的,但這種渴望在面對父親的另一個家庭時又不得不壓抑。朱朝陽面對父親的境況與張東升面對妻子時的情況是一致的,他們都在向另一個目標尋求關注,并通過重復性動作企圖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不同的是,兩人所用的方式和結果。朱朝陽在壓抑的過程中也會委婉向父親表達自己的想法,例如在發現父親偷偷錄音后,他沒有情緒失控,反而對父親說下一番極為煽情的言語,不論其中真心有多少,這個孩子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回曾經遺失的父愛,于是他的需求最終在父親的關愛和誓死保護中得到了滿足;而張東升對妻子則是一味地放低姿態,除了求妻子不要離開之外,他想不到其他方式來改善兩人關系,最終妻子并未按照他的預想來行動。
從東升到朝陽,他們在一種“像”的基礎上重復著欲望的壓抑和釋放過程,但最終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局,因此這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重復,差異的生成意味著困境可以在非同一化中被消解。
三、符合時代理想的啟蒙邏輯
李澤厚先生在討論“西體中用”“中體西用”時談到“體”最終不應該只談理論形態和思想體系,應該落實到社會存在的本體,即現實的日常生活。[5]對于當代影視文化的意義同樣可以做出如此要求,電視劇帶給觀眾的啟發不應當只是理論形式的引導,更多地應涉及現實生活,改變人應對事件時的處理方式。同時,這種涉及到日常現實的啟發應當與時代理想相符合,從而使處在混沌中的人們感受到啟蒙式的光輝。
在朱朝陽和張東升這一組創造性的重復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與自己所追求的那個對象的位置是失衡的,朱朝陽對父親的崇拜在前期壓倒了他對自我的重視,張東升對妻子的愛慕同樣壓制著他的個性,這種不對等的狀態不僅無法形成互尊互愛的良好動態循環,而且長久以往,處于劣勢的一方終會將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放置在處于優勢的一方身上,于是靈魂的自由亦會被無形的枷鎖所捆綁。后期的朱朝陽在重復張東升的過程中產生了創造性的差異,在看到糖水里的那一只蒼蠅后他驚覺自己與父親的關系早已不如當初純粹,因此他通過另一種自我剖白的方式使父親產生愧疚之感,愧疚之情轉化為消失多年的父愛,于是二者的位置重歸于平衡狀態,父慈子孝在一種計謀之下獲得兩全,同時,不再壓抑內心對父愛渴求的自由也回到了嚴良最初認識的那個狀態,松弛而自由的狀態。
古代封建社會的宗族本位制演變為當代的家庭本位制,人們對于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在《隱秘的角落》中,導演通過消極的空洞性重復類型凸顯非正常家庭可能使孩子形成的性格缺陷,從反方向呼吁觀眾重視我國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家庭教育。在母親的強勢控制下生活著的朱朝陽不斷渴求父愛,因出身而自卑的張東升不斷尋求妻子的認同,缺少父母溫情陪伴的嚴良養成了任性而為的性子,雙親去世的普普為救弟弟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即便是得到無微不至父愛的葉馳敏也因為母親形象的缺失養成了過度好勝的執拗性格……這些角色不斷重復一些行為或態度,最終使自己陷入困境無法自拔。當然,導演的目的并非旨在說明社會不允許非正常家庭模式的存在,而是熱切呼吁家長能使用更合理的教育理念對青少年進行引導。例如朱父如能夠平衡好兒女的關系,注意到雙方感受,或許能夠使兩個家庭更為溫馨和睦,再比如未曾在故事中露臉的張東升父母如果能教會其不卑不亢,在青少年時期便培養其正直善良的品格,或許便能阻止一場場悲劇的發生。
總而言之,《隱秘的角落》通過不同的重復類型展示了符合當下時代的思想邏輯,劇作精巧,散發著啟蒙光輝。
結語
《隱秘的角落》憑借詭異的基調、邏輯嚴密的情節與充斥著懸疑氣息的細節收獲觀眾如潮好評,但更多人感受到的并非只有劇本形式設置的精密,而是潛藏于形式背后的難以言喻但又啟發人心的思想啟迪。當下時代中關于家庭、個人的熱點問題在這一部懸疑劇中逐漸展開,故事的發展為觀眾提供了多種解決模式,總而言之,現實是開放的,思想是多元的,我們應該在一種去同一化的趨勢中尋找到對生活與存在的最佳定義。
參考文獻:
[1][2][美]尤金·W·霍蘭德.導讀德勒茲與伽塔里《千高原》[M].周兮吟,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9,8.
[3]許旺.僧道與農民——《紅樓夢》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超情節人物[ J ].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0(04):77-82.
[4]董樹寶.差異與重復:德勒茲論擬像[ J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9(04):28-34,191.
[5]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333.
【作者簡介】 曹 芳,女,江蘇南京人,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文化管理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0年度江蘇省地區橫向科研項目“鞏義、旬陽交通系統形象宣傳片”(編號:
2020h-1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