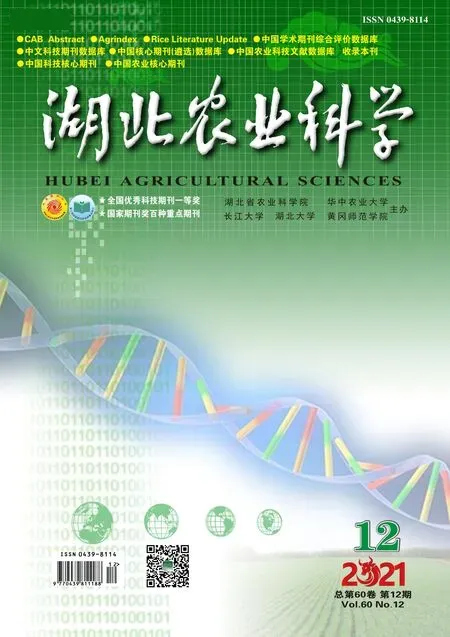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的邕河流域生態狀況分析
王國重,李中原,程煥玲,張繼宇,楊 柳,劉占欣
(1.黃河水文水資源科學研究院,鄭州 450004;2.河南省水文水資源局,鄭州 450003;3.河南省水土保持監測總站,鄭州 450008;4.河南黃河河務局,鄭州 450003;5.南陽市水土保持監督監測站,河南 南陽 473000)
生態安全是維護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生態環境不受威脅的狀態,是生態系統整體健康性和完整性水平的反映[1,2]。作為區域、國家或其他安全的基礎和載體,生態環境一旦受到污染或者退化,就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危及區域、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科學地評估區域生態安全、測度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就成為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研究的熱點。
目前,許多學者在多個方面對生態安全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主要理論性研究還是局限于國際通用的“壓力-狀態-響應(PSR)”[3-5]及其改進版“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6-8]模型,通過選取評估指標因子來構建評估指標體系,然后采用模糊數學、綜合指數等方法進行評估。由于評估因子的選擇、指標權重的確定具有很大的主觀性,使得評估結果與當地實際情況難免有所偏差[9]。隨著生態足跡模型的提出與不斷完善,逐漸走向成熟,不少學者將其應用于生態安全領域,陳世發[10]采用該模型評估了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1998—2007年的生態安全狀況,認為由于不斷增加的人類活動使其生態環境處于不安全狀態,需采取相應的措施;黃世光[11]測算了福建省古田縣2006、2011、2016年的人均生態足跡和生態赤字,以分析其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狀況;王金榮[12]根據1991—2005年的統計數據,應用生態足跡模型對內蒙古各地市的生態安全進行了評估;韓韋笑[13]將該模型與GIS技術相結合對祿豐縣的土地生態安全狀況進行分析,認為該縣當前的土地生態安全形勢嚴峻,亟需采用新的發展模式以保證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由以上分析和文獻搜索可知,生態足跡模型用于研究國家、區域層面生態安全的報道較多,但針對小流域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見。邕河小流域位于南陽市市區,2016年被河南省評為生態型清潔小流域,本研究嘗試采用生態足跡模型對其2016年的生態狀況進行評估。
1 研究區概況
邕河發源于南陽市郊紫山的東南部,流經獨山風景區和達士營、邢營、白塔、沙崗店、釣魚臺等村,在周寨附近注入白河,河長18.61 km,流域面積34.5 km2[14]。流域為狹長型、屬北亞熱帶大陸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年均氣溫14.9℃,多年平均降雨量805.6 mm、多年平均徑流深230 mm,降雨年內分布不均,6—8月降雨較為集中、約占全年的64%。流域土壤類型主要為黃棕壤、水稻土、沙壤土,平均土壤侵蝕模數為380 t/(km2·年),屬微度侵蝕;加之地形平坦、耕地采用小麥和玉米輪作方式并在周邊修建了農田防護林,有效地遏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流域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15]。
邕河流域跨越南陽市的宛城、臥龍兩區,按照《南陽統計年鑒2017》,2016年末流域總人口189.12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98%;國民生產總值536.351 5億元。
2 研究方法
2.1 生態足跡模型
生態足跡模型是加拿大學者William于1992年率先提出,并經不斷完善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定量測度人類對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16,17],該模型將人類的各種消費轉換為相應的資源消耗量,再將資源消耗與收納人類產生的廢棄物歸結為具有生態生產力的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等6類用地的面積,可由公式表示如下。

式中,Sj為各類生態用地的面積(j=1,2,…,6);Epi表示流域平均產量;CRi表示資源消耗量;i表示資源類型;Pi表示資源生產量;Ii表示資源進口量;Ei表示資源出口量。
各類生態用地具有不同的生產力,將各類用地面積賦以相應的均衡因子然后相加匯總就得到了區域的生態足跡,其計算如式(2)所示。均衡因子是在比較不同生態類型生物生產量的基礎上得到,國際上通用的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等用地均衡因子的取值分別為2.8、0.5、1.1、2.8、0.2、1.1[18]。

式中,EF為區域生態足跡;Si為各類生態用地的面積(i=1,2,…,6);Qi為均衡因子。
2.2 生態承載力與生態盈余
生態承載力是指區域內能夠供給人類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總和,也稱生態總供給。不同國家與地區的資源稟賦不同,其各類用地單位面積上的生態生產能力相差很大,即便同種類型的生態用地,單位面積上的生產能力也有很大差別。為此引入產量因子以利于比較,各類用地面積乘以相應的產量因子、均衡因子即為生態承載力,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C為區域總生態承載力;Gi為i類生態用地的產量因子,這里采用被廣泛應用的Wackernagel等[19]的計算值;Si為各類生態用地的面積(i=1,2,…,6);Qi為均衡因子。
生態盈余(ES)為生態承載力與生態足跡之差,如果ES>0,代表區域生態可持續;ES<0則說明其生態不可持續。
2.3 人均生態協調系數
人均生態協調系數能夠反映區域資源的稟賦狀況,可以彌補生態盈余的缺陷,公式表示如下。

式中,ds為人均生態協調系數;ec表示人均生態承載力;ef是人均生態足跡。由于ec、ef>0,顯然有1≤ds≤1.414,若ds越接近1說明協調性越差,反之,越接近1.414意味著其協調性越好[20,21]。
2.4 安全評估標準
以人均生態盈余與人均生態足跡的比值(安全指數)作為評估依據,依據文獻[17]將區域生態安全狀況劃分為病態、不安全、較安全、安全、極安全5個等級,如表1所示。

表1 生態安全分級標準

式中,B為安全指數;es為人均生態盈余;其他符號意義同前。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足跡需求
邕河流域生態足跡需求包括生物資源消費的生態足跡和能源消費的生態足跡兩部分,前者主要為農產品、林產品、動物產品,后者則為煤炭、汽油、柴油、液化氣、天然氣、電力等,各類能源足跡面積轉換系數由文獻[22]確定。邕河流域生物資源消費的生態足跡如表2所示,流域農產品消費類型主要是小麥、玉米、稻谷、紅薯、大豆、花生、蔬菜、芝麻、西瓜,相應的生態類型為耕地;林產品類型是蘋果、梨、桃、柿子、棗、葡萄、木材等,其生態類型為林地;動物產品以豬肉、羊肉、牛肉、奶類、禽肉、禽蛋為主,生態類型為草地;水產品主要是各種魚類、蝦類、水生植物的消費,對應生態類型為水域。能源消費的生態足跡如表3所示,流域能源消費類型主要是煤炭、汽油、柴油、液化氣、天然氣、電力等,其中,煤炭的人均消費量最高,其次是電力、天然氣,汽油的消費量最低。

表2 邕河流域2016年生物資源消費的生態足跡

表3 邕河流域2016年能源消費的生態足跡
3.2 生態足跡測算
邕河流域2016年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計算結果見表4。按照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要求[23],應將12%的生態生產用地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承載力計算時考慮了這部分面積。由表4可知,2016年邕河流域人均生態足跡為0.499 12 hm2,而實際的生物承載力是0.265 96 hm2,人均生態盈余為-0.233 16 hm2。

表4 邕河流域2016年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
3.3 生態安全評估
通過對邕河流域2016年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人均生態盈余的分析比較,并結合式(5)可知,該流域2016年的安全指數為-0.467 14,處于不安全等級(表5)。

表5 邕河流域2016年人均生態足跡及其盈余
3.4 討論
ES<0表明該流域從自然界獲取的資源量高于其生態供給量,由于其人均生態盈余大于-0.995 hm2,參照可持續發展程度分級標準[24,25],其發展程度為弱不可持續狀態,原因在于其發展模式是依靠自身的資源存量,難以持續;其人均生態協調系數為1.352 78,即ds<1.414,表明流域的生態處于不協調狀態。邕河流域人均生態足跡最多的是化石燃料,達0.388 08 hm2,其次是耕地、建筑用地、林地、水域、草地;耕地的生態供給面積最多,達0.256 66 hm2/人,為需求的2.91倍;草地的供需矛盾最為突出,究其原因,一是邕河流域牧草地資源匱乏,二是由于生活水準的提升群眾對動物產品的消費量也隨之增加。
4 小結
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結合邕河流域的實際對其2016年的生態安全狀況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其生態系統是不協調的,生態處于不安全狀態,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由于資料原因,未能將流域水資源利用足跡納入模型;在能源足跡中只考慮了吸收CO2所需用地面積,未考慮消納廢棄物所需的生態面積,故上述結果只能是一種樂觀的保守估計。在生態不協調、生態負盈余的情況下,針對邕河流域未來的發展而言,首先,需要改變當地群眾的生活習慣和消費方式,重視對自然資源的節約與保護;其次,要控制人口數量,提升人口質量、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單位面積自然資源的產量;最后,要善于發揮當地資源優勢,高效利用現有資源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