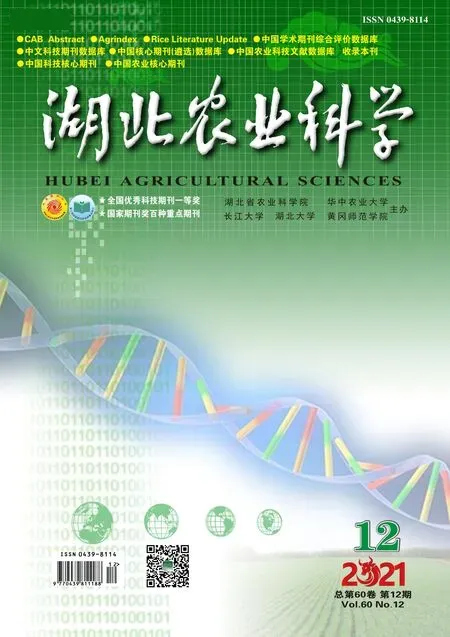基于MSPA的內蒙古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時空動態
林斐菲,謝苗苗,2,張 昊,海 鋒
(1.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土地科學技術學院,北京 100083;2.自然資源部土地整治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35)
內蒙古自治區(簡稱內蒙古)地處中國北部邊疆,其生態環境質量關系到本地區乃至全國和全世界的長遠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內蒙古時指出要努力把內蒙古建成中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然而由于特殊的氣候條件,加上城鎮化進程加快、礦產等資源過度開發等人為活動的影響,內蒙古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草場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十分嚴峻[1,2],生態用地質量受到嚴重威脅,進行生態用地時空動態的相關研究可為內蒙古生態屏障建設提供理論基礎。有關內蒙古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的研究較多,王宏亮等[3]采用多模型測度對內蒙古土地利用進行分析,發現1997—2014年內蒙古草地面積大幅減少,耕地、林地、建設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積有所增加;陳海燕等[4]對1980—2005年內蒙古的土地利用變化進行分析,得出內蒙古平原耕作區受國家政策影響,2000年后林地和高覆蓋草地開墾速度下降,但草地退化和荒漠化速度上升。這些研究顯示,20世紀末期以來內蒙古生態用地面積在不斷減少。
除數量動態以外,用地格局也會對區域生態安全保障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產生重要影響[5-7],其中,連通性的含義是景觀對生態流的便利或阻礙程度[8],生態用地連通性能夠為區域生態系統的穩定提供基礎[9]。形態學空間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方法是基于腐蝕、擴張、開運算、閉運算等數學形態學原理對柵格圖像的空間格局進行分割、識別、分類等的一種圖像處理方法[10,11],可以將目標像元按照形態分為連通性程度不同的類型,從像元層面上識別出連通性意義大的區域[12],與傳統連通性指數相比更能體現空間差異,從而為生態管理提供依據。近年來,MSPA的方法逐漸被用于生態規劃領域[13]。王越等[14]認為MS?PA為景觀格局分析、生態源地識別與結構性廊道提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供了科學的解決方法;王玉瑩等[15]運用MSPA對江蘇省的景觀格局進行分析,建立潛在生態廊道并形成省域生態網絡體系,提出優化生態網絡的策略。但是,有關內蒙古生態用地連通性及應用MSPA進行的研究較少。
為保障區域生態安全和質量,近年來內蒙古實施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措施以及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北防護林等國家林業重點工程和生態修復重點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16]。同時內蒙古近年來也在全面推進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工作。生態保護紅線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制度創新,對保障自治區生態屏障地位意義重大。對生態用地進行連通性分析可為生態保護紅線的科學劃定和完善提供依據。李國煜等[17]通過對比生態用地核心區與生態保護紅線的景觀格局指數和景觀連通性,提出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的生態用地保護策略,對現有生態保護紅線進行補充完善;吳健生等[18]對比了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范圍內外生態用地連通性的變化,提出了完善基本生態控制線策略的建議。對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進行研究,能夠為更好地實現內蒙古自治區北方生態安全屏障的功能以及提出和完善相關生態環境保護策略提供參考。
本研究以內蒙古自治區為研究對象,提取生態用地并應用MSPA將其劃分為7種連通性類型,通過轉移矩陣等方法得到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的時空動態變化特征,探討變化的驅動因素,并對內蒙古生態環境保護及其生態紅線劃定提出一定的建議。
1 研究區概況
內蒙古自治區地處中國北部邊疆,位于北緯37°24′—53°23′,東經97°12′—126°04′,南與黑龍江、寧夏等8個省區相接,北與俄羅斯和蒙古國毗鄰。全區氣候復雜多樣,以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為主。內蒙古自治區呈狹長的條帶狀,由東北向西南斜伸,橫跨中國東北、華北和西北3個地區,總面積為118.3萬km2,占全國總面積的12.3%,共轄12個地級行政區。2019年末全區常住人口2 539.6萬人,共生活著55個民族。內蒙古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煤炭資源保有量為全國第一。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包括內蒙古自治區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18年共8期土地利用數據。該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19],是以Landsat衛星遙感影像作為主要信息源,通過人工目視解譯獲取的精度為1 km的土地利用柵格數據。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態用地界定 應用MSPA方法首先需要在土地利用數據中區分前景像元與背景像元以得到二值柵格圖[20]。本研究定義生態用地的像元作為前景像元,即MSPA分析的輸入源,非生態用地的像元為背景像元。由于目前國內學者對生態用地的含義及分類體系還沒有統一的認識[21],本研究首先對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的內涵進行了界定。Guo等[22]提出了一種促進生態保護紅線管理的生態土地分類系統,包括基本生態土地、輔助生態土地、生產性生態土地和日常生活生態區四大類,主要參考該分類體系及實際情況,本研究生態用地包括了基本生態土地和輔助生態土地兩類。對于在生態用地分類時一直具有較大爭議的耕地,有研究指出除灌溉水田外的農業生產用地不屬于生態用地[23],考慮到內蒙古自治區的灌溉水田面積小且數量少,本研究生態用地不包含耕地。綜上所述,以中國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遙感監測數據分類系統為基礎,定義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用地,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分類體系
2.2.2 連通性功能類型內涵 MSPA方法將前景像元按形態分成7種類型,即核心(Core)、斑塊(Islet)、邊緣(Edge)、孔隙(Perforation)、橋接(Bridge)、環道(Loop)、支線(Branch)[10]。結合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的景觀特點,得到其生態用地MSPA連通性功能類型的定義與其生態學含義及表征(表1)[24-26]。

表1 內蒙古自治區MSPA連通性功能類型定義與生態學含義及表征
2.2.3 基于MSPA的生態用地連通性時空動態分析 應用Guidos Toolbox軟件將生態用地分為互不重疊的7種MSPA類型,得到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格局(圖2)。運行軟件主要步驟包括提取生態用地作為前景像元、關鍵參數設定和處理運算。需要確定的2個關鍵參數為Foreground Connectivity(前景連接)和Edge Width(邊緣寬度)。其中,前景連接參數可取值為4鄰域或8鄰域,軟件基于此進行邏輯運算[20],結合邊緣寬度識別出各景觀類型;邊緣寬度的取值要根據研究對象實際情況和研究尺度而定,其影響核心區的最小面積和前景像元分類[14]。通過反復試驗,確定本研究參數設置為前景連接為8鄰域,邊緣寬度為3,此時得到的核心區面積大小和分布位置與內蒙古自治區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27]和生態環境脆弱區[28]的空間分異大致吻合,較符合實際情況。

圖2 內蒙古自治區連通性功能類型格局
時間動態分析部分從面積結構、轉移矩陣等獲取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在研究期間的變化情況,以及7種連通性功能類型的內部動態關聯。將內蒙古自治區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3個區域,結合連通性類型內部土地覆蓋情況分析空間分異特征,東部地區包括赤峰市、通遼市、興安盟、呼倫貝爾市4個盟市,中部地區包括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頭市和鄂爾多斯市等盟市,西部地區由巴彥淖爾市、烏海市以及阿拉善盟組成。按照蒙東、蒙中、蒙西分別統計各類生態用地組分占該區域總面積的比例,通過各區域內生態用地連通性類型及其生態用地組分的差異表征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空間分異。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用地結構時序變化特征
從土地利用數據中提取出生態用地,統計并分析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各類用地面積的時序變化情況(圖3),有以下幾個特點。

圖3 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各用地類型面積變化情況
1)整體來看,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用地面積占比由79.842%減少到76.383%,共減少3.459個百分點。而非生態用地面積占比由20.158%增加到23.617%,增加了3.459個百分點。生態用地中,只有草地呈減少趨勢,研究期末相比期初其面積占比減少了5.879個百分點,2015—2018年減少的速度突增,因草地的面積遠大于其他生態用地,且減少百分比大,因此,其減少的面積數量遠大于其他生態用地增加的面積,導致生態用地整體面積占比減少。林地和沙地、鹽堿地、沼澤地的面積前期較為穩定,在2015—2018年增加幅度較大,研究期末沙地、鹽堿地和沼澤地面積占比較期初增加了1.730個百分點,面積增加較多,但由于其屬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和敏感區,面積增加會加劇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環境問題。
2)非生態用地中,耕地的面積占比在研究期間增加了1.720個百分點,城鄉、工礦、居民用地的面積占比增加了0.548個百分點。但總體來說,非生態用地占內蒙古自治區總面積的比例仍然比生態用地要低。
3.2 生態用地連通性時序變化特征
3.2.1 生態用地連通性總體變化特征 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中斑塊、孔隙和支線的面積占比均有所增加,其他類型的面積占比則在減少(表2)。連通性功能類型中,核心區面積最大,但其面積占比在研究期間不斷減少,期末比期初減少3.286個百分點。邊緣、環道和橋接面積占比均有所減少,其中,環道類減少了0.095個百分點,橋接區面積占比在1980年比非生態用地多,僅次于核心區,但到2018年時其面積占比減少了0.850個百分點,比非生態用地面積占比更少。斑塊、孔隙和支線面積占比均有所增加,其中,斑塊類面積占比增加較多,增加了0.623個百分點,孔隙類增加了0.249個百分點。

表2 1980—2019年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面積變化情況
3.2.2 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轉移矩陣 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7種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內部以及與非生態用地之間的轉換關系可以通過轉移矩陣來說明(表3),變化情況如下。

表3 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變化轉移矩陣
1)1980—2018年對連通性作用最大的核心區面積減少,對連通性作用最小的斑塊類面積增加。核心區的轉移中,有84.509%的核心區保留,其余主要轉出為橋接類;斑塊類的轉移中,有44.003%的斑塊保留,研究期初11.160%的支線、2.913%的非生態用地、2.310%的橋接轉移為期末的斑塊。其中,核心區向橋接類轉移,支線類向斑塊類轉移都屬于連通性意義高的類型轉移為連通性意義低的類型。
2)核心區之間連通程度降低,內部穿孔問題嚴重、聚集程度下降。1980—2018年,橋接區面積減少,使得核心區之間的連通程度降低,只有64.342%的橋接類在研究期末仍然保留為橋接;孔隙類面積增加,孔隙類越多說明核心區內部零散的非生態用地越多,期初28.011%的孔隙保留下來,2.904%的核心區、6.427%的環道轉為孔隙;環道類面積減少,說明核心區內部聚集程度在下降,只有32.068%的環道保留下來,其余主要轉出為核心區、橋接類和非生態用地。
3)較多的連通性功能類型轉移為非生態用地。研究期間非生態用地面積增加,期初有81.672%的非生態用地保留下來,另有41.841%的斑塊、40.544%的支線、19.950%的橋接、12.502%的邊緣轉移為非生態用地,轉移比例最大的是斑塊類和支線類。
3.3 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空間分布特征
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空間分布整體呈北部連通性高、南部連通性低的特征。比較各期數據,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的空間分布特征基本一致。核心區分布面積最大,2018年占內蒙古自治區總面積的43.899%,主要分布在東北部、中北部和西南部,這些區域主要為各大型生態功能區和生態敏感區,區域面積大且較為完整,連通性良好,具有較大的生態價值。橋接區面積僅次于核心區,2018年其面積占比為21.209%,主要分布在東南部和中南部,此區域主要為耕地和快速發展的較分散的城鄉、工礦、居民用地,生態用地破碎程度較高,連通性較差(圖4)。

圖4 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分布
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中的生態用地組分隨地域變化占比各有不同(圖5)。東部以林地和草地為主,中部以草地為主,西部以草地和沙地、鹽堿地、沼澤地為主。這是由于內蒙古自治區面積遼闊,橫跨東北、華北和西北三區,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勻,東部降水比西部多,蒸發量則相反,因此,內蒙古自治區的氣候也呈帶狀分布,東部主要是濕潤區、半濕潤區,中西部為半干旱區和干旱區。

圖5 各區域連通性功能類型生態用地組成
3.4 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構成結構特征
比較各期數據,內蒙古自治區連通性功能類型的生態用地組分中草地面積占比最大,由此,其對生態用地的連通性功能意義重大。
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地不僅面積在減少,其覆蓋率也在不斷降低。將高覆蓋草地、中覆蓋草地和低覆蓋草地分別提取出來進行分析后發現,占比最大的高覆蓋草地的面積較初始面積減少了31.278%,而低覆蓋草地面積減少了7.516%。
低覆蓋草地屬于極易受到破壞的生態用地類型,占內蒙古自治區草地總面積的20%左右。為凸顯低覆蓋草地對生態用地連通性的影響,以2018年的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利用數據為例,分別對生態用地是否包含低覆蓋草地2種情景進行MSPA分析。結果(表4)表明,生態用地包含低覆蓋草地時,連通性意義最低的斑塊類比未包含低覆蓋草地時減少了2.989個百分點,連通性意義最高的核心區增加了18.342個百分點。低覆蓋草地在現有生態用地連通性中貢獻較大,尤其對生態用地破碎化具有決定作用。相關部門需要重視低覆蓋草地的問題,防止其繼續退化。

表4 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有無低覆蓋草地連通性功能類型面積占比變化情況
4 討論
4.1 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變化原因分析
1)城鎮化速度快,建設用地侵占生態用地現象顯著。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的城鎮化水平增速較快[29],又因其位于重要的樞紐地帶,承擔著許多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和建設項目[30],建設用地需求量增多,大多只能依靠開發生態用地滿足建設開發需求,造成非生態用地面積增加,其中城鄉、工礦、居民用地2018年的面積較1980年增加了60.708%。此外,城鎮規模小、布局不合理,農村居民點布局分散造成的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低[30]使建設用地分割生態用地,阻斷核心區之間的連通。
2)資源粗放式開發經營與生態用地格局破碎化緊密相關。內蒙古自治區經濟飛速增長主要依靠于煤炭等能源產業[31],只追求經濟效益的粗放式開采經營使地表植被遭受難以恢復的破壞,造成草原塌陷等問題[32],核心區內部出現穿孔,生態格局趨于破碎;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地資源也十分豐富,但由于過度放牧,草蓄失衡以及草原退化、沙化、鹽堿化嚴重[33],導致草地面積大幅減少,覆蓋率和質量均降低。
3)特殊的自然條件造成生態環境脆弱敏感。內蒙古大部分地區的氣候是半干旱、干旱或極干旱,降水少且大風天氣多,造成其生態用地質量較差[1]。相對惡劣的自然條件造成內蒙古沙塵暴頻發,人為破壞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加重了這一過程,形成生態惡性循環。此外受到氣候因素的影響,生態工程受災面積增加[34],使得生態修復難度增大,生態環境被破壞的速度大于修復的速度。
4)總體變化趨勢較為穩定,可能原因如下:各類用地面積變化都比較大,但因內蒙古自治區面積遼闊,基數大,所以整體變化速度不突出;作為中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研究期間多項國家林業重點工程和生態保護修復工程在內蒙古推行實施,促進了內蒙古的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使得在內蒙古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其生態環境也保持了相對穩定。雖然這些措施在生態環境的治理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面積仍在減少及其連通性還在下降,說明采取更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十分必要。
4.2 生態用地內涵探討
生態用地的界定是對其進行連通性分析的前提,本研究提出的生態用地主要包括林地、草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地中的沙地、鹽堿地和沼澤地。沼澤地屬于濕地,應將其作為生態用地進行保護,但沙地和鹽堿地屬于植被覆蓋率低、生態功能低的用地類型,對其是否納入生態用地存在爭議。
Guo等[22]提出生態土地分類系統將鹽堿地和沙地歸于輔助性生態土地,還有研究將沙地、鹽堿地作為原生生態用地[35]、保全性生態用地[36]或者主導功能生態用地[37]等納入生態用地范圍內。由于干旱氣候條件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內蒙古自治區的沙地、鹽堿地數量多,幾乎全域都有分布,除蒙西的沙地面積較大外,其他區域的這兩類用地都零散地分布于其他各類用地,尤其是作為基本生態用地的草地,這使得草地破碎化,生態功能降低,如果不對分布于草地的沙地、鹽堿地進行保護和修復,草地生態系統會遭到進一步破壞,沙地、鹽堿地脆弱且敏感的生態環境也可能因為人類的過度干預而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害,最終影響區域生態安全。因此,本研究將沙地、鹽堿地納入生態用地范圍內,依據其形成原因和特征,采取不同的措施對其進行保護或修復。對于天然形成的沙地、鹽堿地以保護其間接生態功能和適當利用為主,提升其生態價值;對于人為造成草地、林地退化而形成的沙地、鹽堿地,以修復為主。
4.3 連通性分析結果的現實意義
1)對于內蒙古自治區來說,草地具有極高的生態價值,同時對農牧業的發展作用巨大[38]。本研究對比是否包含低覆蓋草地的2種情景,MSPA結果證明了如果低覆蓋草地缺失則會對區域生態用地的連通性造成極大影響,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低覆蓋草地與其他生態用地具有相當的功能和價值這一假設。低覆蓋草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較高覆蓋草地等其他生態用地更低,如石羊河上游草地覆蓋降低造成其生態系統服務能力下降[39],因此其對連通性的貢獻可能被高估。僅從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來看,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結果較為依賴低覆蓋草地。
2)2017年《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出臺,生態保護紅線上升至國家政策層面。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更偏重生態用地的功能性,未考慮生態保護紅線的整體格局,其內部空間孤立破碎、連通性差成為保護實施中的障礙[40]。本研究通過MSPA分析所提取出的連通性功能類型對提升生態保護紅線連通性具有參考意義,紅線劃定時,不僅應關注生態功能重要區和生態環境敏感區,對于一些連通性意義高的區域,也應該納入紅線范圍,同時要重視生態保護紅線內部空間的連通性和聚集程度,解決當前生態保護紅線區連通性不強的問題。不同生態功能對于具體地區的優先級不同,借助MSPA結果可以保護連通性強、更重要的功能,從結構優化的角度來提升生態保護紅線的整體功能性。生態保護紅線不應只作為生態環境安全的底線,更應該通過其連通各個生態子系統,發揮整體生態系統最大的生態效益。
5 小結
本研究根據內蒙古自治區實際情況,定義生態用地內涵,應用MSPA劃分連通性功能類型,分析生態用地及其連通性在1980—2018年的時序變化,空間分布與構成結構特征,并探究驅動因素,結論如下。
1)1980—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連通性功能類型較多轉為非生態用地,保留下來的生態用地的連通性在不斷降低,分析結果顯示,城鎮化速度加快、資源粗放式開發經營加上特殊的自然條件是造成生態用地面積減少、連通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時,研究顯示低覆蓋草地承擔了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的重要部分,然而其又是相對脆弱的生態用地類型。綜上,亟需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大對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
2)內蒙古自治區生態用地連通性北部較南部更高,但北部核心區內部出現穿孔問題說明其生態環境也在惡化,現狀不容樂觀。從空間分布上來看,內蒙古自治區不同區域的生態環境差異較大,在生態保護中可以因地制宜,揚長避短。
3)應用MSPA方法對生態用地連通性功能類型進行識別,不僅可以得到連通性整體水平,也能夠快速對連通性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判斷。同時,本研究結果可為基于MSPA優化生態保護紅線連通性格局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定依據,對中國北方生態安全屏障的建設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