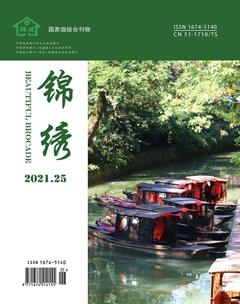當(dāng)代中西方藝術(shù)生態(tài)差異
現(xiàn)代主義之后,人們對(duì)日常生活和藝術(shù)的定義非常模糊,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今天,隨著社會(huì)的不斷發(fā)展,經(jīng)濟(jì)和工業(yè)的不斷進(jìn)步,出現(xiàn)了幾種新的媒介,當(dāng)代繪畫(huà)堅(jiān)持開(kāi)放、自由和探索的精神,勇敢地創(chuàng)造了各種表現(xiàn)形式和藝術(shù)風(fēng)格多樣化,這些通過(guò)西學(xué)東漸影響了中國(guó)當(dāng)代繪畫(huà),使得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在一個(gè)更自由更廣闊的海洋中,而新的表現(xiàn)形式和藝術(shù)風(fēng)格更直觀,更簡(jiǎn)單,更強(qiáng)大。這種純粹的藝術(shù)追求需要人的原始直覺(jué),這種審美傾向也從筆直上延續(xù)了當(dāng)代繪畫(huà),并照亮了人的生命本質(zhì)。
制度塑造文化,一種強(qiáng)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價(jià)值的共享上,在中國(guó)宋代時(shí)期因統(tǒng)治階級(jí)對(duì)藝術(shù)的崇尚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平民階級(jí)的受眾面增大,此時(shí)大眾表現(xiàn)出對(duì)藝術(shù)的酷愛(ài)、藝術(shù)家受到統(tǒng)治階級(jí)賞識(shí)。藝術(shù)家需要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支持,這在歐洲想來(lái)是有傳統(tǒng)的,從古代的藝術(shù)贊助模式到今天發(fā)達(dá)的藝術(shù)市場(chǎng)、各種民間官方項(xiàng)目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gè)成熟的生態(tài),相比較西方,中國(guó)還在邯鄲學(xué)步的階段,西方的美術(shù)體系之成熟,表現(xiàn)在一切操作都體現(xiàn)出以觀眾為導(dǎo)向的用心;提供信息的便捷程度方面,讓人們能在線上和線下輕松獲得全方位的參觀引導(dǎo),建設(shè)非常完美的網(wǎng)站,根據(jù)不同的游客中心、不同的參觀需求以一卡通的方式提供涵蓋市內(nèi)交通的博物館聯(lián)票,并且藝術(shù)和商業(yè)的結(jié)合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
每個(gè)時(shí)代的藝術(shù)觀的形成和變遷都是建立在對(duì)價(jià)值的破壞和重建的基礎(chǔ)之上的。我們從整個(gè)西方繪畫(huà)史中能夠看出它是一部語(yǔ)言時(shí)間的內(nèi)在要求與外在功用的磨合史。對(duì)再現(xiàn)如何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期成為風(fēng)格史基本導(dǎo)向的質(zhì)詢,能夠我們看繪畫(huà)在一種線性的演變過(guò)程里究竟遺失了什么,這也是當(dāng)代繪畫(huà)完成價(jià)值重建的基本前提,許多學(xué)習(xí)西畫(huà)的國(guó)人對(duì)西方的藝術(shù)史了解不多,他們對(duì)于西方藝術(shù)的學(xué)習(xí)僅僅局限在作品上,他們把重點(diǎn)大多放在“如何做”而不是“為什么”。
我曾一直自問(wèn),西方是寫(xiě)實(shí)的鼻祖,為何在這里卻不再視為圭臬?盡管經(jīng)過(guò)數(shù)百年的演進(jìn),對(duì)表象世界的再現(xiàn)一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和根深蒂固的接受習(xí)慣,在今天卻從各個(gè)層面被降級(jí)為一種語(yǔ)言類型,與其它方式平行而不再是主流。這背后有著完整的蛻變過(guò)程和西方人對(duì)自身視覺(jué)文化的持續(xù)反思。從文藝復(fù)興到法國(guó)大革命,寫(xiě)實(shí)技術(shù)的每一次飛躍都伴隨著激烈的權(quán)力斗爭(zhēng),將繪畫(huà)風(fēng)格的轉(zhuǎn)向置于歷史、宗教現(xiàn)實(shí)的框架內(nèi)考量,越來(lái)越揭示出,再現(xiàn)實(shí)質(zhì)是一種特點(diǎn)特定時(shí)代需求下的風(fēng)格突變,同時(shí)也表明繪畫(huà)史并不完全是按照邏輯進(jìn)化的過(guò)程。事實(shí)是,有很多實(shí)體證據(jù)征明,西方人早在古希臘羅馬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征服了再現(xiàn)技術(shù):古希臘瓶畫(huà)上一出現(xiàn)透視短縮法;從龐貝城出土的壁畫(huà)、埃及法尤姆出土的羅馬帝國(guó)統(tǒng)治時(shí)期的木乃伊肖像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古羅馬時(shí)期的畫(huà)家已經(jīng)掌握了精準(zhǔn)的透視和表現(xiàn)體積的嫻熟手法。但那時(shí)這些技巧還只是作為一種趣味,而不是大一統(tǒng)的準(zhǔn)則。
在對(duì)繪畫(huà)語(yǔ)言變遷的表述上,一般意義上的繪畫(huà)史傾向與將再現(xiàn)和普蘇的符號(hào)本能割裂開(kāi)來(lái)。實(shí)際的情況缺失是,兩種表現(xiàn)方式之余繪畫(huà),就像一部車套了兩各個(gè)性迥異的馬,本國(guó)藝術(shù)家在學(xué)習(xí)西洋藝術(shù)在看待這輛馬車時(shí)的視角是側(cè)面的看不到背后的另一匹馬。西方藝術(shù)發(fā)展至今也是在磨合這兩匹馬,使得兩匹馬用力的方向一致,這樣御者才能駛向自己的目標(biāo)。而兩者早在十五世紀(jì)曾奇跡般和諧共存于早期尼德蘭繪畫(huà)。就弗萊芒原始繪畫(huà)而言,盡管被視為平行于意大利的寫(xiě)實(shí)技術(shù)的發(fā)源地,卻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再現(xiàn)。在我看來(lái)其本質(zhì)是一種中世紀(jì)的風(fēng)格化表現(xiàn)和再現(xiàn)技術(shù)的折中,其中保留的鮮明的符號(hào)學(xué)特征。
今天的西方藝術(shù)史已經(jīng)擺脫孤立地關(guān)注風(fēng)格的方式,以圖像學(xué)作為研究方法,將風(fēng)格問(wèn)題置于特定語(yǔ)境內(nèi),揭示出一般的線性藝術(shù)史無(wú)法觸及的“形式真相”。尼德蘭繪畫(huà)在今天看來(lái)仍然是一種強(qiáng)大的圖像范式,在于它既是受時(shí)代語(yǔ)境催生的,優(yōu)勢(shì)出自實(shí)踐的立場(chǎng)。這一點(diǎn)在弗萊芒原始繪畫(huà)中表現(xiàn)為語(yǔ)言的高度兼容性,在十七世紀(jì)北部繪畫(huà)里表現(xiàn)為純粹的視覺(jué)趣味,,兩者分別從語(yǔ)言和觀念層面各自成功地使繪畫(huà)在內(nèi)、外兩種驅(qū)力的摩擦下找到了維系基本立場(chǎng)的方式。這也是為何西方繪畫(huà)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哲學(xué)和方法論的源頭。誠(chéng)如維特根斯坦所說(shuō),未來(lái)哲學(xué)的任務(wù)是對(duì)語(yǔ)言的剖析。深入到藝術(shù)實(shí)踐內(nèi)部,由內(nèi)至外地構(gòu)建一個(gè)新的認(rèn)識(shí)脈絡(luò),一成為當(dāng)代美術(shù)的核心工作。中國(guó)作為符號(hào)大國(guó),缺少的正是對(duì)視覺(jué)文化演變的內(nèi)在邏輯和結(jié)構(gòu)性外因的探討,尤其是需要將對(duì)當(dāng)代性的認(rèn)識(shí)構(gòu)建于科學(xué)的藝術(shù)史學(xué)觀之上。在本民族傳統(tǒng)和當(dāng)下藝術(shù)時(shí)間之間找到有效的對(duì)接方式。而這個(gè)人物,遠(yuǎn)不能期待孤立地在藝術(shù)內(nèi)部完成,而是需要一個(gè)從藝術(shù)價(jià)值的生產(chǎn)、詮釋到傳播的完整的系統(tǒng)工程。西方藝術(shù)家特有的、成熟的藝術(shù)觀、繪畫(huà)觀,既是尤其民族的審美基因和特殊的歷史決定的,也有賴于對(duì)自身藝術(shù)史的不斷重建和憑借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傳播體系打造的受眾基礎(chǔ)。我想在此論文當(dāng)中嘗試展開(kāi)的探討并不是藝術(shù)史,而是希望透過(guò)我對(duì)今日西方當(dāng)代藝術(shù)體系的方方面面的體驗(yàn),去理解那種成熟的藝術(shù)觀念得以在本國(guó)生根的土壤。
參考文獻(xiàn)
[1]萬(wàn)金良,《簡(jiǎn)明西方美術(shù)史》,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出版社,2013,第307頁(yè)。
[2]王婧,《原始藝術(shù)精神對(duì)現(xiàn)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影響》,《學(xué)術(shù)交流》,2009。
[3]丁寧,《西方美術(shù)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第6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龔田夫、張亞莎,《原始藝術(shù)》,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婧,《原始藝術(shù)精神對(duì)現(xiàn)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影響》,《學(xué)術(shù)交流》,2009。
[3]曹大霖,《原始繪畫(huà)與西方表現(xiàn)主義繪畫(huà)的異同》,《美與時(shí)代月刊》,2010。
[4]介聶,《藝術(shù)本質(zhì)和精神完善》,《人民政協(xié)報(bào)》,2015。
作者簡(jiǎn)介:
王棟(1995.05.14-),男,漢族,籍貫:遼寧葫蘆島,河北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油畫(huà)專業(yè)19級(jí)在讀研究生。
(河北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