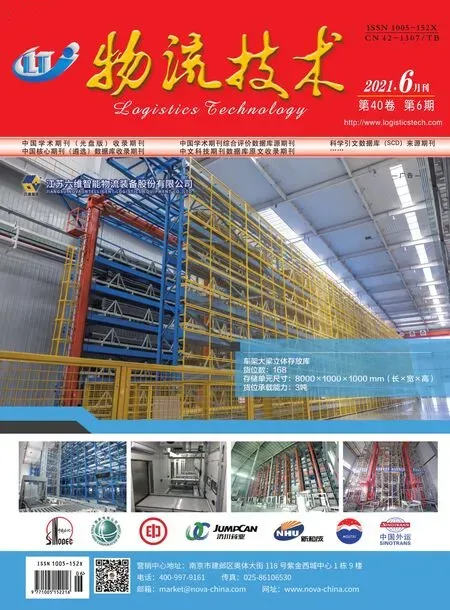南通市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分布特征及演化趨勢研究
劉 學,羅潔瓊,俞 越
(1.南通大學 藝術學院(建筑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2.南通大學 江蘇長江經濟帶研究院,江蘇 南通 226019;3.南通大學 交通與土木工程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0 引言
網絡購物的發展帶來城市居民購物習慣的變化,導致新的物流需求。運貨到家成為互聯網物流區別于傳統物流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這意味著互聯網物流必須滿足更加復雜的物流需求,末端物流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末端物流自提服務是網絡購物最后一米(last mile)的重要服務,其要求在人口密度高、空間模式混合和環境有限的城市內部空間中,滿足消費者更加復雜的物流需求[1]。因此,末端物流是第三方物流供應鏈中與消費者直接聯系,成本最高、配送組織最為復雜的環節,也是網絡購物模式中最重要且關鍵的物流基礎服務。
近年來,出于優化消費者購物體驗和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第三方物流中的末端物流在城市內部空間快速擴張,擴張的數量大致與城市內部人口經濟活動密度成正比。可以預見,城市的末端物流配送量將大幅度增加。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對末端物流空間分布特征進行研究,探討未來城市末端物流自提空間的演化趨勢,對于“互聯網+”背景下合理規劃末端物流空間、節省配送成本和提高消費者購物體驗具有指導意義。
1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近年來,網絡購物與物流發展社區化趨勢明顯。2016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印發《南通市“十三五”信息化和互聯網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該通知指出相關部門和行業要加強城市社區、鄉村地區、學校等場所的電子商務智能物流設施建設,推廣城市共同配送模式,鼓勵社區物業、村級信息服務站(點)、便利店等提供快件派送服務,加快完善“最后一公里”配送網絡。為了更加有效的實施這項政策,需要統籌分析南通各街道的面積、人口、道路等資源的差異性,為相關主體更好地規劃和配置末端物流網點提供指導建議。研究范圍包括崇川區、港閘區和開發區三個城區的21個街道,各個街道在發展時序、規模、空間尺度上存在較大差異。研究區域的矢量地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包括行政界線和道路分布,如圖1、圖2所示。

圖1 研究區域街道劃分

圖2 研究區域主要道路
1.2 數據來源
大數據時代,隨著電子地圖中關于地理位置服務業務的發展,以電子地圖興趣點數據(Point of Interest,POI)為代表的空間地理數據得到了完善與優化,成為研究城市空間的一類重要的地理空間大數據,其在更新速度、獲取成本和準確度(包含經緯度及地址)方面相較于官方統計技術數據有一定的優越性。POI數據是一種代表實際地理位置的點數據,通常包含名稱、類別、經緯度以及地址等基本地理位置的屬性信息。本文使用高德地圖作為POI數據來源,2018年1月從高德地圖提取南通三個區參與社區末端配送的POI點,共計290個,主要分為三類:快遞企業末端配送網點、菜鳥驛站、電商企業末端配送網點。
1.3 研究方法
1.3.1 最鄰近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本文首先以最鄰近分析判斷南通末端物流空間分布是否存在空間集聚。其指標為每個觀測點與最鄰近點的平均距離及隨機分布模式下與最鄰近點的平均距離的比值,指標值小于1代表空間點聚集,愈趨于0聚集程度愈高;指標值大于1則代表空間點分散。
1.3.2 核密度估計(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若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分布有集聚性,再以核密度估計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的分布密度與空間特征。每個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對周圍的影響會隨著距離愈遠而漸趨于0,對此可用核函數(kernal function),根據空間點分布特性估算其分布密度。
在核密度估計中,帶寬h的確定或選擇對于計算結果影響很大。本文通過試驗、比較不同帶寬1 000m、1 500m、2 000m和2 500m發現,1 000m帶寬相比其他帶寬,其空間差異大,且反映的地區類別較多。因此,確定1 000m帶寬以分析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分布特征。
1.3.3 局域Getis-Ord G*指數法。本文使用Getis A和Ord J.K.(1992)提出的Getis-Ord G*統計方法呈現南通三個區末端物流活動空間分布的熱點集聚區特征。其對每一個空間單元(街道)賦予一個指標值,代表該街道與鄰近街道屬性特征的空間集聚程度。若某街道與鄰近街道的末端物流網點比皆為高值,則該街道Getis-Ord G*值即為高值,為末端物流網點比例高的熱點區域(hot spot)。
具體步驟:(1)構建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密度指標,以街道為單元,計算街道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密度值;(2)通過Global Moran's I指數確定要素屬性值的空間自相關性;(3)依據所有要素都至少具有一個相鄰要素,且不與其它所有要素相鄰的原則計算空間矩陣閾值;(4)最后通過熱點分析探索南通市末端物流自提活動空間分布的熱點集聚區特征。
2 南通市末端物流空間分布特征
2.1 末端物流自提空間數量及密度特征
截至2017年底,南通城區范圍內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量共計290個。研究區面積約為372.09km2,人口約120.52萬人。本文首先采用兩類指標對各行政區域內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分布概況進行統計分析,見表1。一是總量指標,即統計各行政區劃內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的總體數量差異;二是密度指標,包括末端物流自提網點面積密度,即各行政區劃內每平方公里的末端物流自提營業網點數,用于表現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在不同區域的分布強度;三是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的人口密度,指各行政區內每萬人所擁有的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用于表現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各區域的供應服務強度。

表1 研究區域自提網點總量及密度特征
從圖3、圖4可以看出,這290個點在各行政區的分布和數量上存在差異。總體上呈現中心集聚、四周分散的態勢。統計顯示,崇川區已建成的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量最多,為160個,遠高于開發區和港閘區的網點數量。從末端物流網點的面積密度來看,南通三個城區的均值為0.7個/km2,其中,崇川區為1.6個/km2,遠高于均值,港閘區為0.48個/km2,開發區為0.36個/km2最低,表明崇川區作為老城區其末端物流網點空間集聚效應較強。根據各行政區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的數量和人口密度統計可以看出,南通三個城區每萬人約擁有2.4個末端物流自提空間,開發區的常住人口最少,其配置的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個數可達到每萬人3個,高于平均值,常住人口較多的崇川區和港閘區每萬人配置為2.25和2.24個的標準,略低于平均值。

圖3 研究區域自提網點密度指標

圖4 研究區域自提網點空間分布
在ArcGIS軟件中運用最鄰近分析工具箱,以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為研究對象,通過計算得到其平均最鄰近距離≈294m,而期望平均最鄰近距離≈608m,故最鄰近點指數R≈0.48<1。結果表明,南通末端物流在自提空間分布上表現為集聚的態勢,集聚分布特征顯著性較強。
2.2 基于核密度分析的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分布特征
2.2.1 基于分區的分布特征。運用ArcGIS軟件將搜索半徑設定為1 000m,對南通三個城區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的空間分布進行核密度分析。由圖5可以看出,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在三個行政區內分布不完全均衡,具有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其中,崇川區范圍內,環濠河區域分布密度最高,且分布的范圍遠大于其他片區;東部的觀音山新城區和南部的CBD新城區分布范圍和密度次之。港閘區范圍內,北大街商圈核心區分布范圍最廣,其次為北翼新城居住片區和西部居住片區;開發區的片區中心星湖101分布密度最高、范圍最廣,其次為北部五山居住片區和南部的蘇通科技園區。這些區段都是南通重要的居住、商業和高校集中的區域。

圖5 研究區域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核密度分布
2.2.2 基于道路網絡的分布特征。城市道路是連接居民和自提空間之間的通道,更是限制和影響末端物流空間布局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城市內部的還是外部的物流,都把交通作為影響其空間布局的重要因子[2]。本文引入南通城區城市交通道路網絡要素,通過統計分析等方法,對研究范圍內末端物流網點與城市內部道路網絡相關的布局特征進行探討。設定研究區域城市道路不同的搜索半徑,進行末端物流網點分布數量的統計,分析末端物流網點分布的道路指向性特征。具體做法為利用ArcGIS中的buffer分析工具對研究區所有城市道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作緩沖區分析,其分析半徑分別為50m、100m、200m,如圖6所示。對各緩沖區范圍內的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量進行統計,可以得出南通市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多集中在道路50m和100m的范圍內,數量共占到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總量的88.0%,這說明網點分布沿城市道路指向性明顯。其中,道路兩側50m范圍內的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量最多,共有165個,占到網點總量的57%。50-100m范圍內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數量為89個,占總量的31%。而100-200m范圍內末端物流自提網點有28個,占南通三個城區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總量的10%,其余還有8個位于道路200m范圍以外的區域。

圖6 研究區域自提網點與城市道路緩沖區分析
2.2.3 基于土地利用類型的分布特征。宏觀層面上,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呈現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中觀層面上,在ArcGIS軟件中對2017年南通城市用地現狀和末端物流自提網點進行疊合分析,研究網點的分布與城市內部不同功能屬性用地之間的關系。如圖7所示,統計得到約87%的布點位于居住用地、商務辦公用地和高校科研用地之中。可以看出,末端物流自提網點與用地屬性之間的關系也間接說明其需求和服務對象的產生主要依賴于居民日常生活的居住空間和就業空間。微區位層面上,譚如詩在對南京菜鳥驛站空間布局的分析中,通過對各地點名稱和地址描述進行詞頻分析,得出菜鳥驛站主要依托和服務于“大學”“小區”等居住空間,同時,“大廈”等就業空間和“公交”“地鐵”等相關出行空間也有所涉及[3]。

圖7 末端物流自提網點與城市用地現狀疊合圖
2.2.4 基于人口的分布特征。張智,等(2017)以深圳末端城市物流網點為研究對象,指出其空間分布除了和上文所提及的土地屬性及開發有關之外,人口規模也是其布點的主要依據。與商業網點的布局存在類似之處,末端物流網點的分布也是以市場自發導向為主,這意味著居民的需求是推動末端物流發展的直接動力,即人口規模決定了市場規模和服務對象規模等要素。因此,本文通過對人口環境的分析可以更加客觀地從供需角度反映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空間布局結構的規律。
首先以街道為尺度對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分布密度與人口密度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顯示街道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分布密度與街道人口密度兩者之間呈現高度相關性(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r值為0.956),即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分布與人口的分布有相同趨勢,兩者空間耦合程度較好。
其次,將各街道人口與網點密度進行空間分布情況的對比,深入分析各街道人口與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分布的空間相關性特征。按各街道人口密度和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密度值大小在ArcGIS進行分級可視化,生成圖8、圖9。
對比圖8、圖9可以看出各街道人口密度與末端物流網點分布密度的相關特征。研究區內各街道的人口密度分布以濠河圍成的老城區為中心,并以圈層式向外遞減,最終到達開發區最南端南通農場和港閘區最北端陳橋街道的人口密度低級區。末端物流網點密度同樣以老城區為中心密集并向外遞減的態勢分布,其總體分布格局與人口密度相似。
圖8與圖9在空間分布上仍存在一定的差異之處。在人口高密集區的城東、學田和虹橋街道,末端物流網點密度相應較高,但相比于高密度人口的街道分布更為聚集,高值區僅為學田街道,說明末端物流網點密度在人口高密度區的擴散程度還相對較低,可能原因為:這一地區為南通傳統的城市中心區,老人居住比例更高,房價租金高,城市空間狹窄,大多設置自提柜更加方便、經濟。外圍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但是末端物流網點密度相對較高的地區,如崇川區的鐘秀街道擁有郭里頭、中心、百花三大小商品批發市場群,開發區的新開街道是開發區片區商業、商務辦公中心,這說明末端物流網點的空間分布具有區域商業、商務指向性。

圖8 研究區域末端物流自提網點

圖9 研究區域各街道人口密度圖
2.3 末端物流自提空間集聚類型
采用局域Getis-Ord G*指數探索南通末端物流自提活動的熱點區域(如圖10所示)。根據表2的統計結果:以街道為單元,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密度符合熱點分析聚類模式統計特征,即用于檢驗的Z得分大于1.96且符合在95%置信度(概率似然值P<0.05)的P值要求的熱點區域共有7個,主要分布在崇川區的老城核心區和南部CBD區。其中新城橋街道和城東街道的Z得分分別為4.14和3.57,遠大于1.96,表明這兩個街區內末端物流自提網點密集分布,且被其它同樣具有高網點密度的相鄰街區包圍,是城市末端物流自提活動最為活躍的區域。熱點分析表明,以城市主干道工農路為中軸線,兩側的街區為末端物流自提活動熱點地區,工農路連接的老城核心區和南部CBD區作為南通城市居住、商業、商務等的雙核心,也成為末端物流自提活動空間格局的雙核心。

圖10 研究區域自提網點分布的熱點區域

表2 研究區自提空間熱點分析的統計特征
通過對熱點區域的可視化表達(如圖10所示),比較歸納7個熱點區域的分布格局和特點,可將南通市末端物流自提聚類區域分為以下三種空間布局模式:
2.3.1 人口集中-社區生活服務導向型。快遞公司設立的自提空間布局是以市場開發為導向的,其基本目標就是為消費者提供便利的取件服務,這其中兩個重點分別是消費者人口規模和便利的本質。因此,在擁有大量人口,尤其是網絡購物的主力軍年輕人集中居住的區域或者有取件便利需求的地區,容易形成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布局的集聚區域。圖中位于老城區的學田街道,是南通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屬于南通開發較早的大型居住生活區,其中沿著青年東路分布有南通工程學院、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南通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等多所高校,生活機能完善,擁有大量的本地居民、大學生和外來人口,從而促成了末端物流網點的發展與集聚。
2.3.2 商業集中-工作便利服務導向型。經常通過網絡購買商品的大多數為年輕人,擁有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通常表現為工作壓力大、工作時間緊迫,午休時間在單位附近解決,工作時間與快遞配送時間兩者之間的匹配度更高。即處于工作空間,居民在取件的時間支配上更加自由、靈活[3]。因此,對于在商業商務密集地區工作的居民而言,綜合寫字樓和獨立單位用樓中物業管理良好,一般會在一層設置自提柜,或者與樓宇邊上的連鎖超市、私人商鋪結合,提供自提服務。圖中的和平橋街道和文峰街道,是老城核心區和新城CBD區商務辦公樓高度集聚的區域,如鼎典大廈、如云公館、鳳凰文化廣場、南通大飯店財富中心、圓融中心等。大量的商務辦公人群以及封閉式的就業空間可依托的商業和服務設施較多,從而促成兩個街道末端物流自提網點的聚集。
2.3.3 交通便利-出行鏈導向型。在網絡購物發展的背景下,由其所派生出的自提行為,已經成為居民家務活動的一種類型,是城市日常活動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自提行為需要居民克服取件的空間位移和時間制約,因此其出行通常會和購物、上下班等出行鏈結合,從而節省居民的時間和精力。國外許多城市自提空間的布局往往與停車場、加油站、地鐵站等交通節點相結合。例如,英國城市依托超市、加油站等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的CDP(Collection and Delivery Point)。我國由于城市城區范圍內人口密度高、城市空間模式混合化以及城市居民的出行習慣更加多元化,自提空間一般較少依托交通站點布局,大多數都是分布在交通可達性好、沿著城市居民上下班、上學等主要活動線路的節點。由老城區鐘秀、城東、新城橋、學田街道一直延伸到南部新城區文峰街道的工農路作為南通早期建設的城市主干道,道路兩邊居住、商業、商務辦公等功能活動密集分布,便捷的交通方便了人流和物流的流動,從而使末端物流網點以此為導向而聚集。
3 新的流動性下末端物流活動的空間結構演化
3.1 虛擬商業在實體空間中的主要存在形式
網絡購物的盛行,衍生出了虛擬商業空間,其在實體商業空間中藉由物流、信息流、現金流的流動形成一個虛實交織且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空間,而這樣以虛為主的空間也形成了全新的城市商業空間形態和結構。全新的城市商業空間結構中包括因為新興產業的出現,而衍生出的新的空間類型——末端物流活動空間,其在城市內部空間高密度布局,從而方便商品在城市中的流動。
虛實交織的商業空間中,商家在實體空間的分布呈現了末端物流空間的布局,使得網絡經濟在城市實體空間的流動程度更大,除此之外,隨著網點的實體空間與虛擬商業空間之間的互動更加頻繁和緊密,網點的功能角色和所提供的服務也日趨多元化[4]。
3.2 空間分布社區化,充斥城市內部空間
在網絡購物中,物流與倉儲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網購業者相繼投入大量的前期資金建設末端物流空間,以“降本增效”和“用戶體驗”為核心,提高消費者未來再次網購的機會[5]。例如,韻達通過20 000余個自建門店,16 650余個合作便利店,140 000個智能快遞柜,進一步縮短送貨到家的時間,強化末端100m的攬派服務。可以看出,末端物流在城市內部空間四面八方延展,通過自建空間、與城市便利店結合等方式,增加電子商務產業在城市中的可達性,末端物流空間在城市中布局社區化,充斥城市內部空間。
3.3 功能日趨多元化,成為線下短距離消費體驗的場所
末端物流網點充分利用其接近生活圈的稀缺資源,建立了一種離用戶足夠近的“實體店”,其在配送快遞的同時,功能日趨多元化,包括:(1)分布式倉儲點,網絡購買者更加便捷地提貨;(2)退換貨的接收點;(3)大數據支持,根據社區特點,明確目標人群的構成,推薦目標人群最需要的商品,并提供陳列和展示,消費者可以線下體驗,站點“千點千面”,站點的結構和功能更加合理化;(4)引流,可以通過線下的一些活動和渠道將目標客戶有效的導流到線上店鋪。
可以看出,末端網點不再僅僅是一個包裹的收發站點,而應該以提高目標人群服務為導向,成為一個標準接口,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成為互聯網時代新零售渠道之一。例如,2018年4月歐萊雅品牌與菜鳥驛站合作,消費者可以通過手機天貓或是菜鳥驛站網點掃碼線上下單,立即在菜鳥驛站線下領取。菜鳥驛站利用大數據平臺分析購買歐萊雅化妝品的人群特征,定位為24歲以下的年輕女性,且大學生占比很高,其從全國4萬個菜鳥驛站的點挑選了750個目標用戶最多的站點,300個在學校,450個在社區精準定位,半個月的時間,吸引了30萬用戶,用戶總量比去年翻了一倍。證明從菜鳥驛站精準切入潛在消費者人群,是完全可行的新零售渠道之一。
4 結語
本文的背景是互聯網時代新興產業的出現,導致傳統零售業產業結構的轉型,著重分析新興產業之一——物流倉儲業的末端物流的空間活動。首先,基于核密度分析,從分區、人口、道路和土地利用四個方面,分析末端物流活動的空間分布特征,得出以下四個結論:(1)南通末端物流自提空間在三個行政區內分布不完全均衡,具有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2)網點分布沿城市道路指向性明顯;(3)80%以上的網點位于居住用地、商務辦公用地和高校科研用地之中;(4)街道尺度上,網點密度總體分布格局與人口密度相似。其次,采用局域Getis-Ord G*指數,基于21個街道尺度,探索南通末端物流自提活動的熱點區域。統計結果分析顯示,南通末端物流活動存在7個熱點區,歸納總結這7個熱點區的分布格局和特點,可將南通市末端物流自提聚類區域分為以下三種空間布局模式:(1)人口集中-社區生活服務導向型;(2)商業集中-工作便利服務導向型;(3)交通便利-出行鏈導向型。
在此基礎上,本文歸納了新的流動性下末端物流活動的空間結構演化趨勢:(1)虛擬商業在實體空間中的主要存在形式;(2)空間分布社區化,遍及城市空間;(3)功能日趨多元化,成為短距離線下消費體驗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