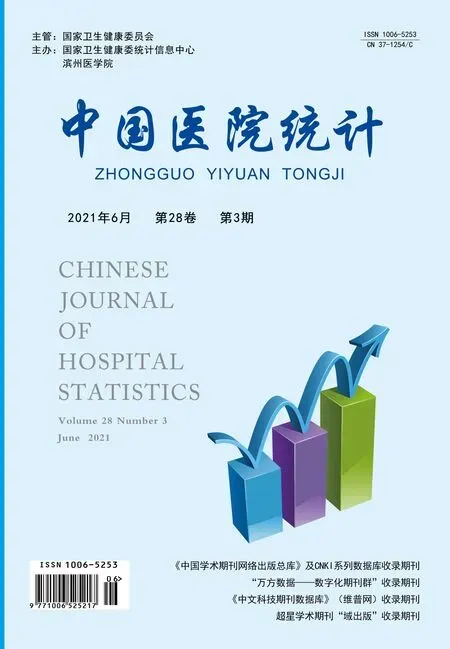成年期腰圍個體內變異與新發高血壓關聯的縱向隊列研究
趙相娟 董玉燕 吳喜梅 高 杰
山東大學附屬山東省婦幼保健院,250014 山東 濟南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飲食結構、生活習慣等方面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人群肥胖和高血壓患病率呈增長趨勢[1-2]。最新數據顯示,我國35~64歲成年人的超體質量率為38.8%、肥胖率為20.2%、高血壓患病率為27.9%[3-4]。肥胖和高血壓以及所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帶來了嚴重的疾病負擔[4-5]。研究肥胖引起高血壓發生發展的病因模式并進行早期干預,對于預防和延緩心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義[6]。
已有大量文獻通過橫斷面和隊列研究證明肥胖是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7-9]。肥胖測量有體質量指數(BMI)、腰圍、腰臀比和腰身比等多種指標,我們通常用BMI作為肥胖定義指標,例如我國CDS代謝綜合征診斷標準中將BMI>25 kg/m2定義為超體質量和肥胖[10]。而國際標準則是采用腰圍來定義中心性肥胖(國人男性腰圍>90 cm、女性腰圍>80 cm)。腰圍是反應腹部的脂肪含量,既往研究表明腰圍相對于BMI對預測高血壓發生風險更為敏感[11-13]。除關注腰圍絕對水平與高血壓的關聯性之外,縱向隊列的腰圍重復測量數據所含有的變異信息同樣值得關注[14-16]。本研究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縱向隊列數據,研究5 723名成年人腰圍的動態變化與新發高血壓之間的關聯性,探討腰圍變異與高血壓潛在病因的關聯,為我國肥胖者的健康管理、高血壓早期預防政策制定提供流行病學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自CHNS的1989年至2011年間9輪調查數據。調查覆蓋遼寧、黑龍江、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在內的9個省份。采用分層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方法,第一階段抽取調查省市 (自治區),第二階段調查隨機抽取城市和縣,第三階段抽樣時抽取居委會以及村莊,第四階段隨機抽樣時抽取調查戶[17]。根據本研究的目標,研究對象選取在調查時年齡為20~60歲、腰圍在65~130 cm、并且在研究開始時尚未診斷為高血壓的成年調查對象。根據CHNS數據庫的隨訪資料,了解每個研究對象高血壓疾病的發生發展狀況,并且剔除了每個研究對象發生高血壓后的隨訪記錄,在此基礎上篩選出隨訪記錄4次以上的個體。剔除沒有或者無法追查到年齡、腰圍、高血壓患病情況的樣本,最終納入的研究對象為5 723例。
1.2 研究指標
人口統計學及行為因素指標:包括性別、年齡、地區、受教育程度、每日能量攝入(包括脂肪、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飲酒、吸煙情況等。腰圍:經臍部中心的水平圍長,或肋最低點與髂嵴上緣兩水平線間中點線的圍長,用軟尺測量,在呼氣之末、吸氣未開始時測量。以cm為單位記錄到小數點后一位,測量2次取平均值。
腰圍變異指標包括極差(R)、標準差(S)、變異系數(CV)和變化速率(K)。極差:單個觀測對象在隨訪過程中的最大和最小腰圍之差;標準差:單個觀測對象隨訪過程中腰圍離均差平方和除以自由度(n-1)后開平方;變異系數:單個觀測對象隨訪過程中腰圍的標準差除以均數;線性斜率:單個對象分別建立隨訪過程中的縱向腰圍測量與年齡線性回歸,回歸方程的斜率即為變化速率。極差、標準差和變異系數3個變異指標衡量了在隨訪過程中的個體內腰圍變異程度,其中變異系數考慮了腰圍的水平,以便于不同腰圍水平個體之間比較。線性斜率則衡量了在隨訪過程中個體內腰圍的整體增長速率。
1.3 研究結局
高血壓定義:收縮壓>140 mmHg(18.7 kPa)和/或舒張壓>90 mmHg(12.0 kPa)、或服用降壓藥者或在醫院就診被確診為高血壓的研究對象定義為高血壓結局。血壓測量使用汞柱血壓計,坐位,測前至少休息15 min,取Korotkoftt′s第一音為收縮壓,消失音為舒張壓,每個被測量者測量3次,取平均值。
1.4 統計學方法
按照新發高血壓結局對研究對象進行分組,分為未患病組和高血壓組,對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其中服從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以均數和標準差進行描述,定性資料用頻數、率或構成比描述。對高血壓組和未患病組間差異進行比較,定量資料采用成組t檢驗,定性資料組間差異比較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采用R語言進行數據整理和分析。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腰圍變異指標對高血壓結局發生的影響。在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為探討腰圍變異指標對新發高血壓的獨立作用,除校正基線年齡、性別、地區、吸煙、飲酒等協變量外,校正了基線腰圍和基線血壓水平。對腰圍變異指標以及其他連續型變量均進行標準化,進而估計得到其標準化偏回歸系數、優勢比(OR)及其95%置信區間(95%CI)。為更好地反映腰圍變異和新發高血壓之間的劑量反應關系,對腰圍變異指標按照四分位數分組,編制啞變量。以最小四分位組為參考,求得其余3個分位數組與高血壓相關的標準化OR及其95%CI,作森林圖。
2 結果
2.1 基線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5 723名研究對象,其中男性2 597名、女性3 126名,基線平均年齡為(34.8±8.8)歲。平均隨訪年限為(11.6±4.1)年,隨訪期間新發高血壓患者為1 415名。在新發高血壓組和血壓正常組間,基線年齡、性別、既往吸煙率、經常飲酒率和血壓的差別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入選研究隊列樣本的基線資料
2.2 腰圍變異指標
計算隨訪期間的腰圍變異指標,包括標準差(S)、變異系數(CV)、極差(R)、線性斜率(K)。新發高血壓組和血壓正常組的平均腰圍分別是80.9 cm和77.6 cm,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新發高血壓組和血壓正常組的腰圍標準差、變異系數和極差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新發高血壓組和血壓正常組的個體內腰圍線性斜率的中位數分別是0.59 cm和0.49 cm,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表2 研究對象的腰圍與變異指標情況
2.3 腰圍變異指標與新發高血壓的關聯性
校正基線年齡、性別、隨訪年限、吸煙和飲酒情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腰圍指標與新發高血壓的關系。基線腰圍和平均腰圍的標準化OR分別為1.05(95%CI: 1.04~1.06)和1.07(95%CI: 1.06~1.08);在校正基線腰圍和基線血壓水平的情況下,腰圍變異指標與新高血壓的關聯均有統計學意義,腰圍的標準差、變異系數、極差和線性斜率的標準化OR分別為1.02(95%CI: 1.01~1.03)、1.01(95%CI: 1.00~1.03)、1.01(95%CI: 1.00~1.03)和1.05(95%CI: 1.04~1.06),此外,為探討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腰圍指標的效應,在多因素logistic回歸中納入性別與腰圍指標的交互作用項,各腰圍變異指標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項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腰圍變異指標與新發高血壓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為進一步反映腰圍變異指標和新發高血壓之間的劑量反應關系,將腰圍變異指標劃分為四分位數,以最小分位組為參考,求得其余3個分位數組與高血壓相關的標準化OR及其95%CI。腰圍標準差、極差和變異系數指標的上三分位數組(Q2,Q3,Q4)與參考組(Q1)相比,OR值在1.03~1.06之間(P<0.05),線性趨勢檢驗無統計學意義(P>0.05);腰圍的線性斜率上三分位數組(Q2,Q3,Q4)與參考組(Q1)相比,OR值分別是1.06、1.11和1.14,線性趨勢檢驗有統計學意義(Ptrend<0.05)。見圖2。

圖2 腰圍變異指標四分位數與新發高血壓關聯的森林圖
3 討論
以往隊列研究已經證明了兒童期和成年早期的腰圍水平是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并在肥胖的防控指南中按照腰圍的絕對水平定義肥胖標準。本研究基于CHNS隨訪10余年的前瞻性縱向隊列數據,所有研究對象至少具有4次高血壓發病前的腰圍測量,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的可能性非常小。本研究重點關注成年早期腰圍變異和增長速率,通過較為簡單的統計指標定義了個體的腰圍變異指標(包括極差、標準差、變異系數和線性斜率)。使用多因素logistic模型證明了成年早期較大的腰圍變化速率和變異與高血壓風險的增加有關,而且該關聯獨立于腰圍的水平。
本研究的縱向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線性斜率的標準化OR值更大、并且森林圖顯示具有顯著的劑量反應趨勢。因此,線性斜率可以看作是更好的新發高血壓預測指標。值得注意的是,在表2的腰圍變異指標描述中,本研究發現腰圍標準差、變異系數和極差在高血壓和血壓正常組差別沒有統計學意義,而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中,在校正了協變量(特別是基線腰圍)情況下,腰圍的變異指標與新發高血壓的關聯性均有統計學意義。為了說明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結果不一致的原因,本研究計算了腰圍變異指標(標準差、變異系數、極差和斜率)與基線腰圍水平的Pearson相關系數,分別是-0.070、-0.185、-0.102和-0.347。線性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基線腰圍水平與這3個腰圍指標均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成年早期的基線腰圍水平比較低,則在成年期的個體腰圍變異程度較大,需注意保持腰圍水平、控制腰圍變異,以便預防未來高血壓的發生。
本研究關注成年期腰圍的整體變異特征,而按照生命歷程理論,不同年齡組和性別的變異特征和效應可能不同。本研究探討了性別與腰圍變異指標的交互作用,發現交互效應項均無統計學意義,表明男性和女性的腰圍變異指標的效應具有同質性,男性和女性均需要注意控制腰圍的變異。由于本研究的變異指標計算要求具有一定的重復測量記錄,若按照年齡組分層則無法保證變異指標計算的穩定性。縱向隊列重復測量次數的限制具有局限性,本研究未按照年齡組進行分層分析。
本研究所觀察到的成年腰圍變異與高血壓關聯的潛在機制尚不清楚。體質量變異的決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遺傳因素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肥胖相關的FTO基因是具有導致肥胖測量變異的[18]。此外,個體腰圍的變化可能是反映人體對環境變化的反應或適應的一種基本特征。當環境有利于腰圍增加時,由于環境變化而導致腰圍變化的趨勢會增加發生高血壓的風險[19-20]。腰圍變異與腰圍水平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雖然基線的腰圍水平較低,但未來可能具有較大的腰圍變異和增長速率,仍需要控制好腰圍的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較低的腰圍變異可能反映了即使面對肥胖環境也有保持穩定體質量的傾向。后續需要更多研究來確定其他影響腰圍變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