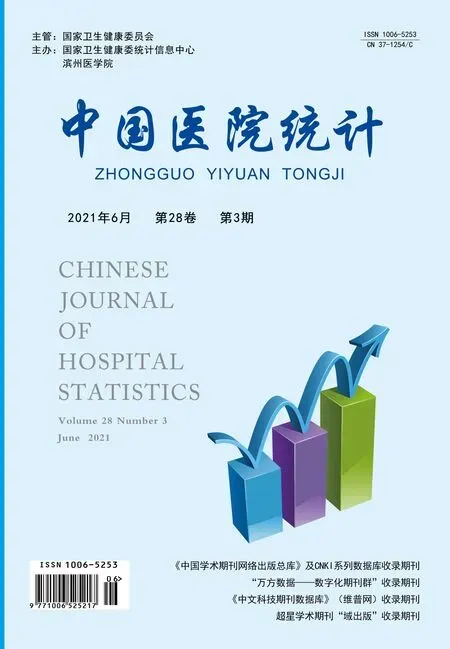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公眾認知、態度和應激反應調查
孫 聰 劉海霞 范思語 呂 鵬
1 煙臺市芝罘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64003 山東 煙臺;2 濱州醫學院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264003 山東 煙臺
應激反應是指機體在各種內外環境因素及社會、心理因素刺激時產生的全身性非特異性適應反應,是各種過強的不良刺激,以及對它們的生理、心理反應的總和[1]。當一個生命體所面對的事件,比如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打破了自己的平衡和承受能力,或超越了自己的應對能力時,所產生的一種應對反應。這種反應不僅會出現生理上的不適,更主要的是會產生心理上的困擾。COVID-19的暴發,擾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許多人開始擔憂、焦慮,甚至出現過度恐懼、緊張不安等應激反應[2]。北京大學研究人員在《柳葉刀》上報道說應對公眾心理障礙和實施心理危機干預被納入31個省市自治區啟動的頂級公共衛生應急響應;國家衛健委也發布了促進疫情期間各類人員心理危機干預的指導方針[3],提示COVID-19暴發時期,大眾心理應激和危機干預至關重要。本研究在疫情急劇上升時期,通過問卷調查了解公眾群體的認知與態度,分析公眾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的應激反應及其影響因素,為增強人們對疫情下應激反應的調節和應對能力,實施有效的心理干預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公眾群體為研究對象,在COVID-19疫情爆發感染人數快速上升時期,采用問卷星線上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發布和截止時間為2020年2月1日至2月25日。實際調查結束數據顯示,具體填寫日期為2020年2月2日上午8時58分至22日上午9時11分,99.5%的人是在2020年2月2日至2月15日填寫。阿里健康·健康報實時跟蹤數據顯示(國家衛健委宣傳司指導發布),此時間段為新型冠狀病毒新增確診病例人數快速上升時期。
1.2 測量工具
自行編制《公眾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認知及應激反應調查問卷》,問卷包括2部分內容:(1)認知與態度調查內容參照王磊等[4]設計問卷,主要包括對COVID-19疾病的了解、關注和態度,對周邊疑似患者的關注和態度,外出和在家的行為與感受等內容;(2)應激反應測量,采用姜乾金等編制的《應激(壓力)反應量表(SQR)》[5],該量表包含情緒反應(FER)、軀體反應(FPR)和行為反應(FBR)3個維度,采用1~5等級計分法,以條目總分(SR)表示應激(壓力)反應程度。本研究中問卷和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數分別為0.798和0.961,KMO分別為0.742(P<0.01)和0.793(P<0.01),問卷較為適用。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不同群體應激反應得分比較,滿足正態性和方差齊性采用t檢驗,不滿足則采用t′檢驗或秩和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收回問卷585份,有效問卷585份,有效率100%。男女各占40.3%和59.7%;年齡集中在21~40歲,占總人數的82.4%;48.5%來自于城市,城鎮和農村各占21.5%和29.9%; 59.8%為本科學歷,初中及以下占5.5%,學生占56.6%。見表1。

表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n=585)
2.2 公眾對COVID-19的認知與態度
2.2.1 公眾對COVID-19的認知情況
585名被調查者中96.6%的人知曉該病,其中14.7%的人對COVID-19非常了解,51.1%的人比較了解;對于預防措施,分別有24.4%和50.3%的人反映非常了解和比較了解;從疾病知識獲取渠道來看,31.6%的人是通過網絡了解的,其次分別是通過電視/收音機渠道和親人朋友了解。見表2。

表2 公眾對COVID-19的認知情況(n=565)
從人群感染及其風險認知來看,在調查的585名調查對象中,有3人被確診,占調查總人數的0.51%;5人回答其家人被確診,占總人數的0.85%;9人回答其朋友被確診,占總人數的1.54%;71人回答其周邊有不熟悉的人被確診,占總調查人數的12.14%。當被問到“認為周邊的親朋好友是否有可能被傳染”時,66.7%的被調查者認為“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分別有3.7%和29.6%的人認為“非常可能”和“可能”。
2.2.2 公眾對COVID-19的關注和態度
63.2%的人時刻關注COVID-19,3.8%的人漠不關心或稍有關心。39.5%的人在一天中會使用0~<1 h的時間去了解或瀏覽該疾病最新信息,32.0%的人1~2 h,2 h以上者達到24.6%。從關心信息來看,主要關注疫情進展、預防措施、科學研究進展等。98.4%的人在網絡平臺上看過關于新冠疫情的報道;61.6%的人在這些平臺上傳播過關于COVID-19的預防或防治知識;23.9%的人給予過捐款或物資幫助。對身邊感染者的態度來看,88.5%的人選擇“隔離,并提供關心和幫助”;對于從武漢回來的親朋好友,75.2%的人選擇勸他主動找有關部門或醫院登記并隔離觀察。見表3。

表3 調查對象對COVID-19的關注及態度(n=565)
從疫情給人帶來的影響來看,40.68%的人在過去一周從來不出門,28.89%的人一周出1次門,9.58%的人每天都出門。大家宅在家里的主要娛樂方式排在前5位的是:玩手機/電腦、看電視/電影、讀書/學習、與人聊天和聽歌/唱歌。而從疫情對個人的最大影響來看,27.4%的人反映是工作學習,27.1%的人認為是生活,還有10.8%的人直接反映是心情狀態。
2.3 大眾群體應激反應情況
調查人群應激反應總得分為52.61分,與無特殊應急事件時期普通健康人群(作為常模)[5]無統計學差異,心理(FER)、軀體(FPR)、行為(FBR)反應維度得分均有統計學差異,心理反應得分高于常模,而軀體和行為方面反而低于常模,見表4。從不同變量應激反應得分比較來看,人口學特征變量和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認知變量對應激反應得分無影響(P>0.05);而大眾在網絡平臺上表達、傳播行為對應激反應總得分均有影響(P<0.05),在平臺上表達過對于新冠疫情的擔心與恐慌的大眾的應激反應得分明顯高于沒有表達過的人群,在平臺上傳播過新冠疫情的防治知識大眾群體的應激反應總得分和軀體反應得分高于沒有傳播行為的大眾群體。大眾對COVID-19是否對自己和家人造成了影響的反饋、大眾對待感染者或武漢回來患者的態度變量對應激反應總得分與各維度得分均有影響(P<0.05),認為新冠疫情對自己和家人影響嚴重者,應激反應總得分和各維度得分最高;對于從武漢回來的親朋好友的態度,其中選擇“勸他在家自我隔離,不與他接觸”的應激反應總得分、心理反應、軀體反應得分最高,而“主動舉報并登記”者的行為反應得分最高。見表5。

表4 研究人群應激反應得分與普通健康群體(常模)比較

表5 大眾認知對應激反應各維度得分的影響

表5 (續)
3 討論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無論是患者還是醫護人員,或者普通大眾,都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機與應激反應[6]。公眾群體應激反應研究較少,更多關注患者和一線醫護人員,而較少關注普通大眾。王芬等[7]調查發現,新冠疫情下抗疫一線醫護人員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恐懼、無助、疲勞、工作壓力及應急能力下降的心理應激反應;蔡芳芳等[8]研究發現,醫護人員參加救援后1周內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應激反應。葛傳惠等[9]研究發現,新冠疫情下心理健康自評檢出率最高的分別為疲勞、不快樂、很難做決定,女性的負性情緒較明顯,疫情知曉率低于本研究的調查結果。
本研究中人群應激反應總得分與無特殊應急事件時期普通健康人群的應激反應得分無差異,但心理(FER)、軀體(FPR)、行為(FBR)反應維度得分均有統計學差異。新型冠狀病毒暴發時期大眾群體的心理應激反應得分高于常模,而軀體和行為方面反而低于常模,這與一級預警措施下杜絕外出和居家隔離的相關措施有關,特別是在暴發時期,身體和行為反應相對滯后有關,可在后期繼續關注其身體和行為反應情況。在平臺上表達過對于新冠疫情的擔心與恐慌的大眾的應激反應得分高于沒有表達過的人群,在平臺上傳播過新冠疫情的防治知識大眾群體的應激反應總得分和軀體反應得分高于沒有傳播行為的大眾群體。這可以解釋為有較明顯應激反應的群體更多關注網絡平臺傳播和評論;反過來,更多關注網絡平臺傳播與評論的大眾群體,反應在應激反應得分上就越高,兩者一致。從大眾對COVID-19是否對自己和家人造成了影響的反饋來看,認為新冠疫情對自己和家人影響嚴重者,應激反應總得分和各維度得分最高;對于從武漢回來的親朋好友的態度,其中選擇“勸他在家自我隔離,不與他接觸”的應激反應總得分、心理反應、軀體反應得分最高,而“主動舉報并登記”者的行為反應得分最高,這種預警意識與其產生的應激反應是一致的。
研究提示,在疫情中要關注大眾的焦慮、恐懼、無助等心理應激反應;要加大網絡、電視疫情宣傳力度,重點宣傳疫情“可防、可控、不可怕”,降低大眾對疫情心理壓力;同時強化社區、居委會在疫情防控宣傳中的作用,對重點人群進行合理的心理疏導。在疫情發展的中后期仍不能掉以輕心,要持續關注長期居家狀態下大眾的心理健康問題,這也是本研究今后重點關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