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拽回被推出去的“壞孩子”
谷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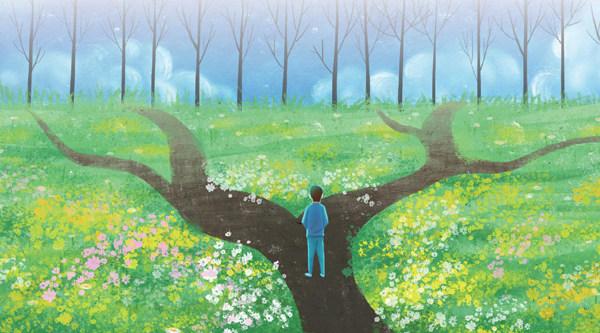
共青團北京市委聯合課題組做過一項調研,梳理不良行為青少年男女比例后發現,在233名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47名看守所青少年犯罪嫌疑人、169名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47名北京普通中學及技校的有不良行為青少年中,男性占比分別為89.3%、95.5%、95.9%和87.2%。壓倒性的占比,揭示出男孩子在與社會規范接軌時,發生錯位的潛在危險。就像一塊邊緣凌亂的拼圖,難以順暢地融入整個畫面。
不過,在試圖將其導向正軌的社工看來,他們依然是孩子——極度渴望認同,試圖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定義自我。人在環境中,社工們的努力,就是想幫助這群“迷途人”找準位置,完成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扭轉畸變的軌跡
“一個班里通常只有一兩個女生,更多的時候一推門,全部是男生。”回顧起有偏差行為的服務對象,葉露吟的講述并未停頓,但有了略顯沉重的一絲微瀾。
作為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以下簡稱“陽光中心”)的社工,葉露吟也承擔著聯校社工的職責。她的日常工作是和有各種行為問題甚至輕微違法犯罪的孩子打交道——在外人眼里,這是群典型的“壞孩子”,并且男生壓倒性地“雄踞”不算稀奇。
和葉露吟一樣,張瑾瑜同樣就職于陽光中心,擔任信息管理主任。根據中心服務對象的情況,就有偏差行為青少年的男女比例,他給出了7:3的大致數據。往往進入青春期后,這些男孩難以與身心發育產生的變化良好相處,外部環境又進一步激發了困惑和憤怒,在一段搖搖晃晃的時期里,反復偏離主流認可的路徑。
與他們初次建立關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打電話沒人接聽,或者被直接按掉;上門造訪,隔著門板冷冷傳來幾句回應,隨后被告知“我不需要”。碰壁的時候,社工會采取迂回方式,通過居委會等社區機構側面了解情況,從中找到敲開孩子家門的辦法。
家庭往往是孩子踏錯路的第一把“推力”。與其他留守兒童現象突出的地區相比,陽光中心督導周敏蔚提到,自己的服務對象多半并非家庭成員完全缺位,卻或多或少存在家庭教育的問題,“比如說家庭結構不完整,或者家庭支持不充分,抑或是家庭教育模式不良,都可能導致男孩行為問題的產生”。
特別是對困境兒童而言,監護困境的童年以及家庭固有罪錯行為的代際傳遞,導致了張瑾瑜形容的“如吹氣球一般的劣勢累積趨勢”。重大生命事件一旦發生,就可能變成“扎破氣球”的那根針,引起生命狀態從正常向非正常畸變。而他們也成為陽光中心重點關注的群體。
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是中心成立肇始的目標。根據張瑾瑜介紹,2003年,陽光中心正式落成,彼時的服務對象是上海市違法犯罪高發群體之一的未進一步就業青少年。歷經十幾年的持續服務,該群體從8萬人減少至2.5萬人左右,中心的服務對象也演變為包含未進一步就業青少年、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涉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困境兒童、有不良行為或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等六類群體。13個行政區,近400名社工,如同毛細血管延伸到城市的末端,所面對的幾乎都是傳統教育的“棄兒”——學校里沒有他們感興趣的知識,家庭又無法給予適當的支持,缺失吸引力。
扭轉畸變的軌跡,除了引導個體,周敏蔚也選擇家庭入手。雖然某種程度上,家長比孩子更難以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或者推著走兩步就退一步,但家庭的動力不可或缺。周敏蔚的技巧是,不能以要求的口吻對待家長,而應平等溝通,使其漸漸改變忽略教養或者簡單粗暴的管教方式,從家庭層面不斷支持和理解孩子。
進行犯罪預防工作的頂層設計時,張瑾瑜和團隊會使用社會聯結理論:在家庭自帶基因的影響外,如果兒童從小立定一個遠大志向或者職業目標,那么在產生偏差行為前,就會更多考慮犯罪成本的問題,從而獲得終止行為的內部動力。因此針對一些處于偏差行為邊緣的未成年人,社工會著意為他們提供人生規劃的服務。比如2020年疫情期間涌現的諸多英雄人物,就成為榜樣引領的鮮活案例。更重要的是,游蕩在城市街頭巷尾的青少年被組織起來參與社區志愿服務,親身體味付出的辛苦和受到他人認可的喜悅。屏蔽掉缺點后,沒有目的性的孩子開始試圖找到人生的方向。
實現自我的正確方式
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孩開始走出家庭,參加社團、組織的機會越來越多,極易受到他人行為的影響。世界各國關于青少年越軌行為的研究中,朋輩都被視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交往的朋輩是健康的,男孩會自然而然朝向積極的方向發展,反之,不良的交往情況可能導致相互“感染”。
張瑾瑜曾對中心服務的21個典型案例進行研究,結論是15個曾結交不良朋輩,其中9個更以此作為一系列行為畸變升級的開端:或是行為頻率的增加,如每周逃一次課演變成一周數次;或是類型的變化,如出入網吧演變成學會抽煙、喝酒,頻繁出入不良場所;更大的可能性是行為程度上的變本加厲,從自害型的不良行為升級為他害型的嚴重不良行為,甚至觸法或犯罪。
了解服務青少年的朋輩交往情況,是陽光中心基層社工的任務之一。一些孩子法制意識淡薄,難以辨別朋輩行為的性質,小宏(化名)便是其中之一。葉露吟和他接觸時,他正在虹口區的一所職校讀汽修專業。童年留守、初中父母離婚、母親再婚并繼續常年在外打工,和朋輩的交往占據了小宏課余生活的絕大部分時間。直到一次出入酒吧時被陌生人無意踩了一腳,在同伴的慫恿下,小宏帶人去找對方索要賠償,不可控地演變為聚眾毆打。在介入的過程中,小宏對自己觸犯法律一無所知,也暴露出對朋友的偏誤認知。
怎樣界定朋友、什么樣的朋友值得交往,類似話題在尚未成熟的頭腦中顯得輪廓模糊。當和服務對象建立起充沛的專業關系,周敏蔚會鼓勵孩子們說出愿意和朋輩交往的理由,以及分析朋輩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有的孩子因為感受到交往的快樂,有的因為朋友能把自己“帶進圈”,還有的為了所謂的面子,“作為社工,我們一般不會直接告訴孩子結果,而是希望他們自己能夠擁有分辨朋友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