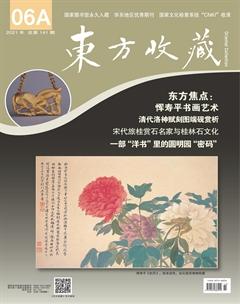明清時期中國繪畫的“西風”接受與“東風”傳播
摘要:中國古代繪畫的傳承與革新,一方面來源于對自身傳統的實踐與總結,另一方面則來自外來文化藝術的影響。在明清時期,東西方文明開始產生交流,外來藝術的沖擊致使中國傳統繪畫呈現出“中西融合”的畫風,風靡一時。但交流是相互的,中國傳統繪畫在接受外來技法的同時,也將其特色傳遞給了世界,影響著世界藝術。本文旨在從接受與傳播的角度,通過時代特點、傳播方式、形成影響去分析在明清時期,西洋繪畫如何影響中國傳統繪畫以及中國傳統繪畫對世界美術的影響。
關鍵詞:明清繪畫;西風東漸;中西美術交流;藝術傳播
中國的古代繪畫經歷著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多種多樣且具備時代特點的。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大夫中間人物品藻大為盛行,成為一種社會風氣。這時人物品藻已不再像東漢那樣著重人物的經學造詣和道德品行,而是著重于人物的風姿、風采、風韻”,于是在人物畫的創作中便出現了“傳神寫照”的審美追求;到了隋唐五代時期,畫科分類逐漸清晰與豐富,人物故事畫取材不僅涉及宗教且較前朝更加貼近生活,山水畫方面也出現了青綠或水墨的表現形式;宋朝時期,花鳥畫筆墨技巧的日趨完善、意境營造的匠心獨運以及畫家對自然萬物的體會觀察,使得宋人花鳥的創作在中國花鳥畫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章;到了元朝時期,以趙孟頫及“元四家”為代表,他們在宋人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筆墨趣味,將文人畫的發展推向了高潮;而在明清時期,畫派紛繁,風格各異,除了自身傳統的繼承與流變,由于東西方交流的大環境變革,“伴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方注重科學數理的各種繪畫作品和技法也陸陸續續地傳到中國,以其精確的寫實性,對于傳統繪畫側重于意境、筆墨的觀念形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影響著中國傳統繪畫的創作與審美趣味。
一、明清時期“西畫東漸”對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
1.明清時期“西畫東漸”的時代條件
明初,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開始出現契機。明成祖朱棣時期,三保太監鄭和奉命出使西洋。史有記載“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多齎金幣。”從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共計出海七次。“對當時及此后的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包括國內外商品的供應、生產和加工等,例如陶瓷和錢幣的生產,生活用品及高檔奢侈品的需求等物質層面,也包括文學、藝術、歌舞、戲曲等精神文化層面”。而放眼當時世界整體的交流環境,此舉不僅擴大了中國海外貿易及文化交往,連接了東西方文明,還為之后的文明交融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縱觀明清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期間朝廷雖然實施過“海禁”,但總的來說似乎從未完全停止過交易,從明朝中后期的“隆慶開關”再到清朝前期“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可見明清時期的中國并沒有固執己見,絕對地“閉關鎖國”,將外來的種種拒之于門外。甚至在15世紀至16世紀之交,“伴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西方殖民地化進程的推進,受到《馬克·波羅游記》一書的影響,一批西方人嘗試以全新的方式叩開古老中國的大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等在明代中后期相繼來到東方,并以社會團體或國家的名義,嘗試與中國交往,匯聚成一股中西交流的浪潮”,正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與西方的文明開始產生交匯,從而推動了西洋繪畫在明清時期的傳播。
2.西洋繪畫在明清時期的傳播方式
明清時期,除了海外貿易,西洋繪畫進入中國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傳教士。這些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后,不僅帶來了當時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并且在文化藝術方面,開闊了時人的視野,其中就包括美術作品、圖像資料以及西洋繪畫的理論與技巧。根據相關記載,最早在中國傳播西洋繪畫的傳教士為明末來華的意大利人利瑪竇,“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教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此后,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這段時間里,他所帶來的歐洲油畫、銅版畫展示出了不同于中國傳統繪畫的明暗對比以及透視效果,在宮廷內外都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由于美術作品在視覺功能上所具有的獨特優越性,除了利瑪竇以外,幾乎所有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都不曾忽視充分利用這種工具來發揮它的媒介效用”,宣傳宗教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洋繪畫傳入中國的進程。與利瑪竇相近時期在中國的傳教士還有龍華民、湯若望等人,均對西畫在中國的傳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清朝入關后,原先為明朝服務的天主教傳教士紛紛轉投清朝”,甚至在往后的時期,清朝外來的傳教士當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具備繪制西洋繪畫的能力,在畫院參與宮廷繪畫的創作,影響著當時的繪畫風格與審美取向。這批傳教士包括南懷仁、馬國賢、朗世寧、王致誠等人,其中以供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郎世寧的影響最大。郎世寧是意大利米蘭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奧內,圣名若瑟,“1707年加入耶穌會,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受耶穌會葡萄牙傳道部派遣到北京,由此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他“擅長畫人物、肖像、走獸、花鳥,重視明暗、透視,用中國畫工具、按西畫方法作畫,形成精細逼真的藝術效果”。在清廷服務期間,郎世寧留下了一大批畫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流傳至今,如《聚瑞圖》《嵩獻英芝圖》《乾隆皇帝大閱圖》《百駿圖》《乾隆帝后妃嬪圖卷》等。在這些作品中,他結合了中西方繪畫不同的畫法,展現出了一種折衷主義的畫風。進行創作的同時,他還培養了一大批能夠靈活運用中西方繪畫技法的宮廷畫家。從清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中可以找到西方傳教士畫家向中國畫家傳授西畫技法的記載。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郎世寧奉命帶徒弟學畫,“將畫油畫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達里等四人,留在養心殿當差;班達里沙、八十、孫威風、王介、葛曙、永泰等六人,仍歸郎世寧處學畫;查什巴、傅弘、王文志等三人革退”。由此可見,相較此前利瑪竇、艾儒略等明朝的來華傳教士,郎世寧等人則在傳播西洋繪畫圖像資料的基礎上,直接將西洋繪畫的技法帶到了中國,并結合中西方不同的繪畫技法,產生出了一些實驗性的繪畫風格,從而促進了東西方藝術上的交流。
3.西洋繪畫影響下的明清中國傳統畫科
西洋繪畫及其理論技巧在明清時期的傳入,對我國傳統繪畫的風格塑造與表現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并逐漸滲透到了各個畫科。人物畫方面,明末的曾鯨開風氣之先。其晚年之時,在中國傳統的肖像畫技法中吸收了17世紀傳入中國的西洋寫實技術。曾鯨融中西繪畫于一身,折中運用而作肖像。其法妙得神情,別開生面,遂形成了畫風獨到的“波臣派”。在他所繪制的《葛一龍像》《王時敏像》《張卿子像》等作品中人物面部“寫真效果”的呈現不難看出,除了對傳統技法的繼承之外,“不用粉彩渲染,而用淡墨烘染出陰影凹凸,然后敷彩,雖烘染不重,但有體積感”又體現出了對西法的采用。學者陳師曾就認為“傳神一派,至波臣乃出新機杼,其法濃墨重骨而后傅彩,加以暈染,其受西畫之影響可知”。到了清朝,在西方傳教士畫師的指導下,宮廷畫師丁觀鵬、姚文瀚等人的作品中同樣可以看出西方技法在人物畫當中的運用。在山水畫方面,來自西洋繪畫的空間維度與焦點透視效果之表現技巧亦出現在明清畫家的創作之中。明代張宏的園林山水畫《止園圖》便使用了西方寫實主義的技法,采用鳥瞰圖的視角描繪了明代蘇州止園的場景。并且,他在實景作品中“增加了對景物細節的描寫,從高處俯視遠景時也較能首尾一致地把握高點透視原則,畫面具有一種全新的空間遼闊感和空曠感,并有許多明暗和光影的暗示,這些特點都表明他可能曾受到某些歐洲繪畫的啟示”,以此使觀者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在他的另一幅山水作品《夜登華竹山》中,蘇立文先生認為其中的表現手法透露出了西方特色,“畫上有一條順著斜坡盤山而上通暢的長路,山頂山站立著三個人,這種畫法明顯來自納達爾神父所作《福音書故事畫》”。除此之外,還有清代冷枚的《避暑山莊圖》,畫中空間深度的效果“來自于畫家對山莊各處景物依其遠近而作比例縮小的精致安排,以及全景由前往后,由寬變窄,變成一正三角形幾何形狀的特別構圖安置。他顯然是采用了來自西方的透視法技巧來處理畫中山莊的位置問題”。以上多幅明清時期的山水畫作品均體現出了對西方繪畫技巧的借鑒。此外,明清時期花鳥畫的部分創作在色彩組合上的創新性同樣與西洋繪畫的影響不無關系。可見外來技法之傳入致使各傳統畫科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了多種藝術風格交融的新局面。
二、明清時期中國繪畫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傳與陶染
明清時期,中國繪畫除了受到來自西洋繪畫的影響從而產生新的表現形式之外,由于東西方海外貿易的展開以及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中國繪畫逐漸通過以上的方式傳播到了荷蘭、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并且引發了“中國美術熱潮”。例如在法國,“路易十四的宮廷從17世紀60年代起對東亞藝術的興趣迅速膨脹。這些人大半是宮廷內身份很高的貴族。有人描述他們收藏東亞美術品的屋子說:‘這些房間充滿了珍奇裝飾……其中有不少優美的中國瓷器,也有瓷人和中國繪畫”。不僅法國宮廷的貴族們對來自東方的藝術品有著濃厚的興趣,藝術家們同樣如此,畫家布歇“在他的畫室里藏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繪畫、陶瓷、家具以及佛像、武器之類的古玩”,甚至還將他從中國藝術品中獲知的東方元素運用到自己的繪畫創作如《躺在沙發上的女人》《早晨的喝咖啡時間》當中。與此同時,西方傳教士作為明清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環,他們一邊將西方的繪畫與理論技法帶入中國,另一邊又將中國的繪畫西傳至歐洲,促進了世界文化藝術的碰撞與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世紀中期開始出現的廣州外銷畫。“18世紀,清代外貿持續增長,出口商品除絲綢、陶瓷、漆木家具等外,還有繪畫作品。有充分的記載和實物證明,18世紀,在廣州,出口商品作坊已經相當活躍,其產品遠銷歐洲和美國”,雖然在題材與材料媒介等方面,東西方藝術風格糅合的廣州外銷畫并不屬于常規意義上的中國傳統繪畫,甚至在繪制的過程中還有一些西洋畫家的參與;但它卻通過此種形式,將畫中的“中國風情”傳遞到了西方,向歐洲展示著神秘東方古國的魅力。然而,明清時期中國繪畫更具滲透性的影響力卻是在隔岸的日本所體現出來的。明朝時期“堪合貿易”的條例實施使得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互動更加頻繁,藝術間的交流亦包括在內。室町時代的著名畫僧雪舟等楊便是在這一時期來到了中國,在中國學習交流的期間,雪舟等楊結識了不少畫家、閱覽了不少名家墨跡,從中受到了浙派繪畫風格的影響。回到日本后的雪舟又將其在中國習得的技法風格融合到自己的繪畫創作中,引領了室町時代水墨畫的發展。不僅如此,日本江戶時代興起的“浮世繪”同樣與中國繪畫有著淵源。浮世繪“作為描寫民間日常生活的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尤其在印刷術方面的發展,乃是日本藝術生活的一個新面貌,并且為其特色有三個世紀之久”,甚至影響了西方現代藝術的發展。然而究其風格來源,浮世繪“是學習中國畫的一種畫風,這種畫法來自中國最發達的盛唐文化以及明代的陳洪綬。陳洪綬的畫當時受到了日本上層社會的追捧和喜愛,爭相模仿。日本人也承認浮世繪這一來源”。可見,明清時期中國繪畫在接受來自西方繪畫之影響的同時,亦通過多種渠道將中國的繪畫風格傳播至海外,影響著世界美術。
基于上文的分析,在中國的明清時期,由于世界交流環境的變化,中國傳統繪畫受到了通過海外貿易、西方傳教士來華等方式傳入的西洋繪畫的影響,在其中吸收了關于明暗對比、空間透視的寫實性表現技法,從而產生了中西技法融合的畫風且涵蓋了人物、山水、花鳥等各個畫科,可謂豐富了中國傳統繪畫的表現形式。此外,通過以上的交流方式,中國的美術品得以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傳播并在一段時期內引發了歐洲國家對于中國美術品的收藏熱潮,中國傳統繪畫作為之中較為直觀的視覺表現媒介,向歐洲各國展示著古老東方大國的藝術特色,甚至將東方元素的繪畫符號引入了一些西方繪畫的創作之中。不僅如此,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繪畫的傳播與交流還影響了與我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對室町時代的水墨畫創作以及江戶時代的浮世繪風格起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繪畫對西洋繪畫技法的接納以及它在世界范圍的傳播與影響,共同為世界美術的多樣性提供了可能。
(作者簡介:孫啟,上海戲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繪畫史、中日美術交流)
參考文獻
1.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徐建融《中國繪畫》[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3.許嘉璐《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九冊》[M],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4.彭勇《明史》[M],人民出版社,2019。
5.倪玉平《清史》[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6.王鏞《中外美術交流史》[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7.楊仁愷《中國書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潘耀昌《中國近現代美術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9.鄧鋒《中國人物畫通鑒8:秋風紈扇》[M],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
10.高居翰、黃曉、劉珊珊《中國古代園林繪畫:不朽的林泉》[M],三聯書店,2012。
11.M·蘇立文《東西方美術的交流》[M],陳瑞林譯,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
12.石守謙《山鳴谷應》[M],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
13.秋山光和《日本繪畫史》[M],常任俠、袁音譯,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14.陳傳席《中國藝術如何影響世界》[N],《湖北日報》,2020-12-31。
15.華彬《中國宮廷繪畫史》[M],遼寧美術出版社,2015。
16.范勝利《中國人物畫通鑒9:硯田百畝》[M],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