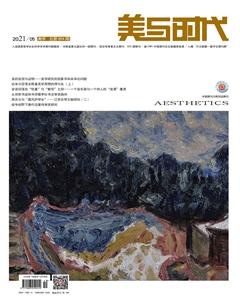“氣韻生動”在工筆花鳥畫創作中的表達研究
摘? 要:作為謝赫“六法論”的核心要素,“氣韻生動”自魏晉以來成為中國繪畫創作、批評和鑒賞所遵循的主要原則,亦是歷代書畫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歷代對于“氣韻生動”的論述主要在人物、山水和寫意花鳥畫中,當代工筆花鳥畫在經歷衰頹之后重振旗鼓,畫家們孜孜不倦地探索工筆花鳥畫的新形式與新內涵。探討工筆花鳥畫創作中的氣韻表達,從古意、詩意和筆墨三個層次分析“氣韻生動”在工筆花鳥畫創作中的表現,揭示傳統文化藝術之于當代工筆花鳥畫創作的重要性。
關鍵詞:氣韻生動;工筆花鳥畫;創作;表達
一、“氣韻生動”的概念界定
早在魏晉時期氣韻就被用于形容人的性情氣質和談吐風度,進而成為人物畫中的品評標準,與顧愷之“傳神”相對應,后逐漸擴展到對山水、花鳥畫的品評。關于氣韻,古今畫家和學者各有說法而萬變不離其宗。五代荊浩認為“氣”存在于“心隨筆運”而取象的過程,“韻”是隱跡以立形,為去俗而周備眾儀的結果[1];北宋郭若虛認為氣韻“必在生知”,氣韻足而生動至;明代董其昌認為氣韻為天賦,亦可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后天努力中獲得;近現代宗白華先生認為氣韻是宇宙中促進萬物和諧生長的“氣”的存在;徐復觀認為氣韻是繪畫中兩種極致的美;陳傳席認為氣韻指人由內而外的、只可意會的精神氣質;鄧以蟄認為“氣”是萬物和我合而為一的“氣”,“韻”是萬物變化過程中隱秘細微的節奏變化,“氣韻”在繪畫中最終通過筆墨表現出來[2];胡家祥認為氣韻是借作品符號而呈現的物象的精神——氣勢和韻致[3]。“氣韻生動”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體系,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豐富的哲學、美學內涵。筆者認為,就工筆花鳥畫而言,“氣韻”包涵客觀氣韻與主觀氣韻兩個層次:客觀氣韻指畫中物象基于外在形似的精神氣質與性格特征,使觀者觀畫如觀實物、實景,甚至能感受到甚于實物實景的更純粹的生機與活力;主觀氣韻指作者借助描繪對象和成熟精煉的技法表現出來的素養、情感與個性。在主觀氣韻的作用下畫面是有節奏而富含意蘊的,能觸動欣賞者的內心而使之產生精神上的共鳴。“生動”是“氣韻”之于觀賞角度而言的形象表達,指畫面內容有生命、有活力、能感動人,為“氣韻之光輝,之色澤”[4]“茍無氣韻,即無生命”[5],氣韻成則生動出。
二、工筆花鳥畫中的氣韻表達
(一)尋氣韻于“古意”
在一定程度上“古意”可理解為基于“復古”的“師古而化”。中國繪畫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文化之中,十分重視傳承,承前才能啟后,使中國繪畫在一脈相承的軌道上更上一層樓。歷史上不乏推崇“古意”的例子,元代趙子昂主張繼承唐代和北宋的作畫技法和畫面意趣、意蘊以追求“古意”中樸素、古拙與典雅之氣韻;明代邊景昭、呂廷振等人以唐宋花鳥畫的風格作為畫面基調作畫,雖沒有明確的復古理論,但作品中多體現出對前代繪畫藝術的敬意;清初“四王”在山水畫領域主張復古并付諸行動;清末康有為主張“以復古為更新”,在繪畫上提倡追溯宋代院畫傳統以求創新,把復古作為一種借古開今的策略;于非在20世紀初工筆花鳥畫處于衰頹的低谷之時大力復興工筆花鳥畫,提倡與古為徒,追摹宋院體并重拾寫生傳統。各個時期的“復古”現象都是在當時畫壇出現種種弊端的背景下發生的。事實證明,歷史上提倡“復古”的現象都超越了“古”,實現了創新,而脫離正統的盲目創新往往走向極端。
正如鄧以蟄所說,古意“無非為氣韻而發”,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意蘊上的“復古”,都是以追求古人畫面氣韻為目標的。尋氣韻于“古意”,不能“徒學古人之所作”,關鍵是要以古人之心境觀其所觀,思其所思,如此方能取古人之精髓。因此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對追求“氣韻生動”尤為重要,傳統是在優勝劣汰的規律下,靠歷朝歷代文人與藝術家的智慧積累而來的。現代工筆花鳥畫是基于對中國千年傳統文化藝術的繼承發展起來的,同時它也是未來繪畫藝術的傳統[6]。加強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習以使學識底蘊得到強化,才能在繪畫創作中向著更高水平發展,推動中國繪畫藝術向前邁進。“古意”思想要求現代工筆花鳥畫家“移步不換形”,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理念與藝術精神,在師古中循序漸進,以求氣韻生動,同時師古與師法自然并駕齊驅,立足于經典而超越經典。
(二)求氣韻于“詩意”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作為語言之藝術的“詩”和作為視覺之藝術的“畫”本屬于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意境”是兩者在精神本質上的切合點,使二者有相似的意趣。北宋蘇軾曾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①不論那首詩是不是好事者所補,都可以看出詩與畫意境的相似與相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可以從畫面上表現出來,然而“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是很難將詩中的意味通過畫表達出來的,這是詩的魅力所在。不能啟發人產生詩意的畫作就只能作為一張紀實的照片或寫實的圖片而不是畫[7]。正如晁以道所言:“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畫外之意由詩來表達,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圓滿而使氣韻的表達更濃郁,同時畫能使詩中的景與物具體形象化而使詩的韻味得以成就,詩畫交輝,取長補短,耐人尋味。傳統中國畫常常講求“詩書畫印”合而為一以求氣韻亦是如此之道理。
在工筆花鳥畫中,意境是繪畫中的精神氛圍,或空靈、或清逸、或蕭疏、或蒼茫、或雄渾、或絢麗,意境的營造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寓情于境”。“詩情畫意”在本質上源自畫家的藝術氣質和各方面之修養,包括哲學、書法、文學、音樂藝術和閱歷等對他們精神的豐富,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8]。這份感悟源自畫家對生命的體驗,并通過畫面意境延展到畫之外,直達觀者內心,極具藝術感染力。
(三)歸氣韻于筆墨
唐岱在《繪事發微》中說:“氣韻與格法相合,格法熟則氣韻全。”氣韻貫穿繪畫的整個構思與表現過程,最終落實到筆墨上,由筆而生。筆墨是氣韻的實體擔當,是中國畫最基本的技法要求,亦是評判一幅作品水平的基本要素,其中墨之氣韻比較容易掌握,筆端之氣韻卻是世間少見。筆墨與謝赫“六法”中的“骨法用筆”與“隨類賦彩”相對應,在工筆花鳥畫中指用筆用線和用墨賦色這兩種技術層面的表現形式,尤以“骨法用筆”最為重要。
其一為用筆,畫家在用筆上的功力與氣韻息息相關,唐岱說:“氣韻由筆而生,或取圓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用筆不癡不弱,是得筆之氣也。”歷代古人通過掌握用筆的提、按、頓、挫、輕、重、緩、急等執筆與運筆方式變化創造出“傳統十八描”之線條樣式,這是以“骨法用筆”為精神內核衍生出來的產物。“骨法用筆”關乎作者情感、素質、審美體驗與筆力的融合,通過力道的運用作于紙上,勾畫出有質量的線條,這需要千萬次的練習。工筆花鳥畫中的線條不是用以勾勒物體輪廓的純粹線條,它是繪畫對象內部骨架自里顯于外的結構線,使對象具備最基本的“形似”,又是整個畫面的骨架子,以中氣十足的用筆支撐起整個畫面而使之具有一種特殊的“骨”力美[9]。其二為賦色,工筆花鳥畫中的“隨類賦彩”是一種由外在的客觀因素與內在的主觀思想相結合的賦色方式,即根據對象的特點、畫面的需要和作者要表達的情感找到最合適的顏色,以充分表達主題。工筆花鳥畫的色調風格從顏色的冷暖、強弱、明暗上分為多種,或淡雅、或樸素、或艷麗、或明朗、或沉穩。色調是畫家傳達內心情感的媒介,能從視覺上迅速觸動觀者的內心而激發其情感體驗,使畫家與欣賞者產生情感的溝通與交流。
在中國傳統藝術美學觀念中,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分為“應目”“會心”“感神”和“神超理得”四個階段②,“歸氣韻于筆墨”則是在充分認識客觀事物,達到“神超理得”境界之后的具體表現過程。這個過程實質上始于立意構思,關乎經營位置、用筆、象形、賦彩等問題,各要素遵循畫面整體和諧的原則,層層遞進,相互協調,以造感人之意境,生動人之氣韻。
三、結語
“骨法用筆,非氣韻不靈;應物象形,非氣韻不宣;隨類賦彩;非氣韻不妙;經營位置,非氣韻不真;傳移模寫,非氣韻不化。”③作為謝赫“六法”的核心要素,“氣韻生動”是貫穿所有表現技法和形式的生命線,它以遵循萬物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實質為基礎,十分重視筆墨上的趣味,對畫家情感個性與人品素質亦有很高的要求,在不同時代特征和思想意識下的表達形式各有不同。“氣韻”源自畫家內在氣質、素養、審美和學識,以“生動”的藝術形式展現出來,它是每個畫家獨特性的表現,亦是不同時代社會精神和審美觀念的表現。在現代工筆花鳥畫創作中,“氣韻生動”這個萬古不變的準則要求畫家向內求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形式為基石,發掘更豐富的形式與精神內涵。
注釋:
①此詩為蘇軾在評論王維的《藍田煙雨圖》時所作。
②南朝宗炳《畫山水序》:“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
③出自明代汪珂玉《跋畫》。
參考文獻:
[1]俞建華.中國古代畫論精讀[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262.
[2]鄧以蟄.鄧以蟄全集[M].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8:258.
[3]胡家祥.“氣韻”探幽[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17-23.
[4]鄧以蟄.鄧以蟄全集[M].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98:257.
[5]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210.
[6]姜今.中國花鳥畫發展史[M].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1:168.
[7]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
[8]何東,王智慧.中國畫評審標準談[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226.
[9]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24-125.
作者簡介:莫嫻,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