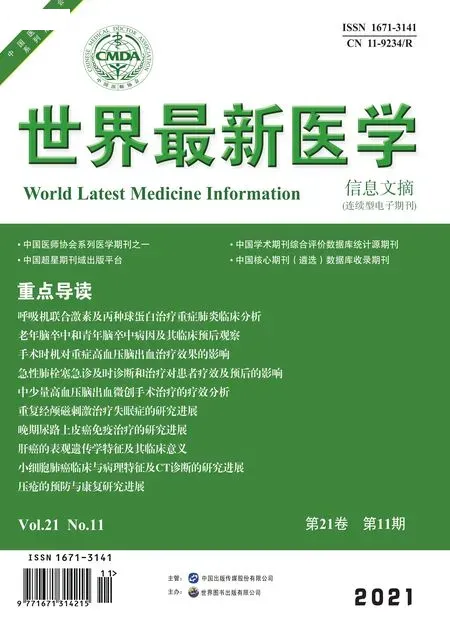急性雙側小腦梗死32例臨床特點分析
王利惠,毛倫林,陳文亞,馬愛金
(江蘇大學附屬武進醫院/徐州醫科大學武進臨床學院 神經內科,江蘇 常州 213003)
0 引言
小腦梗死常表現為頭暈嘔吐及行走不穩,查體可有眼球震顫、共濟失調,若合并腦干或幕上腦梗死,可表現為頭痛、意識障礙、球麻痹及肢體癱瘓等,部分臨床癥狀不典型。既往研究發現,小腦梗死發病率不高,約占所有腦卒中的20%[1-2],而雙側小腦梗死占比更低,約占后循環腦梗死的17.4%[3]。但是雙側小腦梗死伴腦干或幕上梗死的患者癥狀相對較重,預后較差[4]。根據頭顱MRI的DWI序列上腦梗死病灶部位將雙側小腦梗死分為兩個亞組:單純雙側小腦梗死(Pure bilateral cerebellar infarction,pBCI)組和雙側小腦梗死伴腦干或幕上梗死(Bilateral cerebellar infarction plus supratentorial stroke,sBCI)組,對比兩組一般臨床資料、影像學資料和臨床預后差異,可以為臨床上診治小腦梗死提供指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連續收集我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住院的經MRI彌散加權成像(DWI)證實急性小腦梗死患者168例,其中雙側小腦梗死的患者32例。記錄所有患者一般資料及心房顫動、腦卒中史、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相關病史。入院72 h內完成頭顱MRI檢查,病情允許的在1周內完成頸顱增強MRA檢查。
1.2 方法。頭顱MRI的DWI序列上,小腦梗死灶的血管供血區按照文獻[4]判讀如下:小腦后下動脈(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PICA)通常起源于椎動脈遠端,供應小腦后表面;小腦前下動脈(an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AICA)起源于基底動脈,供應單葉、上葉和下半月小葉的前面以及絨球和小腦中腳;小腦上動脈(superior cerebellar artery,SCA)起源于基底動脈的末端附近,通常供應小腦的上表面和前葉。另外,椎基底動脈系統血管狹窄情況根據頸顱增強MRA報告判讀。所有影像學判讀由2名神經科主治以上職稱醫師參考放射科報告共同完成。
1.3 觀察指標。觀察兩組眩暈、嘔吐、眼球震顫、指鼻試驗、跟膝脛試驗、閉目難立征等臨床表現差異[5]。對比兩組年齡、生化指標和治療前e-NIHSS[6]差異。分別記錄兩組梗死灶的血管供血區和MRA血管狹窄情況,用例數n(%)表示。對比兩組出院時mRS差異。
1.4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既往病史和癥狀體征比較。本研究168例急性小腦梗死患者中,雙側小腦梗死32例,占19%。雙側小腦梗死患者中,pBCI組12例和sBCI組20例,性別比例、糖尿病、腦卒中史、冠心病、心房顫動等既往史在兩組間無明顯差異(P>0.05),眩暈、嘔吐、指鼻試驗、跟膝脛試驗兩組間無明顯差異(P>0.05),pBCI組高血壓比例明顯高于sBCI組(P<0.05),pBCI組眼球震顫和閉目難立征陽性比例較sBCI組明顯升高(P<0.05),見表1。
2.2 2組生化指標和e-NIHSS的比較。入院時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在pBCI和sBCI組間無顯著差異,sBCI組平均年齡明顯高于pBCI組(P<0.01),入院時sBCI組CRP水平和e-NIHSS評分明顯高于pBCI組(P<0.05,P<0.01),見表2。而且pBCI組e-NIHSS評分均不大于6分,sBCI組有11例(55%)不大于6分,9例(45%)大于6分。
表2 pBCI組和sBCI組年齡、生化指標和治療前e-NIHSS比較()

表2 pBCI組和sBCI組年齡、生化指標和治療前e-NIHSS比較()
注:*與pBCI組比較P<0.05;#與pBCI組比較P<0.01。
項目 pBCI組 sBCI組 P平均年齡(歲) 58.2±13.76 73.5±8.90 0.00314#LDL-C(mmol/L) 3.24±0.72 2.98±1.05 0.406 Hcy(umol/L) 16.56±7.18 21.85±28.02 0.431 CRP(mg/L) 4.39±3.19 26.64±43.26 0.0334*Glu(mmol/L) 6.10±1.62 7.56±7.10 0.388治療前e-NIHSS 1.83±1.53 7.80±7.43 0.00222#
pBCI組中,梗死灶位于PICA供血區9例(75%),PICA和AICA供血區2例(16.7%),PICA和SCA供血區1例(8.3%)。sBCI組中,梗死灶符合基底動脈尖綜合征(TOBS)表現17例(85%),梗死灶位于基底動脈腦橋支、AICA、SCA和幕上大腦后動脈供血區,PICA和幕上2例(10%),PICA、SCA和幕上1例(5%)。
pBCI組中,頸顱增強MRA示未見椎基底動脈系統明顯血管狹窄3例(25%),單側椎動脈細小2例(16.7%),雙側椎動脈狹窄1例(8.3%),單側大腦后動脈狹窄3例(25%),其余3例未能完成MRA。sBCI組中,頸顱增強MRA示基底動脈和椎動脈狹窄4例(25%),雙側椎動脈和大腦后動脈狹窄3例(15%),單側椎動脈細小1例(5%),其余12例因病情危重、神志昏迷無法完成頸顱增強MRA。
出院時sBCI組mRS評分(2.85±1.90),明顯高于pBCI組的(0.25±0.45)(P<0.01)。sBCI組中出院時mRS 0~3分11例(55%),4-5分的9例(45%),而pBCI組出院時mRS均為0-1分。
3 討論
本研究中雙側小腦梗死32例,占所有小腦梗死患者的19%,略低于我國學者報道的30%[7],可能與地理上南北方人口學差異有關。本研究的32例雙側小腦梗死患者中,sBCI組平均年齡明顯高于pBCI組,入院時sBCI組CRP水平和e-NIHSS評分明顯高于pBCI組,提示sBCI組基線病情顯著重于pBCI組,與文獻[8]報道相符。
既往的研究發現,雙側小腦梗死的發病機制最常見的是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和心源性栓塞[9],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的責任血管以椎動脈V4段和基底動脈為主[10],表現在頭顱MRI的DWI序列上梗死灶常見于PICA和SCA供血區[11]。然而,本研究pBCI組中,梗死灶位于PICA和SCA供血區僅1例(8.3%),sBCI組PICA、SCA和幕上1例(5%),低于王普清和張偉晴等報道的比例。
此外,sBCI組在MRI的DWI序列上除了雙側小腦梗死灶,往往還合并腦干梗死、丘腦梗死、枕葉梗死、顳葉內側梗死灶等,符合基底動脈尖綜合征(TOBS)表現[12]。TOBS的發病機制可能與心源性栓塞和動脈-動脈栓塞有關,脫落的栓子可造成責任血管的栓塞而致病[13]。由于有幕上(丘腦及顳枕葉)幕下(腦干及小腦)同時受損表現,且都有2處以上病灶,故TOBS臨床表現多樣化,易被漏診誤診,其中腦干梗死和丘腦梗死病灶常表現為意識障礙、球麻痹和肢體癱瘓等,本研究sBCI組e-NIHSS明顯高于pBCI組,其中有9例(45%)大于6分,而pBCI組e-NIHSS評分均不大于6分,故sBCI組臨床上病情危重,往往需要神經科監護室或ICU收住,預后較差,sBCI組中出院時mRS 4~5分的9例(45%),而pBCI組出院時mRS均為0~1分,與文獻[14]報道TOBS患者中mRS評分4-6分者占比最多相符,常常死亡或自動出院。sBCI組中部分TOBS患者病情進行性加重,無法完成頸顱增強MRA或CTA,建議在首次MRI時加做3D-TOF檢查,初步評估椎基底動脈狹窄閉塞情況[15]。
對比每例患者DWI序列梗死灶的血管支配區和頸顱增強MRA的狹窄血管,發現兩者不完全匹配,考慮原因如下:一方面,雙側顱內外動脈和wills環的側枝循環代償存在,實際梗死灶體積小于狹窄的責任血管供血區;另一方面,MRA的敏感性決定了僅能顯示椎基底動脈和大腦后動脈等大動脈,PICA、AICA、SCA和基底動脈腦橋支往往顯示不清,評估血管的金標準仍需依靠DSA檢查[16]。
綜上所述,雙側小腦梗死中sBCI組病情明顯重于pBCI組,pBCI組預后良好,臨床上更需要重視sBCI組患者,sBCI組除了雙側小腦梗死灶,還合并腦干梗死或幕上梗死灶,符合TOBS表現,由于TOBS患者預后大都不佳,故早診斷早治療尤其重要,“時間就是大腦”,如果能在3-4.5小時內到達醫院且評估完畢,則有機會使用阿替普酶靜脈溶栓;如果在24小時內完成評估,部分患者還有可能嘗試血管內支架取栓[17]。本研究的局限性:雙側小腦梗死發病率較低,本研究回顧性分析本單位單中心的雙側小腦梗死患者的臨床特點,若能采取多中心協作研究,將能更準確的總結雙側小腦梗死的臨床特點和預后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