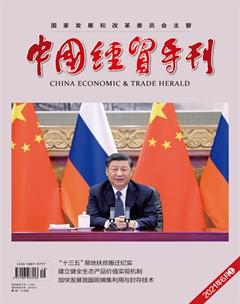優化國內產業協作關系是產業鏈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徐建偉
受全球競爭格局調整影響,我國產業鏈不穩不優不強的問題愈加突出,關鍵技術裝備及核心部件材料“卡脖子”狀況頻發,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更顯重要,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形勢嚴峻、甚為緊迫。要盡快扭轉產業鏈高度外聯、自我循環支撐能力不足的困境,需要深化國內不同產業和領域環節間的技術、產品與市場聯系,積極推進建鏈復鏈拓鏈進程,進一步優化本土產業協作關系,為提高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打好基礎、鍛好架構。
一、鏈條摩擦頻發暴露產業鏈存在安全隱患
(一)部分核心零部件及重要材料供應緊張
這與我國大量進口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有關。在電子信息領域,由于國際上產能供不應求,再加上國內芯片制造技術差距大、關鍵化學材料進口“卡脖子”,導致國內高端芯片供給緊張、缺口較大,企業光刻膠每批次采購量從超過100公斤降至10—20公斤,產品價格也大幅上漲。在汽車領域,我國汽車芯片進口比率超過90%,先進傳感器、車載網絡、“三電”系統、自動駕駛等關鍵系統芯片被國外壟斷。芯片供應緊張導致部分企業生產經營波動,被迫調整產量或產品價格。
(二)關鍵技術領域國際合作空間被壓縮
一些國家采取措施加嚴技術轉移管控,給我國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帶來一定沖擊。如,美國針對電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領域的“337調查”不斷增多。國際上限制技術出口的《瓦森納協定》也在不斷修訂更新,部分國家還謀劃建立科技合作聯盟,以圖通過聯合制定標準規則、協調技術管控等方式,阻撓我國在科技創新和高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
(三)傳統出口產品及市場遭遇經貿摩擦
我國部分產業及產品出口外向度較高,如紡織品、服裝等,受國際服裝品牌商、零售商影響大,面臨國外貿易及非貿易壁壘帶來的市場沖擊。如,耐克超過20%的鞋子和服裝在我國生產,優衣庫超過100家、約一半的代工廠分布在我國,國內一些企業為國際品牌代工的比例超過80%。這也暴露出我國傳統優勢產業在研發設計、品牌運營、零售分銷等環節存在嚴重短板,特別是品牌成長滯后于產業和市場發展。在2020年全球最有價值的50個服飾品牌中,美國、意大利、法國分別有17個、8個和7個,我國只有2個入選。
二、我國產業鏈穩定高效協作面臨多重挑戰
(一)外部關聯震蕩化
由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部分國內企業與國外零部件供應商、品牌運營商、終端零售商等合作緊密,內生自主的產業關聯被打破。從供給端來看,大量企業在技術裝備、核心零部件、關鍵材料等方面依賴進口,“卡脖子”問題突出。2020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額高達3500億美元,芯片進口受阻給產業發展造成制約。從需求端來看,一些企業習慣于“前店后廠”“外店內廠”的接單代工式生產,在產品開發、市場訂單、售后服務等方面處于被動地位。隨著全球經貿摩擦加劇,在零部件供應、技術合作、出口市場等方面的外部震蕩風險加大,給國內企業維護產業鏈供應鏈暢通、保障生產穩定運行帶來挑戰。
(二)國內協作割裂化
國際化的產業協作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本土產業協作,導致國內不同產業和環節間互不銜接、支撐斷裂,“有產業缺關聯”“有企業弱協作”的現象比較突出。一是產業鏈上下游合作割裂,國內企業對國外零部件和材料供應商高度依賴,本土零部件和材料企業想要替代國外供應商、嵌入本土產業鏈難度很大。二是產業間支撐協作被打破,企業在技術裝備、軟件系統、關聯服務等方面傾向于選擇高端優質的國外供給,自主創新產品推廣應用的市場機會稀缺。由于本土產業協作斷裂、“孤島”效應突出,導致本土企業在產品供需互動、技術合作開發、新品推廣應用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導致國內自主建鏈任務重、成本高、難度大。
(三)企業競爭同質化
鏈主型企業、基底型企業和生態主導型企業是構建產業鏈的關鍵中樞。由于跨國企業成為我國產業鏈的重要構建者和治理者,國內缺少能夠主導產業鏈構建的鏈主型企業,導致產業鏈話語權缺失。國內發展優勢長期鎖定在加工組裝環節,大量的企業技術水平相近、市場定位趨同、產品同質競爭嚴重。由于部分產業發展路徑“短平快”,在引進國外技術和進口零部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企業集中在顯示度高的下游組裝和終端領域,支撐產業發展的重大裝備、關鍵材料、共性技術等基礎積淀薄弱,基底型企業不穩不強的問題非常突出。近年來,國內一些平臺型企業快速成長,在構建產業新生態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資源整合、業態模式等方面還處在探索之中,存在互相模仿、重復建設的問題。
(四)自建鏈群封閉化
出于做大經濟總量、做強產業鏈條等考慮,一些地方和企業鏈群封閉化發展傾向增加。一是部分地區不顧自身發展條件,競相提出自建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全周期布局研發創新、加工制造、增值服務等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甚至打造從科技創新到轉移轉化再到推廣應用的全過程。如,各地重復布局高端芯片項目以及全鏈條布局電動汽車、氫能源、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的現象非常普遍。二是許多企業推進建設自我主導的產業生態圈,如,眾多家電龍頭企業紛紛提出全場景智能家居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共享或兼容的。鏈群封閉發展導致產業重復建設、資源過度競爭、市場碎片化等問題,最終不利于鏈群協作體系和良好競爭生態的構建。
(五)內生建鏈弱勢化
在國際分工合作體系下,國外的研發設計、技術裝備、部件材料、專業服務等產業資源在我國匯聚集合,疊加國內強大的勞動技能和產業配套能力,形成最具全球競爭優勢的加工制造能力。在應對外部震蕩風險、推進國內自主建鏈的進程中,由于自主創新產品的性能提升和產品迭代需要一個過程,采用備鏈方案或國內替代產品,短期內可能會造成一定的產品效率損失和質量下降。對部分領域來說,短期的競爭力下降是鏈條重建的必然過程,也是邁向更高水平國際競爭的涅槃之路。但在我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同時,可能面臨著新的全球制造基地崛起,由此帶來的產業沖擊和市場替代不容忽視。
三、進一步優化鏈條協作關系的關鍵著力點
(一)推動產業深度融合發展
產業鏈現代化首要的是建立本土產業協作關系,扭轉過度依賴外部關聯、國內協作嚴重斷裂的發展格局。一是推動關聯產業深度融合發展。加強裝備與材料、機械與電子、整機與部件等產業在技術、產品和市場上的協作聯動,化體量規模優勢為關聯協作優勢,提高產業間的暢通循環能力和協調發展水平。二是推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加快補齊研發設計、信息咨詢、高端軟件、售后服務等短板,把產業鏈兩端做起來,形成制造衍生服務、服務支撐制造的良性循環。三是推動制造業與新技術深度融合發展。加快推廣應用5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智能技術、低碳技術,推動產業發展模式轉型與鏈條重塑。
(二)加快培育建鏈關鍵企業
產業鏈協作的核心是暢通企業協作,構建聯系緊密、層級有序、治理高效的現代企業群落。一是培育產業鏈鏈主企業。推動制造業龍頭企業增強創新優勢和發展能級,引領帶動本土企業貫通產業鏈供應鏈,把國內企業互相協作、融合發展的架構搭建起來。二是培育基底型支撐企業。更大力度支持共性技術平臺、基礎科學和前沿科學機構創新發展,引導基礎部件、基礎材料、基礎裝備、基礎軟件企業向專精特新發展,緩解“卡脖子”瓶頸約束。三是培育平臺型生態企業。發揮平臺的要素聚合、資源交換和優化配置作用,提高產業鏈上下游、前后側、內外圍的耦合發展水平。
(三)協作共建優勢產業鏈群
發揮各地比較優勢、共建高水平鏈群是推進產業鏈協作的重要導向。一是引導各省市、各地區協同共建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立足于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區域,加強產業鏈對接合作,在汽車裝備、電子信息、基礎材料、輕工紡織等領域建設一批標志性產業集群。二是深化東中西及東北地區的梯度協作。加快東部地區優勢產業向研發設計、品牌運營、系統集成、增值服務等高端領域延伸,鼓勵中西部地區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優勢、完善產業配套條件,厚植承接產業轉移的良好生態。三是加強新興產業領域的協同合作。聚焦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推進錯位協同發展,防止各地一哄而上、重復建設。
(四)構建自主產品推廣生態
供需順暢是產業鏈協作的動力條件,要發揮需求牽引作用推動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建設。一是更大力度推動自主創新產品推廣應用。建立符合國際規則的創新產品政府首購制度,加大對首臺套裝備、首批次新材料和首版次軟件等創新產品采購力度,為創新產品提供應用場景和升級迭代的市場空間。二是鼓勵“卡脖子”領域、斷鏈環節和符合升級方向的產品創新。依托各類企業云平臺,搭建自主知識產權產品采購對接平臺,支持企業互相認購采購,促進供需對接、產銷銜接。三是提高自主創新產品認證信用水平。加快完善質量基礎設施和檢驗認證制度,建立高認可度的試驗驗證評價體系。
(五)優化國際鏈條協作關系
多元彈性的國際協作鏈條是產業鏈穩定安全的巨大回旋空間。一是構建更加多元的全球產業鏈。加強與歐盟、日韓等國家在高端制造領域的合作,更大力度引進優質資本和先進技術,加強與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合作,推動國內優勢產業鏈外延拓展,加快構建更具話語權的生產協作網絡。二是拓展豐富全球創新鏈。整合利用俄羅斯、東歐、巴西、南非等國家在基礎科學和細分領域的創新資源,搭建國際創新合作平臺,提高協同創新和合作開發能力。三是逐步提升全球服務鏈。重點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周邊市場,推動制造企業和服務企業協同“走出去”,不斷拓展中國制造的增值空間和整體優勢,不斷提升中國服務的質量效率和水平能級。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