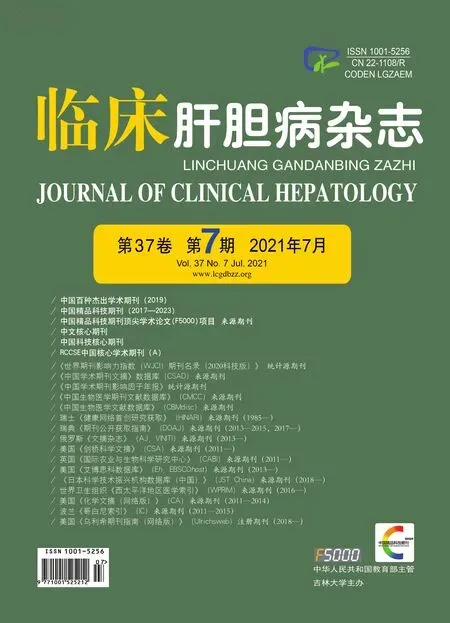Braun吻合對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胃排空延遲的影響
楊思捷,張 輝,王正峰,史志龍,周文策,
1 蘭州大學 第一臨床醫學院,蘭州 730000;2 蘭州大學第一醫院 普外科,蘭州 730000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目前是治療膽胰匯合部周圍惡性腫瘤及部分良性疾病的唯一根治性手術方式。但是其手術范圍廣,創傷較大,故術后并發癥多。其中,胃排空延遲(delayed gastric emptying,DGE)患者術后禁食時間延長,恢復慢,并且嚴重影響了患者術后的生活質量。近年有研究[1-2]表明,Braun 吻合(Braun anastomosis,BE)可降低PD術后DGE的發生率,但尚存在爭議[3-5]。Braun手術始于1892年,Braun對胃切除術后出現嚴重反流性胃食管炎的患者進行二次手術,在連接殘胃的空腸輸入段和輸出段之間進行了腸腸吻合,以降低術后膽汁性胃炎和膽汁性嘔吐的發生,并建議在胃腸吻合術后常規進行該吻合,或可以降低術后吻合口瘺及輸入袢梗阻的發生率[6]。理論上BE可以使膽汁和胰液等消化液通過BE口排出,減少對胃黏膜的刺激。亦可通過該吻合口排出部分胃內容物,減少潴留[7]。也有學者[1-2]認為可防止腸道扭轉并維持消化道穩定,并通過減少胃腸道壓力降低胰瘺發生率,進而減少DGE的發生。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進一步明確BE對預防PD術后DGE的影響。
1 資料及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6年12月—2019年12月在蘭州大學第一醫院行根治性PD的患者資料。根據術中是否行BE將患者分為BE組和非BE組。收集患者的性別、年齡、BMI、病理分型、基礎疾病、WBC、RBC、PLT、Hb、ALT、AST、TBil、Alb、手術時間、出血量、術后并發癥、止吐及通便藥物使用次數、第1次化療時間(術后)、住院時長及住院花費。
1.2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20~80歲。(2)臨床上確診膽胰匯合部周圍惡性腫瘤及部分良性疾病,并經多學科會診后,建議行PD的患者。(3)DGE診斷標準參考《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癥診治及預防的專家共識(2017)》[9],術后 3 d因仍需要氣管插管而留置胃管等其他非胃排空功能減弱的情況,同時上消化道造影證實未見胃蠕動波并伴有胃擴張時,出現以下情況之一者,可診斷為術后DGE:①術后需置胃管時間超過 3 d;②拔管后因嘔吐等原因再次置管;③術后 7 d仍不能進食固體食物。根據其嚴重程度分為A、B、C 3級。A級:鼻胃管(nasogastric tube,NGT)時間大于術后3 d,或術后7 d不能耐受固體飲食,可伴嘔吐,可能需要應用促胃腸動力藥物。B級:NGT時間術后8~14 d,或術后7 d后重插NGT或術后14 d仍不能耐受固體飲食;伴嘔吐,需要應用促胃腸動力藥物。C級:NGT時間大于術后14 d,或術后14 d后重插,或不能耐受固體飲食時間大于術后21 d,伴嘔吐,需要應用促胃腸動力藥物。(4)胰瘺、膽瘺、出血等并發癥診斷標準參考《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癥診治及預防的專家共識(2017)》[9]。
排除標準:(1)幽門及其他消化道梗阻吻合口狹窄、吻合口水腫等;(2)胃癌;(3)既往有消化道改建手術史;(4)保留幽門的PD;(5)伴有嚴重并發癥不能耐受手術者;(6)拒絕簽署知情同意書者;(7)資料不全者。
1.3 手術方法 兩組患者均行開腹PD,采用標準的術式,切除范圍包括胰頭(包括鉤突部)、肝總管以下膽管(包括膽囊)、遠端胃、十二指腸及部分空腸,同時清掃胰頭周圍、腸系膜血管根部,橫結腸系膜根部以及肝總動脈周圍和肝十二指腸韌帶內淋巴結。重建按照胰腺-空腸吻合、肝總管-空腸吻合和胃-空腸吻合順序進行[8]。BE組:于胃腸吻合口10 cm處,將連接殘胃空腸的輸入端與輸出端使用直線切割閉合器行空腸-空腸側側吻合,吻合口直徑2 cm。兩組患者術后均常規于膽腸吻合口、胰腸吻合口各放置1根腹腔引流管,胃腸減壓管1根,鼻腸營養管1根。
1.4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由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LDYYLL2021-12,所納入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132例患者,胰頭惡性腫瘤41例,良性疾病 10例,膽管下段膽管癌 43惡性腫瘤,良性1例,壺腹部惡性腫瘤12 例,十二指腸惡性腫瘤 25例。合并高血壓者29 例,合并糖尿病者26 例。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BMI、術前WBC、RBC、PLT、Hb、ALT、AST、TBil、Alb,糖尿病高血壓病史以及病理分型,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2.2 術中出血量及手術時間比較 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兩組患者在出血量及手術時長上均無明顯差異(P值均>0.05)(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3 術后第1天生化指標比較 術后第1天,兩組患者常規檢驗指標中BE組WBC水平高于BE組(H=-2.402,P=0.016),其他指標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
2.4 術后并發癥比較 與非BE組相比,BE組C級DGE發生率較低(P<0.05)。其他并發癥如出血、胰瘺(B+C級)、胃腸瘺、切口感染、傷口裂開、腹腔感染、腸梗阻及A級、B級、總體DGE生率均無明顯差異(P值均>0.05)(表2)。

表2 術后第1天生化指標、并發癥及DGE發生率比較
2.5 術后其他治療指標比較 與非BE組患者相比,BE組患者止吐藥物使用次數少,術后住院時間短,化療開始時間早,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在胃管持續時間、恢復飲食時間、住院費用方面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3)。

表3 術后其他治療指標
3 討論
目前研究認為PD術后DGE的具體病因尚未明確,多數研究支持可能與以下多種因素有關:促胃動素分泌的減少[10-11]、胃節律的破壞[12]、胃黏膜受反流性膽汁的刺激[13]、鴨爪神經損毀以及幽門切除喪失了對胃排出功能的約束,減少了膽汁反流入胃的阻礙[14-15]、吻合口狹窄或水腫[16]、術前合并糖尿病[17]、術后并發癥如:胰瘺、膽瘺、腹腔內感染[18]、精神心理因素[19]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而BE在理論上可能降低PD術后DGE的發生,故近些年部分研究者[1-4,7]將BE引入PD中。有研究[1-2,7,20]發現,BE方式可以降低PD術后DGE、堿性反流性胃炎或邊緣性潰瘍的發生。部分研究[7,21]甚至報道其降低了胰瘺的發生率。在Hochwald等[7]的研究中,BE組在DGE總體發生率、盡早拔除胃管、盡早進食、盡早出院等方面與非BE組有統計學差異,而臨床相關的DGE(B級+C級)差異更加明顯(7% vs 31%,P<0.01)。Xu等[2]研究發現,BE組DGE發生率顯著降低(6.7% vs 26.87%,P<0.001),且多因素分析顯示BE是唯一的獨立危險因素;同時BE組有著更低的臨床胰瘺發生率(P<0.001)。Meng等[1]研究顯示,胰腺殘端連續縫合加BE能顯著降低DGE(P<0.01)及臨床相關PF發生率(P<0.05),但是該實驗未能明確BE在結果中的具體作用,亦有可能是連續縫合降低了胰瘺的發生進而降低DGE的發生。部分循證學研究[22]同樣支持BE可降低DGE發生率的觀點。但是不同研究之間在重建消化道距離(BE口與胃腸吻合口)和BE吻合口徑上不一致,并在術后治療和護理方案上均存在差[1-4,7],部分研究[3-4]結果并不支持BE可以降低DGE發生率的觀點。
本研究中,BE減少了C級DGE的發生,與Xu等[2]的研究結果不同。本研究兩組患者在DGE總體發病率上未表現出明顯差異,這可能與本中心拔除胃管時間較晚,導致A級DGE占比(50.43%)較大有關。在目前PD手術加速康復外科理念的實施中,常規術后第2天拔除胃管[23],而本回顧性研究未施行加速康復外科理念治療策略,術后胃管持續時間大多超過3 d,故按照本研究采用的診斷標準,總體DGE發生率明顯高于同期國內水平[24]。在臨床上C級DGE患者術后嘔吐癥狀較明顯,止吐藥物使用次數較多,故在本研究中,BE在降低了C級DGE的發生率的同時,亦降低了術后止吐藥物的使用次數。除此之外,BE組患者術后住院時間較短,這可能與C級DGE患者住院時間較長,而BE組C級DGE患者明顯較少有關。
由于本回顧性研究在單一機構的局限性,未來還需更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統一手術步驟及術后治療護理方案,并在BE口徑以及與胃腸吻合的距離上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索。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楊思捷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撰寫論文;史志龍參與收集數據,修改論文;張輝、王正峰、周文策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