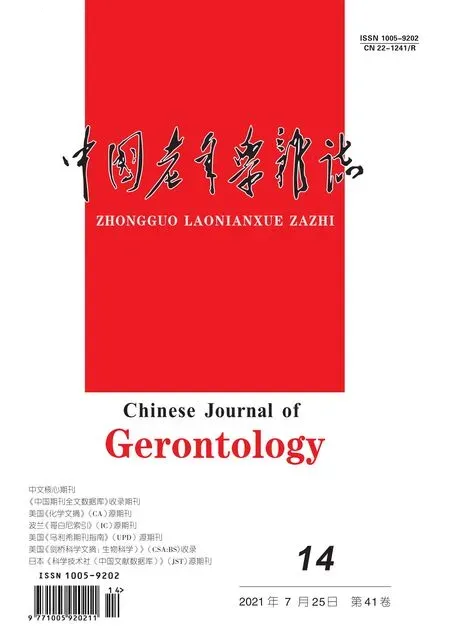湖南土家族中老年人BMI與Heath-carter體型的相關分析
張惠娟 黃大元 田淼 覃大保
(吉首大學醫學院 1護理系,湖南 吉首 415000;2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系)
Heath-carter 體型測量法是“國際生物發展規劃”推薦使用的綜合評價人體體型的方法,近年來已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應用于體質人類學、體育運動科學等領域〔1~5〕,然而研究內容主要以健康族群或者運動員的體型特征為主,營養與體型相關性的研究雖有報道〔6,7〕,但很少見。Baltadjiev等〔8〕研究2型糖尿病患者的體型特征時發現體重指數(BMI)與體型因子之間存在相關性。BMI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用于衡量人體是否超重、肥胖的一個重要指標,研究表明超重肥胖與多項健康風險密切相關〔9~11〕。因遺傳、環境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不同群體的體型特征及超重肥胖流行特點存在差異,故其BMI與體型因子的相關性亦可能存在差異。土家族主要聚居于湘鄂西、渝東南和黔東北地區,武陵山脈橫貫其間,境內有酉水、澧水、清江三大水系縈回環繞〔12〕。本研究旨在了解湖南土家族正常體重、超重肥胖人群的體型特征及BMI與體型的相關性。
1 對象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在知情同意的基礎上,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在酋水河流域土家族聚居地的湖南省龍山縣和保靖縣農村地區抽取50~79歲、身體健康、血壓正常、無畸形殘疾、無營養代謝性疾病、世居當地3代以上、自愿參與本次調查、測量方面無困難的本地土家族中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資料647例(男343例,女304例),男性平均年齡(64.19±7.04)歲,女性平均年齡(62.04±7.75)歲。
1.2研究方法 嚴格按照Heath-Carter人體測量法〔13〕規定要求測量研究對象的身高、體重等10項人體形態指標,根據公式計算BMI,依據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推薦篩查標準〔14〕,將男女性的BMI值進行分級:18.5 kg/m2≤BMI<24.0 kg/m2為正常體重,24.0 kg/m2≤BMI<28.0 kg/m2為超重,BMI值≥28.0 kg/m2為肥胖。所測數據按性別、BMI等級進行分組。根據Heath-Carter體型法的相關公式分別計算同性別不同BMI組及同一BMI組男女性的內、中、外因子值和X、Y坐標值、體型位置均數、體型位置距離(SAD)及身高體質量比率(HWR)等。
1.3質量控制 采用規范化的國際通用的測量儀器,測量之前校正儀器、培訓人員,統一標準,進行小樣本預測試,對各項測量指標每人重復測量兩次,前后兩次所得數據進行相關分析,相關系數r在0.9以上方可進行正式測量。除身高、體重外,其他8項指標均測量身體右側相應部位。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t檢驗、相關分析、二項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OC) 曲線,分析曲線下面積(AUC)。
2 結 果
2.1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形態指標測量結果 同性別不同BMI組之間的形態指標值比較,除了身高、肱骨內外上髁間徑無顯著差異外,其他指標均值正常體重組最小,超重組次之,肥胖組最大,而且各組之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P<0.01);同BMI組男女性之間的形態指標均值比較,除了BMI和上臂緊張圍無顯著差異外,四處皮褶厚度值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身高、體重、小腿圍、肱骨和股骨內外上髁間徑等均值男性明顯高于女性(P<0.05)。見表1。

表1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形態指標測量結果
2.2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體型特征 BMI等級值越大,土家族男女性的內因子、中因子、Y軸坐標值及體脂率值越大,而外因子、HWR、X軸坐標值及體密度值越小,同性別不同BMI組之間各體型參數均值比較,差異都有統計學意義(P<0.05),同BMI組男女性各體型參數值比較,除超重組、肥胖組的中因子值外,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13種體型分布中,男女性超重和肥胖組的體型以偏內胚層的中胚層體型、內胚層-中胚層均衡型和偏中胚層的內胚層體型3種類型為主,其中男性以偏內胚層的中胚層體型占絕對優勢,而女性這3種體型均占一定比例。見表3。從表4,圖1和表5可見,女性正常體重組、超重組和肥胖組各體型點在體型圖上位于內因子軸負值線稍下方從右向左分布,男性各體型點位于女性相應體型點的右上方,男女性各體型點之間的距離都相距較遠,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

表2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體型參數

表3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體型分布〔n(%)〕

表4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男女性體型比較

表5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之間的體型比較

圖1 土家族中老年人各BMI組的體型分布(●男,○女)
2.3超重、肥胖的Logistic回歸分析 分別以男、女性的BMI值確定是否為超重肥胖作為因變量,以超重、肥胖和正常體重的內因子、中因子和外因子為自變量,采用進入法進行二項分類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經模型系數的綜合檢驗,男女性的模型總體都有意義(P<0.05),經Hosmer and Lemeshow檢驗,認為當前數據中的信息已經被充分提取,男女性模型擬合優度都較高。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影響超重肥胖的主要因素是內因子和外因子,其中內因子是正相關因素,外因子是負相關因素,見表6。

表6 土家族中老年人超重肥胖的Logistic回歸分析
2.4預測超重、肥胖的ROC曲線分析 依據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推薦BMI作為篩查超重、肥胖的標準,將內、中、因子作為檢驗變量,正常體重和超重、肥胖作為狀態變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敏感度為縱坐標,“1-特異性”為橫坐標,繪制預測超重肥胖的ROC曲線圖,男女性內、中、外因子的AUC距離0.5都越遠,且P均<0.01,說明各組模型都有預測價值。見表7,圖2、3。

表7 預測超重、肥胖的ROC曲線分析

圖2 內因子和中因子預測超重肥胖的ROC曲線

圖3 外因子反向預測超重肥胖的ROC曲線
3 討 論
內因子值反映了體內脂肪含量,中因子值反映骨骼、肌肉的發達程度,外因子值反映了身體的瘦高程度〔13〕。本研究結果說明在身高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反映人體重量和橫向生長的指標如體重、皮褶厚度、圍度等指標均值伴隨著BMI等級值的增大而增大。體質量由脂肪質量和瘦體質量兩部分組成,瘦體質量主要成分是骨骼、肌肉等,故隨著BMI等級值越大,脂肪含量越來越高,體脂率隨之增高,同時骨骼、肌肉越來越發達,導致土家族男女性的內因子和中因子值增大,外因子和HWR值變小,線性度越來越差,身體充實度逐漸升高,以致于到了肥胖等級表現出內因子和中因子很高,外因子很低的極端體型,這與有關報道一致〔15〕。又因為脂肪的密度低于骨骼、肌肉的密度,而土家族中老年人的體密度值隨BMI等級值增加而減小,表明了土家族中老年人的BMI等級值增加主要是因為脂肪含量增加占主導地位所致。男性正常體重組、超重組、肥胖組和女性正常體質量組的平均體型均為偏內胚層的中胚層體型,女性超重組和肥胖組均為內胚層-中胚層均衡體型。本研究結果表明同民族、同性別之間BMI等級不同,其體型亦有差異;土家族中老年男女性,無論是體重正常還是超重或肥胖,其體型均存在性別差異。本研究結果可見,內因子值越大、外因子值越小,土家族中老年人越易發生超重與肥胖。

ROC曲線分析時,需要采取合適的診斷超重肥胖的篩查金標準,然而,有學者認為BMI作為營養評價標準可能存在著局限性〔18〕,主要是因為體質量由脂肪質量和瘦體質量兩部分組成,脂肪質量或瘦體質量的變化都會影響體重的變化。BMI由于沒有充分考慮到瘦體質量的變化,可能會出現一些假陽性和假陰性。Nevill等〔19〕研究發現用BMI評價運動員和普通人群的肥胖問題時存在差異,并提出需要適當調整運動員的BMI值,以便更好地反映運動員的肥胖問題。湖南土家寨一般建在半山腰,這種地理環境鍛煉了土家人較發達的骨骼與肌肉,又因土家人從小要從事繁重的與田地、山林有關的農耕勞作,使得他們的骨骼、肌肉相對發達,導致瘦體質量會增高,BMI值會增大,根據BMI評判標準可能為超重肥胖,但脂肪含量并不一定超標,從而出現超重肥胖假陽性現象;同樣,對于體力活動不足的少部分土家人,即使BMI處于正常值范圍,也可因瘦體質量偏低,出現脂肪質量可能超標的假陰性現象。因此有學者認為用BMI制訂營養異常篩查標準時應考慮到調查對象的體力活動水平〔20〕,也有學者〔21,22〕認為脂肪質量指數排除了瘦體質量的干擾,比BMI更適合用于肥胖的評價。可見,根據土家人體力活動情況,適當調整BMI值或者用脂肪質量指數作為診斷超重肥胖的篩查標準可能會提高土家族中老年人ROC曲線下面積估算體型三因子臨界值的準確性。